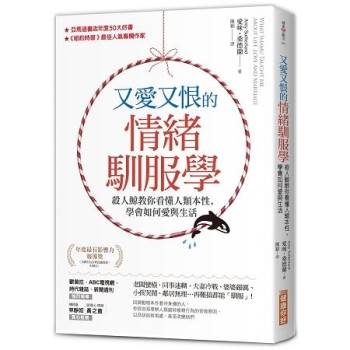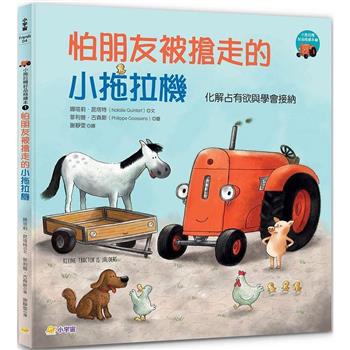對於愛書人來說,買到一本心儀的好書既講求時機,更講求緣分。買書及藏書的過程因這不可捉摸的緣而顯得妙趣橫生,令人回味無窮。
本書集結三十八位愛書人的買書回憶,通過分享淘書及藏書的過往,講述古舊書背後鮮為人知的趣聞軼事,展現書與人之間的緣分故事,一窺近三十年來古舊書收藏的變化。
作者簡介:
陳子善,華東師範大學教授,現代文學研究專家,著有《發現的愉悅》《看張及其他》《不爲人知的張愛玲》等,編有《知堂集外文》等。
許定銘,香港作家、藏書家,著有《醉書隨筆》等。
譚宗遠,雜誌編輯,作家,著有散文隨筆集《風景舊曾諳》《寂寞的纜繩》等,編有《嚴文井文集》(四卷本)。
謝其章,作家、藏書家,著有《創刊號風景》《搜書記》《書蠹艶异錄》等。
柯衛東,作家、藏書家。著有《舊書隨筆集》《舊書的踪迹》《迤逦集》等。
止庵,學者、作家,《周作人自編集》校訂者,《張愛玲全集》編者,著有《周作人傳》《茶店說書》《惜別》《受命》等。
傅月庵,台灣作家、出版人,台北茉莉二手書店執行總監,著有《生涯一蠹魚》《書人行脚》等。
胡桂林,收藏家、作家,著有《书情旧梦录》。
趙龍江,藏書家。
趙國忠,藏書家,著有《聚書脞談錄》《春明讀書記》等。
臧偉强,收藏家。
艾俊川,媒體人,古典文獻學者,著有《文中象外》《且居且讀》等。
王洪剛,藏書家。
龔晏邦,藏書家,著有《方寸書香:早期中國題材藏書票》。
白撞雨,古籍文獻藏家,著有《翕居讀書錄》。
胡文輝,學者、媒體人,著有《陳寅恪詩箋釋》《現代學林點將錄》《擬管錐編》等。
戴芒,藏書家。
方韶毅,新聞工作者、學者,著有《民國文化隱者錄》《東嘉故書譚》《獵書瑣談》等,另編有《伍叔儻集》《吳鷺山集》《過來人言》等。
林冠中,香港藏書家。
高山杉,學者,就職于中國社科院哲學所,著有《佛書料簡》等。
陳曉維,本書編者,著有《好書之徒》《書販笑忘錄》《像鑽石一樣閃耀》等。
胡同,布衣書局老闆。
陳逸華,臺灣九歌出版社資深編輯。
勵俊,著有《追尋江村秘藏》。
趙胥,收藏家。
……
作者序
陳子善
讀這麼多愛書人的買書回憶,我的感受可以用八個字來形容:津津有味,倍感親切。津津有味,是因為他們記述的買書經歷雖然有長有短,各各不同,但中文外文,古籍今籍,娓娓道來,均精彩紛呈,引人入勝;倍感親切,是因為他們之中竟有十九位,也就是正好二分之一,是我認識或者熟識的,新老書友蒐集珍藏了那麼多有趣有意思的書,我感到由衷的高興。
我也算是出入新舊書店和徜徉新舊書攤多年的人了,也有過在上海或北京天蒙蒙亮就趕早市淘舊書的記錄,足跡還遠至東京、大阪、柏林、漢堡、倫敦、劍橋、波士頓、洛杉磯和新加坡,在那些名城買過舊書或新書,自以為經歷不可謂不豐富,收穫也多多少少有一些,只是近年來因不上網而坐失購書良機無數,與書中各位愛書人相比,真是自愧不如,羨慕不已。因此,當編者不棄,要我為本書寫幾句話時,我躊躇再三,不知寫些什麼好。
思來想去,也來寫一寫我的沈從文書緣吧,雖然遠比不上曉維兄的《尋沈記》豐富和生動。
記得是1980或1981年的事。我只要不上課,往往上午泡圖書館,下午逛舊書店。當時上海舊書店只有“上海書店”一家,那天我踏進福州路上海書店內部書刊門市部,倪墨炎先生已先我而至。倪先生以收藏新文學書刊著名,也很會寫文章,我們早已是熟人,常在舊書店中見面。自然,我只是大學青年助教,他的“級別”遠比我高。內部書刊門市部有兩個陳列室,他都可自由進出,我卻只能進外面的一個,而“好書”往往都在我進不去的裏面那個陳列室,我為此一直引為恨事,但也無可奈何。
那天他從拎包中取出一書對營業員說:“買重了,換一本。”營業員認識這位常客,一口應允。我在旁偷眼一看,原來是沈從文的《邊城》單行本,機不可失,當即說:“老倪不要了,我買吧。”營業員倒也爽快:“可以!”於是我購得了《邊城》1934年10 月上海生活書店初版本,四十八開平裝,付泉零點六元整。
出得店門,走在熙熙攘攘的福州路上,心情大好,邊走邊翻書,竟還有更大的驚喜。我發現此書前環襯左下有如下毛筆字:
家延兄存 從文 廿三年十月卅日
沈從文三十年代的簽名本啊,且是此書出版當月送出的,實在難得,我幾乎欣喜若狂,真是一個美好無比的黃昏!
這是我獲得的第二本現代著名作家簽名本,第一本是巴金的《憶》。後來遇到倪先生,閒聊之餘,我忍不住問:“你不知道這本《邊城》是簽名本?”他答曰:“我怎麼不知道?但我不專收簽名本,我已有一本《邊城》初版本了,書品全新,正好讓你撿了便宜。”其實,這本《邊城》簽名本也有八成新。於是我倆相視一笑而別。
《邊城》簽名本上款所題的“家延兄”是誰?似非文學圈中人,一時難以查考,只得冒昧寫信向沈從文先生請教。張兆和先生在1983年7月23日覆信云:“家延是我中學的一個同學(女),姓潘,蘇州人,已故。”原來是作者送給夫人的“閨蜜”的。後來我據此寫過一篇小文《〈邊城〉初版簽名本》,這也是我寫的第一篇考證作家簽名本的文章。
當然,更重要的是,我出於好奇,把《邊城》初版本與天津《國聞週報》1934年1月至4月第十一卷第一、二、四、十至十六期最初發表的《邊城》連載本略作對比,發現兩個版本之間存在差異,也就是說初版本已作了修改,後來又讀到姜德明先生介紹《邊城》作者校註本(1935年4月再版本)的《寫在〈邊城〉的書邊上》,進一步意識到一部現代文學名著,往往存在多種不同的版本,這個問題非同小可。因此,當四川龔明德兄起意編“現代文學名著彙校本”叢書時,我自告奮勇,報名彙校《邊城》。沒想到龔兄出師不利,第一本《〈圍城〉彙校本》就出了“問題”,整個計劃也不得不付之東流。多年之後,金宏宇兄等終於出版了《〈邊城〉彙校本》(可惜他沒能利用姜藏作者校註本),我樂觀其成。
此後我雖不刻意但也一直留意搜羅沈從文1949年前的作品,但所得甚微。《記丁玲》正續集、《湘西》《廢郵存底》《長河》等初版、再版或更晚的版本倒是先後入手了,但也僅此而已,他早期(二十年代)的作品集,幾乎一無所獲,未免沮喪。直到九十年代後期在北京中國書店,從一堆雜書中翻出兩本沈從文讀過的書,才算為自己的沈從文書緣增添了新的別致的一章。
一本是《化外人》,歐美短篇小說集,傅東華選譯,列為“文學研究會世界文學名著叢書”之一,1936年3月商務印書館初版,為四十八開精裝本。但我購得的這冊已是殘本,硬布封面封底均已失去,而代之以牛皮紙補裝。這本小書本來不是什麼珍稀版本,何況還是殘本,我之所以如獲至寶,是因為書的前環襯和正文第一頁右側各有一行毛筆小字,分別為“從文 三十六年十一月 北平” 、“從文 三十六年十一月”。
沈從文的字自有鮮明特色,我早已熟悉。因此,我判斷這是沈從文的舊藏,當即購下,付泉二十六元整。
另一本是《思想的方法》,Graham Wallas 著,胡貽穀譯,列為“漢譯世界名著”之一,1936年10月商務印書館初版,小三十二開平裝本,封面封底也已失去,仍代之以牛皮紙補裝。但此書作者序文第一頁右側也有一行毛筆小字:“從文讀書 三十七年五月 北平”。此書雖然也是殘本,因也為沈從文舊藏,故一併購下,付泉五十元整。
從題字推測,沈從文閱讀《化外人》和《思想的方法》兩書時間當在1947、1948年間。“山雨欲來風滿樓”,郭沫若已在1948年3月發表的“名文”《斥反動文藝》中直接點了沈從文的名,而此時的沈從文除了繼續編刊撰文,還在讀外國小說,讀“思想的方法”……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思想的方法》一書中,不少段落有鉛筆圈點或打鈎,應均出自沈從文之手。
眾多中國現代作家中,只有魯迅的藏書(特別是後期藏書)保存得最好,早在1959年9月,北京魯迅博物館就編印了《魯迅手跡和藏書目錄》,以至有論者可以據此寫出《魯迅藏書研究》《魯迅讀過的書》這樣的著作。沈從文就沒有這樣的幸運。他從一個“鄉下人”成長為國際聞名的大作家,在不同的歷史時期讀過哪些書,受到哪些影響,由於他的藏書早已星散,這方面的研究確實難度不小。因此,這兩本我在無意中偶得的沈從文1947、1948年間讀過的書或可對此稍稍彌補一二。
除了《邊城》初版簽名本和1949年以前出版的沈從文其他作品,除了沈從文讀過的兩本書,我的沈從文書緣還應包括改革開放以後出版的他的作品。沈從文1980年5月初遷居北京前門東大街中國社科院宿舍。兩年後的8月,我在這裏首次拜訪他老人家,得到他的熱情接待。我帶去了新印的《從文自傳》 增補本(1981年12月人民文學出版社版)請他簽名,他欣然用毛筆在扉頁上寫下:
子善同志 沈從文 八二年八月
1985年8月,我最後一次拜訪他,又帶去《沈從文文集》 精裝本第一卷(1982年1月香港三聯書店版)請他簽名。他的身體狀況已大不如前,只能勉力在扉頁上用水筆寫下“沈從文 八五年八月”八個字。兩年以後,他老人家謝世,與該年的諾貝爾文學獎擦肩而過。從此以後,這兩冊沈從文為我而簽的簽名本,也為我所寶藏。
然而,我的沈從文書緣並未到此結束。十四年前,收藏家潘兄出版《百年文人墨跡:亦孚藏品》時,由我轉請董橋先生為之寫了序。他高興之餘,執意送我一幅沈從文的字,並再三說明,沈從文的字他已收藏多幅,這枚最小的送我略表心意,千萬不要過意不去。我卻之不恭,只能愧領。這也是我未曾想到的,沈從文書緣之後,又有了沈從文書法緣,也算應了“愛屋及烏”這句古話。
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毛筆字漂亮的作家不乏其人,但能稱得上書法家的並不多,沈從文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位。我得到的這幅字書於北京“榮寶齋監製”的白石老人瓜果小箋上,是一幅行書,全文如下:
圓丘有奇草,鍾山出靈液。王孫列八珍,安期煉五石。長揖當途人,來去山中客。
黃裳先生雅命
沈從文 卅六年仲夏 北平
落款鈐有兩方朱文印,一方為“沈從文章”,另一方為“鳳凰沈從文”。前一方鈐得有點模糊,故而再加鈐後一方也未可知。
這枚小詩箋是沈從文寫給黃裳先生的。黃裳在《珠還記幸.宿諾》中曾詳細回憶他“1947年開始起勁收集時賢書法時的事。曾託靳以寄了一張箋紙到北平去請沈從文寫字,不久寄來了。在一張小小的箋紙上臨寫了三家書法。包世臣、梁同書和翁方綱。在箋尾有兩行小字,是他自己的話,字也是他自己的面目”。沈從文給黃裳寫字遠不止一次,除了這幅“三家書法”,還有“一張長長的條幅”、“一張更長的條幅”等等。但我所得的這枚應該是篇幅最小的,他文中卻未提及。
巧的是,這枚小詩箋也書於“卅六年”(1947年)。所寫的六句詩出自東晉詩人郭璞的《遊仙詩》之七,沈從文只寫了此詩後半首的六句,而且可能是憑記憶所書,個別字詞有所出入。不過,他為黃裳寫字,古詩信手拈來,從中也可略知他的古典文學造詣。沈從文1949年前的書法作品傳世已經不多,除了為黃裳所書的大小字幅,我僅在許傑先生處欣賞過一紙昆明西南聯大時期寫在灑金箋上的橫幅。因此,這枚小詩箋也一直為我所珍愛。
沈從文的書法作品這些年來大受追捧,拍賣價格不斷飆升,我早望而卻步。不料六年前又有機會結識在美國的一位書史研究家,通過他購得沈從文1980年旅美期間在張充和先生寓所書的一枚落款“從文塗鴉 時年七十八歲”的小章草,總算是圓了一早一晚各一幅的沈從文書法緣。
我的沈從文書緣大致就是這些了,“多乎哉?不多也”,不過,我已經滿足。近來一直在想,愛書人是個可愛的雅號,而我只能勉強稱得上合格。真正的愛書人理應對書充滿感情,孜孜以求,難以割捨,但同時也應該是通達的。擁有一本好書,自然證明他與此書有緣;失之交臂或出於各種原因而無法擁有,固然遺憾之至,從另一個角度視之,不也說明他與此書無緣嗎?一切應該隨緣。
作為第三十八位愛書人的買書記歷,這篇不像樣的小文到此就該結束了。
甲午中秋於海上梅川書舍
陳子善
讀這麼多愛書人的買書回憶,我的感受可以用八個字來形容:津津有味,倍感親切。津津有味,是因為他們記述的買書經歷雖然有長有短,各各不同,但中文外文,古籍今籍,娓娓道來,均精彩紛呈,引人入勝;倍感親切,是因為他們之中竟有十九位,也就是正好二分之一,是我認識或者熟識的,新老書友蒐集珍藏了那麼多有趣有意思的書,我感到由衷的高興。
我也算是出入新舊書店和徜徉新舊書攤多年的人了,也有過在上海或北京天蒙蒙亮就趕早市淘舊書的記錄,足跡還遠至東京、大阪、柏林、漢堡、倫敦、劍橋、波士頓、洛杉磯和新加坡,在那些名...
目錄
陳子善 序 1
許定銘 長醉書鄉不願醒 9
譚宗遠 買書記憾 18
謝其章 海王村書肆之憶 22
柯衛東 冷攤奪魂記 34
止 庵 藏周著日譯本記 46
韓智冬 潘家園舊書攤憶往 62
傅月庵 念想 67
胡桂林 我的買書瑣憶 71
趙龍江 拾到的知堂遺物 83
趙國忠 尋訪老版本 91
臧偉強 我的題識本題贈本集藏 97
羅星昊 誤擁萬卷詩詞 114
艾俊川 不至異國,當得異書 121
王洪剛 買殘書 133
何家幹 揚州訪書記 139
龔晏邦 淘書六記 146
白撞雨 再訪海伊書鎮 156
胡文輝 擺花街上舊書香 162
馬 征 凌晨四點 166
戴 芒 買書家 173
林百川 海外搜書記 179
海上散木 我和《述學》的緣分 185
方韶毅 我買書的那點事 192
林冠中 南京圖書一老伯 198
葉 尋 淘書寄樂,聚書隨緣 203
高山杉 我淘到的一些東方學舊書和舊刊 214
陳曉維 尋沈記 226
胡 同 六十噸 234
周 運 我的OED情結 245
舒 罕 中行門下客 250
戴新偉 昆明訪書記 258
陳逸華 九十一天的訪書行腳 264
常青田 淘書十年記 270
勵 俊 尋找朱偰的十年 277
顧 諍 訪書散記 286
劉 聰 買舊書的回憶 294
趙 胥 收藏小記 300
陳曉維 編後記 308
陳子善 序 1
許定銘 長醉書鄉不願醒 9
譚宗遠 買書記憾 18
謝其章 海王村書肆之憶 22
柯衛東 冷攤奪魂記 34
止 庵 藏周著日譯本記 46
韓智冬 潘家園舊書攤憶往 62
傅月庵 念想 67
胡桂林 我的買書瑣憶 71
趙龍江 拾到的知堂遺物 83
趙國忠 尋訪老版本 91
臧偉強 我的題識本題贈本集藏 97
羅星昊 誤擁萬卷詩詞 114
艾俊川 不至異國,當得異書 121
王洪剛 買殘書 133
何家幹 揚州訪書記 139
龔晏邦 淘書六記 146
白撞雨 再訪海伊書鎮 156
胡文輝 擺花街上舊書香 162
馬 征 凌晨四點 166
戴 芒 ...

 共 3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3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