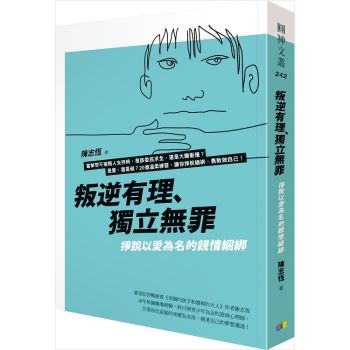推薦序
有人心碎?不讓斯人獨憔悴……
多年前,H的妹妹到巴黎。我和H聊著,妹妹突然插嘴道:「女同性戀不是都外型超美的嗎?怎麼會出妳們兩個長得超不怎麼樣的。」從小被她敬重三分慣了的我,當下驚駭不已。知道自己一教訓起人來,極易不留情面,對方又是對我們有些崇拜的小妹妹,我於是選擇沉默。然而這事真令我感慨:本來是被欽慕的姐姐的死黨,只因一朝被當成拉子,竟被如此輕薄。有天我又想起這事,我突然在腦海中,聽到當時H的話聲,她倒是沒事人般地振振有詞:「哪會啊,我們兩個都長得很不賴啊。」我們兩個長得賴不賴,當然不是重點,重點是,H聲音中活潑的生命力。我於是想道:同女有一種是動不動就會內傷的;另一種是像H這種,始終保有一股堅強的傻勁的。我自問:迴盪在我心中的,難道不應該更是H的聲音才對嗎?
性格女同志的璀璨之聲
一直以來,我都期待我所識或不識的,比較H的女同志,能投入書寫。令我滿心歡喜願意推薦《集體心碎日記》的第一個理由,首先就是,這本書正是那些鮮為外人所聞,風姿獨具且又毫不遲疑的性格女同志的璀璨之聲。
珍.習哈爾(Jeanne Cherhal)在一首笑謔「好女人史詩」的歌中,諷刺急欲與移民與同性戀劃清界線的女人,在臨死前才想到:她浪擲了她的時光∕她浪擲了她的B∕那些活在別處的人∕也許活得更好。與主流女人大大不同,《集體心碎日記》的主人翁身在一個「不浪擲B」的世界,然而作者柴並沒有美化這個選擇,像許多日記體傳統的創作,渾沌的真實遠較清澈的內容是其本質。然而,除了夠流麗的文筆與夠拉子的語言外,此作還是進入兩個特殊當代議題的難得入口。
文化災難現場的及時連線
第一個議題是有關移民經驗。揭露移民眼中異國面貌的作品,與該經驗的多樣性相比,數量並不多,《我在伊朗長大》中有慘痛的奧地利經驗,此外,台灣尚有外交人員之子女如段奕倫等給過一些「文化性被遺棄」的驚人片段。即便享有國際性地位的法籍精神分析學者如朱莉亞.克麗斯多娃(Julia Kristeva ),鑒於其保加利亞出身,仍自承會在特定情境中,有被法國社會摒除的憂戚之感。因此,《集體心碎日記》中隨處可見的邊緣者焦慮,並非被迫害妄想,而是肇因於四處可見、確有所本的緊張情勢。不能歡迎新人的城市是什麼城市?2008年,我從巴黎旅行到維也納,在電影圖書館裡有一女人與我攀談,阿拉伯裔法國籍的她,以流利德語在當地工作,但她說常有排外的人挑釁地問她:「妳為什麼還不回去?」我想了想,跟她說:「下次再有人這樣對妳說,告訴他∕她,都是為了他∕她,妳才不回去。只要有他∕她們這樣的人在這裡一天,妳就有很好的理由留下來。」--此理亦適用於《集體心碎日記》。這是移民以其良知與智識,進入新國境的文化災難現場進行及時搶救,並對外保持聯絡的行動--這種勇敢的立即抵抗精神,是我強烈推薦此書的第二個理由。
檢視我們當代受傷的「基礎自戀」
災難總是關乎良知,也總是關乎政治。法國哲學家貝納.史提各雷(Bernard Stiegler)在其作《愛、相愛、愛我們》中,分析資本主義的控制技術如何摧毀人們「基礎自戀」的可能。「基礎自戀」有兩大特性,一方面失去它會導致嚴重的身心危機:「我一開始不再愛我自己,我也就不愛任何別人,自此所有的違禁都可以來,我的行為既沒有任何限度,這意謂著我可以做出全然顛狂的妄行動(passage a l'acte de la folie pure)。」另方面,「基礎自戀」要存在,有賴於「我們」和「我」之間的扣連。然而一旦「我」被簡化為商品消費人,「我」的獨特性就逐漸被取消:「我」被等同於「我的消費行為」,又被等同於「其他人的消費行為」--這讓大規模的工業經濟得以成立,但這也是以逐步取消「我」為代價,「我」既然對於我越來越不存在,我當然也不可能愛我,「基礎自戀」一報銷,一切報銷。同志最初被經濟漠視,但當同志成為利潤目標後,意圖以定型化同志來製造純消費取向的同志「文化」的商業操縱也隨之展開。這是為何同志形象越來越可見,但同志卻會懊喪自己越來越不見的一個歷史困境。《集體心碎日記》最為驚心動魄的部份恐怕在此,那些不滿商業插手同志文化的或呻吟或怒吼,見證了當代「基礎自戀」飽受威脅的深沉不安與對其的直接衝撞。因此,我會這麼說我的推薦結語:這可不是一個商品櫥窗,這是一篇我們這個時代意圖全力活得像人的受傷史記。受傷所在,既是生命所在,更是重建集體生命之所在。
文∕張亦絢

 共
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