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1
陳健民(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客座研究員)
青年學者李宇森的《離散時代的如水哲學——政治主體與國際主義》是一個重要的思旅標記。他視離散為一種身份,討論「敍事」作為這身份形成的動態過程,但其終點並非本土主義所指向的國族的建構。他希望港人看見離散現象正在當代大規模發生,是資本主義的掠奪性、民主的倒退、國族的衝突、氣候變遷等綜合因素所造成;而各國右翼排外民族主義的興起,令這些政治、經濟、氣候難民狹在故國與他鄉之間,無處安頓。
李宇森認為港人既有祖先地域流動的歷史、又經過二〇一九如水抗爭的洗禮,如果能夠順應世道,更新眼光看離散的身分,反而可為香港以至這個世代帶來未曾想像的貢獻。要能這樣,港人必須養成對資本主義的批判、跨越國族藩籬的合作和對其他受苦的族群和物種的關切。
他這樣說:「我卻認為,只有當香港陷於離散的遭遇,當一國兩制的鳥籠民主普選終於顯露其虛幻之真身,當主權在民不能再化約為民族主權國家模式時,解放與希望才真的出現。這希望不在於固守在一時一地的立國夢,而是如何與千百年來的離散潮流融合,成為推動歷史變革的新力量,在民族國家之外尋求政治的新可能。」
這是我在離散港人群體中讀過最樂觀、最有抱負的一段話。但離散港人最熱烈討論的是在海外如何保存「真香港」;而矢志超越文化認同、邁向民族建國的,會檢討過去港獨運動失敗的因由; 極少港人會結連自身與其他族群(更不要說物種)的苦難,共同對抗厄運。有時我想,香港人不要再建起另一個無形的唐人街已是萬幸。那麼,書寫得如此精緻的《離散時代的如水哲學》有何意義? 會否落得國際主義左膠的罵名?作者自己很清楚,只靠理念不足以改變世界,這書的影響力還要看政治經濟條件的變化。但單是看見作者如此用心閱讀、思考、為抗爭運動尋求出路,那已是一個帶著希望的故事。(節錄)
推薦序2
許是化作春泥更護花
葉浩(臺灣國立政治大學政治系副教授)
據悉,《港區國安法》於二〇二〇年開始實施之後,香港外移人數已遠超過四十萬人,約佔總人口的十五分之一。
正在紐約「社會研究新學院」(The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就讀博士班的本書作者李宇森是否會加入這離散的行列,筆者無從判斷。但能確定的是他在短短數年間不僅在諸多媒體上勤於發表論述性文章,更以《主權在民:理念與挑戰》(2021)和《主權神話論:秩序和衝突》(2022)兩書鋪陳了一個偌大的思想史視野及批判視角,扎扎實實地以書寫作為一種行動來回應身處的時代困境。其振筆疾書的作為與相信理論具有改變世界的力量之信念,正如曾在該校任教多年的離散猶太知識份子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更重要的是,亦如鄂蘭在分析完納粹德國的極權主義起源之後轉向審視人類的根本處境,從而將理論建構的預設層次從民族國家提升至人類整體及其賴以生存的地球,《離散時代的如水哲學》也反映了作者的視域從作為一個主權國家之政治體制的民主拓展至主權國家體系的國際層次之後,將關懷轉向了與日俱增的離散人民及整個地球的生態環境。以本書的術語來說,那是一個意圖取代以民族國家為主要政治想像的「行星性」(planetary)政治哲學立場。民族太小了,人類才是真正的關懷主題!世界公民論(cosmopolitanism)的倡議者曾經如是說。雖然說這話的人在歷史上不乏亡國人士或起身反抗政權而流亡者,但本書拒絕單純將離散當作是一個不可更改的政治事實,也不以哲學修辭的堆疊來掩飾一種鄉愁乃至左派的憂鬱,而是企圖連結一切受迫離散的人民及主流西方政治哲學家較少正視的生靈。
本書的撰寫目的即是為了尋求一個能呼應離散主體並提供在外港人延續社會運動動能的方向。作者以「如水哲學」來稱呼它。「如水聚散,如水漲退」的原則意味一種因應揮動「社會主義鐵拳」的國家暴力之社會運動戰術,取自《孫子兵法》(或說李小龍的「Be water」武術哲學),是一種介於勇武對抗及毫不作為之間的積極行動,也是一種突破主權國家及民族主義的跨國高度之展現。畢竟,那些以高舉民族主義旗幟且不吝於對人民施鐵拳來展現政治權威的主權國家,就是讓人民流離失所並製造生態危機且百般阻礙解決方案的政商統治集團。戰略方向的闡釋之外,作者也提供了許多更為具體的連結其他離散主體之策略與戰術。事實上,本書已是一個規範性(normative)政治理論的嘗試。既有明確的價值追求,宏大的行動方向,更有從近處做起的具體且可行的處方。甚至可以說,《離散時代的如水哲學》本身即是「如水哲學」的一種實踐。相較於遁入虛無主義,冷嘲熱諷的犬儒主義或幾乎與文字遊戲難以區別的某些後現代理論,作者在許多人早已深陷絕望之處看到希望,甚至以文字和概念將這種希望化為具體可行的政治理論,為一個「法治」(the rule of law)正在成為歷史而「主權在民」正朝向遠方未來更遠處逝去的香港,提供一個更宏大的敘事作為行動的指引。
作為一個離散時代的海外香港人,本書的撰寫無疑也是「如水哲學」的一種實踐。在政治寒冬之中不卑不亢,以理論勾勒願景來代替控訴,讓海外港人能在心繫家鄉的同時,也攜手其他的離散族群為世界生態及未來的春天盡一份心力,許是一種既能落實港人哲思,又不落入政權所擅於操弄的狹隘民族主義,反而真正能擁抱世界的廣闊胸襟。那近乎一種化作春泥更護花的精神。筆者以為,將離散作為一個「實然」(is)轉化為一個可欲的「應然」(ought)願景,是一種極具政治理論創作力的展現。(節錄)
前言
李宇森
在二〇一九年七月上機的那一夜,我還記得是八號風球。十多個小時後,到達地球的另一方。下機一刻,內心有種抖動,好似心跳少了幾拍。我隱隱然感覺到,大概這是別離的滋味。可能以後,再也回不去那家鄉了。這幾年,一直在思索離散的主題,也寫過兩本書,只是一直無法連結個人的經歷,內心的掙扎和頭腦上的觀念。到底這時代經歷的離散,還可以如何被理論語言所轉化、個人與集體之間的辯證關係,如何在離散中展開新的可能,一直是我念念不忘的問題。離散既是命,也是運,福禍往往相倚。在離散的時代,如何推演著好的政治思想,發展出合乎當前時代條件的新主體和社群關係,實在是無比重要的事。輾轉在美國參與過一些離散組織的活動,又出席過某年的香港峰會。我一方面欣喜看到海外港人努力面對新的時代挑戰,不懈地連結組織,推動互助網絡,維繫著某種國際社會的聲援網;但同時不住地憂心,在行動之外,再也看不見更大的遠景。在當前波譎雲詭的國際形勢中,再談民主與世界革命早已不知所曰。列寧在百年前擲下一句「怎麼辦?」,今日再度縈迴心頭。
在理論的森林遊走多時,漸漸覺察到故事與敘述,或者才是我們的最終救贖。今天我們所需要的,不僅是故事和記憶,還要為故事正名。全因在敘事的世界,我們才得以擺脫財產個人主義所框限的群己分界,與萬物相連,跨越生死者的國度。敘事使我們連結,使我們得以展現倫理的生命。若要建立離散政治哲學來擴充政治視野,我們不單需要敘事,也要為敘事賦予更深刻的哲學基礎。這既是為了安身立命,也是在面對生態災難與資本主義世(Capitalocene)的離散時代,尋求解殖知識生產的可能。牙買加小說家和思想家西爾維婭.溫特(Sylvia Wynter, 1928-)曾言,人是講故事的物種,只是人常常忘了,以為自己只是眾多生物之一。人既有生物性的面向,但同時卻又跟萬物有所分別,當中的分別在於在云云萬物中,只有人類會訴說自身的故事。有了故事,人類才真的成為人。講故事的能力,像語言或者想像和記憶,固然都跟神經、身體和基因有關,但又只有人類,「作為說故事之人(storyteller),才能以故事敘述自身作為純粹生物(purely biological)狀態而存在的。」3換句話說,「人作為動物之一」的觀念,反而是因為科學敘事才得以可能。因此,人追求關於自身的科學知識,並非等於會順理成章地走進物理化約論(physical reductionism)的死胡同,視世間一切都只是物質活動、物理方程式結果和化學反應而已,反而間接地肯定了人作為敘事者的存在狀態。冷冰冰的科學世界觀,不過是眾多敘事可能之一。
因此,唯有敘事能產生意義、價值、理念和身份,以至與之相關的社會、經濟、政治架構,連帶馬克思的上下層社會經濟結構論(base and superstructure),大概應該要重寫一遍。語言和概念不再是經濟生產關係的產物,不再是單純服務於當前的主流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反倒是社會關係之根本,是一切經濟活動得以可能的先決條件。但我不是想重繪某種固定的歷史結構,因為這不過重覆著上述殖民系統思想的操作。反而令我感興趣的是這意義生產之意義。甚至可以說,只有當出現了敘事,人類才真的擁有自我意識,意識到自己的存在。因此我們可以說,不是人類發明了敘事,而是敘事創造了「人類」。
當然,這種黑格爾主義式的意識歷史辯證過程,很可能被視之為人類中心主義,因為看似只有人類才能站在這意識階梯的高位,宛如阿里士多德(Aristotle)所言,只有人作為政治和懂得運用言語的動物,是存活在天神與萬物之間。但溫特提醒我們,生物性也不過是敘事的結果,因此批判敘事也可跳出科學界對於物種邊界的牢牢劃分,改從物之集結性(assemblage)理解人理解自然、肉身跟技術物的混合體(cyborg),超越物種邊界和人的固定本質。若然如此,敘事來產生的關係網絡和意義,正是冰冷宇宙間的點點溫情暖意。更重要的是,這些敘事使得生者與死者得以在美學世界連結,在敘事的意義王國之中,生者和死者共同組成一個新的共同體,這便是身份和公共記憶的形成。對我來說,這才是離散政治思想的福音。
曾經歷「7.21」香港元朗黑暴事件,如今已離我們而去的前記者柳俊江(1981-2024)在書中寫道,「遺忘,不一定是自然現象。因為時間,記憶消退。因為創傷,選擇忘記。因為謊言,焦點模糊。因為利益,竄改歷史」。記憶和真相是長期的道德戰場,是群體和個人身份與主體性的永恆鬥爭,更是社會變革與否的希望所在。
換句話說,敘事並非單純是自由表達意見的表現,同時社會敘事也不一定盛載著自由多元之主體特質,也能被國家與資本力量馴化,變成意識形態工具。因此,強調意義生產的多元需要根本地抗拒著殖民性的人類中心觀,或者以宰制為核心的自然觀與主權中心觀,並通過敘事和再生產敘事來不斷重塑記憶和身份,從而帶來新的社會關係的想像和可能,新的自然—人—技術世界的意義網。比起阿里士多德的政治動物觀,即通過理性和語言述說價值、或者鄂蘭(Hannah Arendt, 1906-1975)視行動和創造作為體現人的平等的最重要條件,我認為敘事作為言說和行動,才是更為根本的倫理關係。這也算是和應著列維納斯(Emmanuel Levinas, 1906-1995)的「倫理作為第一哲學」的觀點。
因此,如何以新的敘事詢喚(臺譯:召喚)出解放性離散主體,並重新想像眾多離散社群作為廿一世紀的主要政治主體力量,並跟諸多生物死物、生者死者連結成無比重要的歷史推動力。在改造生活世界的同時,正面建立離散群體在政治思想的新範式(paradigm),正是拙作試圖拋磚引玉的嘗試。
作為政治思想形態的敘事,形式上不會限於虛構故事,不是只有童話或科幻之類的才算是敘事。這是在廣義上,蓋括所有故事、神話、歷史、記憶、知識等,都可列入敘事的行列。同時,敘事作為思想方式也可跟抽象推論的理論模型區別開來,前者更強調殊別性、在地性、開放性、世界觀和知識的生產/權力關係,也不會把非抽象觀念堆砌的文本和形式排除在政治思想視野之外。因此,這是從方法論上實踐解殖,避免重複著傳統西方哲學思想套路中高舉普遍抽象,貶低多元殊別與衝突的帝國思想方式。這些原則說易行難,只盼拙作能略盡綿力,嘗試理論地訴說敘事在離散政治的重要作用。
因此,拙作題為《離散時代的如水哲學》,其中六章會分成三個部份。頭兩章會首先討論離散的意思,如何以香港的苦痛連結離散時代,與哀哭的人同哭。我會先區分離散、移民和人口流動之別,還有猶太錫安主義與國際主義的離散概念,以突顯離散作為政治概念的多重意義。第二章會處理當下的時代特質,以離散時代作分期標名,既是因為政治經濟秩序孕育出來的新帝國主義,導致一波波離散人口的出現;另一方面,現代化帶來的生態危機,同樣使得離散現象劇烈地波及世界每個角落。
接下來的第二部份,在第三章我會重塑敘事作為非推論式(non-discursive)的政治思想方法,並深入地思考敘事結構和特 色,如何對應著多維度敘事主體的連結性。這敘事主體性的重構是第四章的主要部份,我會討論四層敘事主體觀,即肉身主體、虛擬主體、公共主體和行星主義,以及其各自的連結關係,以及當中的倫理關係。從人與物、人與技術物、人與人和人與行星自然之間的相連相交,既在單一維度上互相改造倚靠,且在點、線、面般不同維度上又有相互作用。這倫理性(the ethical)是不同於一般意義理解的道德(morality),前者強調的是關係和連結多於責任和規條,並且主體的倫理性跟敘事的結構是相互扣連的,人通過敘事加以連結,而反倫理之敘事正是暴力與不義之源,因為那是對行星世界關係網的毀滅,離散聯邦必須加以摒棄。
最後兩章則是關心離散敘事的實踐問題。第五章會先處理敘事政治的理論挑戰,特別是敘事作為政治技術,往往在消費主義和新帝國主義時代被馴化,成為管治和規訓的工具。我們若要喚起敘事論在離散政治中的解放力量,便需要認清其結構和作用。敘事作為進步政治的技術,跟其在離散主體覺醒所擔當的角色是分不開的,而離散主體怎樣連結起過去數百年的國際主義運動,使其能進一步連結離散群體以外的進步運動,也是這政治視野應發展的方向。最後一章,我會理解香港抗爭運動的如水哲學,作為敘事政治之實踐嘗試。過去對「如水」的詮釋,一直太局限在社運的戰術層面上,令人忽略更廣闊的戰略領域。我認為如水哲學能夠呼應離散主體之敘事觀,在社會運動陷入低潮的當下,推動我們去行動和連結,在離散時代擔當更前瞻的位置。香港不單只為香港自主而奮鬥,更是更是在摸索和實現後主權時代的新政治形態和想像。
因此,我希望敘事視野作為離散時代的新哲學,幫助我們在人工智能、人類世生態災難和全球民主倒退的動盪時代,想像出超越國族的政治形態。敘事的開放性和基進民主面向,都使得敘事共同體必然是多元眾數。只是,我提出「敘事聯邦」這政治視野,並不是期盼其能取代主權國家,能成為下世代的唯一國際秩序主體,一如有幾百年歷史的主權國形態,也不是由少數知識份子調控創作出來的理念產物,而是在無數人的建設與拉扯中形成今天的模樣。敘事聯邦不必然能取代主權國,但至少在並存時能創造出跨地域國族的身份和支援網絡,讓當前國際秩序能受到壓力,政治經濟系統能拉向我們心目中的方向,已是敘事作為政治抗爭的一大價值了。
最後,我希望能點明拙作在主權思考中的位置。在「否想主權三部曲」中,前兩集是以一破一立之方式寫成。第一部《主權在民論》是對歐洲主權在民思想史發展和演變的仔細梳理,而第二部的《主權神話論》,則是揭示和批判當前政治經濟的帝國支配秩序,以顯示舊有主權在民思想的局限,在當前必須加以克服和超越。因此,承接著帝國主義批判,這本《離散時代的如水哲學——政治主體與國際主義》在氣候危機和離散時代的時空前設下,嘗試否想主權在民理想中主體和身份記憶之邊界,重尋人民自主的新可能。主權者之民不能再停留在一國一族,而拙作希望照亮的是共同敘事的離散社群。
這既是知識人的公共責任,也是時代對我們的試煉,更是歷史的轉捩契機。是為序。
記於紐約皇后區2024 年 8 月18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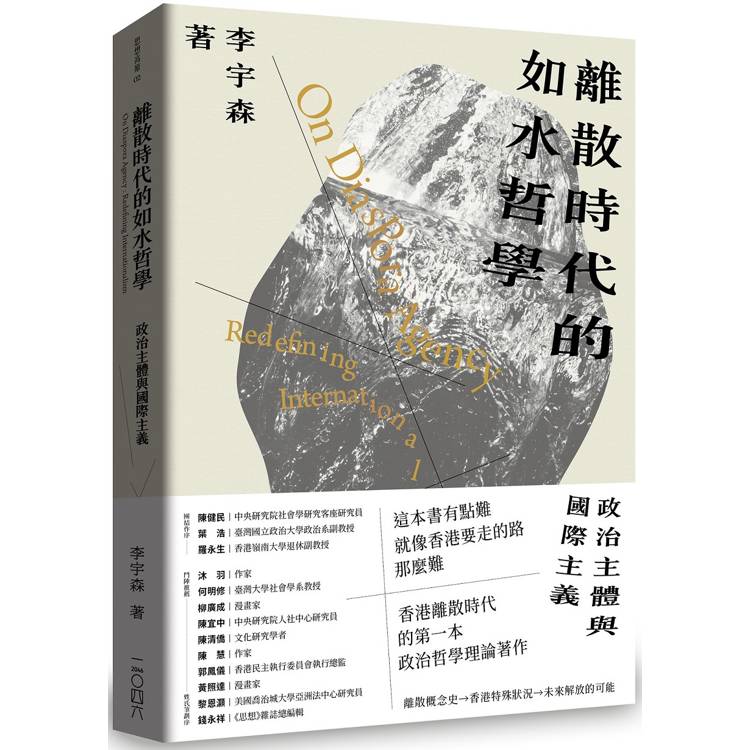
 共
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