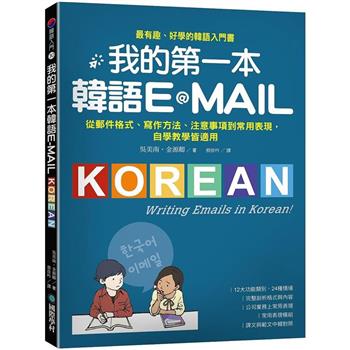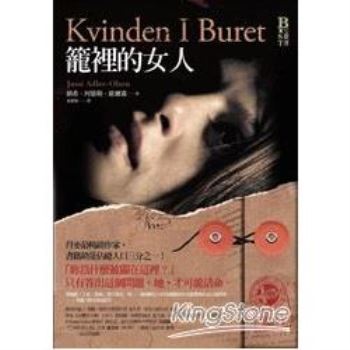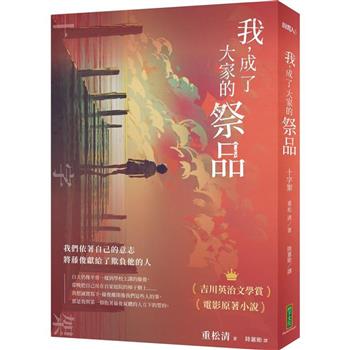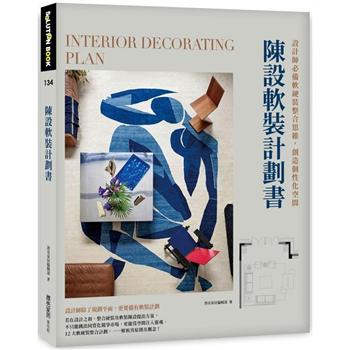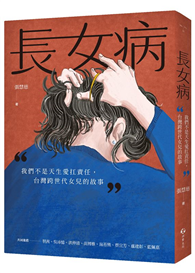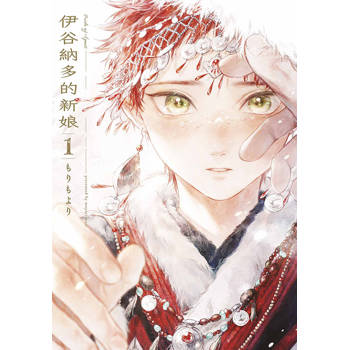一個處境,三個結局。
父親是執法者,兒子是抗爭者,一同困在資本主義的七十四樓,進退兩難!父子在槍管兩端對立,難道有辦法改寫人生?把歷史重新編造一遍?謎底就藏在解封的殖民地檔案中……
|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雲的理由的圖書 |
 |
$ 220 ~ 326 | 雲的理由
作者:鄺國惠 出版社:天地圖書 出版日期:2017-05-19 語言:繁體書  共 3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3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雲的理由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鄺國惠
香港土生土長,記者、小說及油畫創作人。著作有長篇小說《普洱茶》(「第一屆天地長篇小說創作獎」亞軍)、《消失了樹》,及短篇小說集《新聞在另一端》。作品《看樓》獲收錄於《香港短篇小說選:1998-1999》;《青花碗》獲「第二屆兩岸三地短小說大賽」優秀獎。
鄺國惠
香港土生土長,記者、小說及油畫創作人。著作有長篇小說《普洱茶》(「第一屆天地長篇小說創作獎」亞軍)、《消失了樹》,及短篇小說集《新聞在另一端》。作品《看樓》獲收錄於《香港短篇小說選:1998-1999》;《青花碗》獲「第二屆兩岸三地短小說大賽」優秀獎。
目錄
《雲的理由》引發的思緒 / 梅子 4
第一部
一 掌上的輕安 10
二 那邊好陽光 12
三 半條大道 20
四 來了一棵樹 29
五 僭建密室 39
六 資本主義七十四樓 52
七 升旗那邊 69
八 密室宣言 85
九 向後轉方程式 99
十 歷史反論述 115
第二部
一 免於恐懼的牛 130
二 立方體地磚 134
三 吹來一艘遠洋輪 146
四 旋律秩序美 158
五 摹想1972 174
六 舶來咖啡廳 191
七 雲的理由 205
八 越窗 215
九 時間小工兵 219
第三部
一 火車穿山洞 230
二 替雲找一條邊界 235
三 臉上大河 249
四 物理世界七十四樓 268
五 書扉上的廣場 287
附注 296
第一部
一 掌上的輕安 10
二 那邊好陽光 12
三 半條大道 20
四 來了一棵樹 29
五 僭建密室 39
六 資本主義七十四樓 52
七 升旗那邊 69
八 密室宣言 85
九 向後轉方程式 99
十 歷史反論述 115
第二部
一 免於恐懼的牛 130
二 立方體地磚 134
三 吹來一艘遠洋輪 146
四 旋律秩序美 158
五 摹想1972 174
六 舶來咖啡廳 191
七 雲的理由 205
八 越窗 215
九 時間小工兵 219
第三部
一 火車穿山洞 230
二 替雲找一條邊界 235
三 臉上大河 249
四 物理世界七十四樓 268
五 書扉上的廣場 287
附注 296
序
序
《雲的理由》引發的思緖
香港是公認的福地,罕見重大災禍;但在回歸前後一百七十多年裏,這褢卻也並非寧靜如「世外桃源」,恬謐如「無何有之郷」。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的風雨、波濤,大小交織,或疾或徐,可謂無時無之。終日為生計奔忙、無暇他顧的小民,久而久之,難免麻木;而義勇雙全的有識之士,卻於目睹耳聞之餘,總覺心中塊壘不吐不快,毅然宣之於筆,冀求有更多的人相呼互應、同聲共嗚,推動社會擯除弊陋,不斷進步向善。近年,其間出現了幾位小説家,他們認真回眸歷史、關注現實、反省文化、挖掘人性、體悟人生,施展自己得天獨厚抑或苦練而獲的聰明才智,創作了 一些別開生面、頗堪咀嚼的作品;香港文學的庫藏因了他們的貢獻'更加豐盈厚重、多姿多彩,引人囑目。本書作者鄺國惠,便是其中很可注意的一位。
鄺君風華正茂,現任職電視台,報道政治新聞並致力專題特寫。在二十多年記者生涯裏屢獲獎項,包括化The New York Festival(代表香港無綫電視台,2006、 2007及2008年),RTDNA The Edward R. Murrow Awards(代表香港無綫電視台,2003年)及香港人權新聞報道大獎(以採訪北京上訪者冤曲的《告御狀》,2005年)。業餘默默進行文學創作,迄今收穫可觀,成績斐然:早先,以短篇《烏鴉失踪一個月》,成為1992年「香港青年文學獎」小説公開組亞軍(雙亞軍,冠軍付闕)得主;1998年出手的短篇《看樓》,入選許子東編《香港短篇小説選1998-1999》(2001年香港三聯書店出版)。2016年,在第二屆兩岸三地短小説大賽上,其《青花碗》榮膺優秀獎。結集的小説已有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付梓、均以香港回歸前後為背景的三本:奪得1995年「第一屆天地長篇小説創作獎」亞軍(雙亞軍,冠軍付闕)的《普洱茶》(1997年);長篇《消失了樹》(2007年);短篇小説集《新聞在另一端》(2009年)。眼前這本回歸二十年前夕也將在天地圖書印行的《雲的理由》,應屬他的第三部長篇。
《雲的理由》的主角是一對父子,由於家庭破碎,彼此暌違。兒子經多年努力,成了渴求擢升的學院新進,因不滿現實,上街示威;父親卻是警察,被送去進修時,偏巧做了兒子的學生。二人不期相遇,關係頗為棘手。作者運用魔幻手法,安排父子三次重回同一歷史與政治場境,並分別以世故、冒進、優悠三種迥異的態度與方式,處理難題,從而碰撞出生命火花。不同身份的展開,帶來不同 的張力和結局,其中的象徼意義發人深省。作者似乎想問:倘若事後若干年,人們能再回到初始重來,曾有的一些錯誤是否可以繞過?這自是很有意思的問題,人類的許多教訓端賴它的啟迪而生。從這個角度看,本書不啻反思小説。
關於此著創作緣起,作者坦言,乃因感慨且受啟發於近年香港社會的「分崩離析,貧富憨殊」。他認為,社會現實令年輕一代躁動不安,出於善良之心,他們冀求改變社會,提出訴求,進而參加集會遊行,甚至以激進、浪漫的手法付諸行動,爭取理想的實現。「理想」原是歷久不衰、卻生了霉變、而今亟待重振的話題,作家在這座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接壤的城巿,再一次毅然為它寫作,大膽嘗試花大量篇幅討論公社、柏拉圖、資本主義、馬克思的解放社會,以及無政府主義學者Herbert Read的主張,從政治哲學的層面探尋「理想國」的真諦。他説:「小説以『雲』為題,描寫『從容』,正正是針對這問題,探索在紛擾的政治與歷史大環境中,如何從容自在,懷抱理想,走近理想。」他將「理想國」喻作「雲」、「水平線上的一點」,以及數學中的「線」;覺得這些都是奇特的東西,觸摸不到,卻又深入日常生活中。如此構思,有其現實意義,也委實不無膽識和巧技。從這個角度看,本書又不啻前瞻小説。
值得注意的還有,作者既矚目當下、瞻望未來,也不忘歷史。小説通過交代人物活動與解封文件,闡述了英國政府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早已訂下處理香港前途的大策略,並在聯合國相關決議案中實施了出來。這一段故實,據知香港人從未獲悉,正如小説中人物有感而發的,「就像從未發生過」。不過更教人感慨繫之的是,作者也似乎想問:一旦知道了這些「新資料」,我們會相信、拒絕接受、抑或無視它呢?他透露:「作品不單止自我期許為一部記載歷史的小説,亦着力營造神遊古今的恍惚感,思考歷史本身究竟是怎麽一回事。」從這個角度看,若言本書有點「政治揭秘」小説之影,想必也不致被譏為無稽之談。
無論視為「反思小説」也好、「前瞻小説」也好,甚或「政治揭秘小説」都好,均未圓滿道出作者寫作這部長篇的初衷。我以為,本質上,「渴望變革以致美滿」才是此書核心所在。細説之,非長調大論不可,這篇短文未能勝任,留予高手最是相宜。但在文末,我還想補充兩段話:
古今中外的變革之路何曾一帆風順,要達致理想向來須披荊斬棘、前仆後繼;倘能正視歷史經驗與教訓,冷靜、持續地把握民心,看清世潮與國族命途的大勢,朝光明之境無私地開拓前行,挫失應是成功之母。
作者是富有抱負和使命感、歷史意識和人文關懷、特立超然、篤思實幹、勸學好問的作家、記者,只要回顧其創作歷程,特別是他自九七年香港回歸迄今的筆耕心路,從《看樓》、《普洱茶》、《消失了樹》、《新聞在另一端》、《青花碗》一路看來,不難察覺:其足跡總緊靠社會的風雲、差別和變異,尤其是集體記憶;其筆觸總圍繞人生的跌宕、不安、悲苦和人性的難測、多變、異化;其情感總牽扯身份的危機、考驗、歸向和在歷史轉折時刻「人的處境」;殫精竭慮總為尋求公義而致,奇思妙想總由切身體察而生,藝術技法(如寫實、魔幻、象徵、意象、意識流、援引傳説、寓言、回憶及夢境加強敘述、提煉關鍵命題、詩意和哲理等等)總合思想内容而行。「只要能讓大家再一次想到這個地方,這些年頭做過些甚麽,我實在感到欣悦。」他如是説過,教我們對他有殷殷期待。
祝福鄺君,更上層樓!
《雲的理由》引發的思緖
香港是公認的福地,罕見重大災禍;但在回歸前後一百七十多年裏,這褢卻也並非寧靜如「世外桃源」,恬謐如「無何有之郷」。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的風雨、波濤,大小交織,或疾或徐,可謂無時無之。終日為生計奔忙、無暇他顧的小民,久而久之,難免麻木;而義勇雙全的有識之士,卻於目睹耳聞之餘,總覺心中塊壘不吐不快,毅然宣之於筆,冀求有更多的人相呼互應、同聲共嗚,推動社會擯除弊陋,不斷進步向善。近年,其間出現了幾位小説家,他們認真回眸歷史、關注現實、反省文化、挖掘人性、體悟人生,施展自己得天獨厚抑或苦練而獲的聰明才智,創作了 一些別開生面、頗堪咀嚼的作品;香港文學的庫藏因了他們的貢獻'更加豐盈厚重、多姿多彩,引人囑目。本書作者鄺國惠,便是其中很可注意的一位。
鄺君風華正茂,現任職電視台,報道政治新聞並致力專題特寫。在二十多年記者生涯裏屢獲獎項,包括化The New York Festival(代表香港無綫電視台,2006、 2007及2008年),RTDNA The Edward R. Murrow Awards(代表香港無綫電視台,2003年)及香港人權新聞報道大獎(以採訪北京上訪者冤曲的《告御狀》,2005年)。業餘默默進行文學創作,迄今收穫可觀,成績斐然:早先,以短篇《烏鴉失踪一個月》,成為1992年「香港青年文學獎」小説公開組亞軍(雙亞軍,冠軍付闕)得主;1998年出手的短篇《看樓》,入選許子東編《香港短篇小説選1998-1999》(2001年香港三聯書店出版)。2016年,在第二屆兩岸三地短小説大賽上,其《青花碗》榮膺優秀獎。結集的小説已有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付梓、均以香港回歸前後為背景的三本:奪得1995年「第一屆天地長篇小説創作獎」亞軍(雙亞軍,冠軍付闕)的《普洱茶》(1997年);長篇《消失了樹》(2007年);短篇小説集《新聞在另一端》(2009年)。眼前這本回歸二十年前夕也將在天地圖書印行的《雲的理由》,應屬他的第三部長篇。
《雲的理由》的主角是一對父子,由於家庭破碎,彼此暌違。兒子經多年努力,成了渴求擢升的學院新進,因不滿現實,上街示威;父親卻是警察,被送去進修時,偏巧做了兒子的學生。二人不期相遇,關係頗為棘手。作者運用魔幻手法,安排父子三次重回同一歷史與政治場境,並分別以世故、冒進、優悠三種迥異的態度與方式,處理難題,從而碰撞出生命火花。不同身份的展開,帶來不同 的張力和結局,其中的象徼意義發人深省。作者似乎想問:倘若事後若干年,人們能再回到初始重來,曾有的一些錯誤是否可以繞過?這自是很有意思的問題,人類的許多教訓端賴它的啟迪而生。從這個角度看,本書不啻反思小説。
關於此著創作緣起,作者坦言,乃因感慨且受啟發於近年香港社會的「分崩離析,貧富憨殊」。他認為,社會現實令年輕一代躁動不安,出於善良之心,他們冀求改變社會,提出訴求,進而參加集會遊行,甚至以激進、浪漫的手法付諸行動,爭取理想的實現。「理想」原是歷久不衰、卻生了霉變、而今亟待重振的話題,作家在這座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接壤的城巿,再一次毅然為它寫作,大膽嘗試花大量篇幅討論公社、柏拉圖、資本主義、馬克思的解放社會,以及無政府主義學者Herbert Read的主張,從政治哲學的層面探尋「理想國」的真諦。他説:「小説以『雲』為題,描寫『從容』,正正是針對這問題,探索在紛擾的政治與歷史大環境中,如何從容自在,懷抱理想,走近理想。」他將「理想國」喻作「雲」、「水平線上的一點」,以及數學中的「線」;覺得這些都是奇特的東西,觸摸不到,卻又深入日常生活中。如此構思,有其現實意義,也委實不無膽識和巧技。從這個角度看,本書又不啻前瞻小説。
值得注意的還有,作者既矚目當下、瞻望未來,也不忘歷史。小説通過交代人物活動與解封文件,闡述了英國政府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早已訂下處理香港前途的大策略,並在聯合國相關決議案中實施了出來。這一段故實,據知香港人從未獲悉,正如小説中人物有感而發的,「就像從未發生過」。不過更教人感慨繫之的是,作者也似乎想問:一旦知道了這些「新資料」,我們會相信、拒絕接受、抑或無視它呢?他透露:「作品不單止自我期許為一部記載歷史的小説,亦着力營造神遊古今的恍惚感,思考歷史本身究竟是怎麽一回事。」從這個角度看,若言本書有點「政治揭秘」小説之影,想必也不致被譏為無稽之談。
無論視為「反思小説」也好、「前瞻小説」也好,甚或「政治揭秘小説」都好,均未圓滿道出作者寫作這部長篇的初衷。我以為,本質上,「渴望變革以致美滿」才是此書核心所在。細説之,非長調大論不可,這篇短文未能勝任,留予高手最是相宜。但在文末,我還想補充兩段話:
古今中外的變革之路何曾一帆風順,要達致理想向來須披荊斬棘、前仆後繼;倘能正視歷史經驗與教訓,冷靜、持續地把握民心,看清世潮與國族命途的大勢,朝光明之境無私地開拓前行,挫失應是成功之母。
作者是富有抱負和使命感、歷史意識和人文關懷、特立超然、篤思實幹、勸學好問的作家、記者,只要回顧其創作歷程,特別是他自九七年香港回歸迄今的筆耕心路,從《看樓》、《普洱茶》、《消失了樹》、《新聞在另一端》、《青花碗》一路看來,不難察覺:其足跡總緊靠社會的風雲、差別和變異,尤其是集體記憶;其筆觸總圍繞人生的跌宕、不安、悲苦和人性的難測、多變、異化;其情感總牽扯身份的危機、考驗、歸向和在歷史轉折時刻「人的處境」;殫精竭慮總為尋求公義而致,奇思妙想總由切身體察而生,藝術技法(如寫實、魔幻、象徵、意象、意識流、援引傳説、寓言、回憶及夢境加強敘述、提煉關鍵命題、詩意和哲理等等)總合思想内容而行。「只要能讓大家再一次想到這個地方,這些年頭做過些甚麽,我實在感到欣悦。」他如是説過,教我們對他有殷殷期待。
祝福鄺君,更上層樓!
梅子
2017年2月26日夜,香港。
2017年2月26日夜,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