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另類的藝術寫照
從來藝術都以一高華姿態面世,予人特多審美享受,為世上知識經驗/道德經驗以外第三大經驗。此經驗著重在趣味的營造和炫異,事涉美醜價值的估定取捨,已跟前二者所關連的真假/善惡市值競逐有日,甚至在被恆久需求性上還要略勝一籌。
然而,由此一藝術總綰的審美經驗,卻因世人僅當它但存活於現實中而鮮知別有來自靈界相關機制的控勒,致使藝術從產出到接受一直為意外變項所左右,無法給予有效的觀照解決或填補罅漏,徒然造成一門藝術學「鷹視缺位」的莫大遺憾!
以位居優位的創作(產出)來說,藝術越臻上境,成就它所需的才氣越顯重要;而此才氣除了自我稟靈內蘊,再來就是外靈助益。此類助益,有的借體而展現,有的啟導而複製,有的協商而促進,管道多元,價值也不一。這都要細密勾織,以發微藝術的另類寫照,而為藝術的新看待方式張目,以及給藝術教育預留一個彈性空間。
這所能取則的,自有史例斑斑且跡證可感;而相關爬羅剔抉所得備足的理論資源,也不乏陳案在先而為我統轄論定,諸如《靈異學》/《靈異語言知多少》等集中詳示及《中國符號學》/《語用符號學》/《新說紅樓夢》等間為據例著範,幾已全機遇在此書中生效。因此,所布列的〈新學科的召喚〉/〈概念界定〉/〈靈異藝術成學的緣起〉/〈靈異藝術可能的分布〉/〈靈異藝術的造就評估〉/〈靈異藝術的功能〉/〈靈異藝術的文化意義〉/〈新學科的新希望〉等論綱及其細目設定並據為暢論的,無疑能自成一門可名為「靈異藝術學」的新學科(既是科別又能當書名)。規模已具,理解藝術又增多一殊異途徑。
有此一殊異途徑,便能進一步從所貞定的「跨域差異的察覺」/「相仿效或相涵化的可能性辨識」/「美感益世的從新出發」等文化意義而繁衍出「靈異藝術學成立後的學科調整」/「靈異藝術學伸展時的兩界互動蘄嚮」等新希望,一門新學科終於嫣然底定。
周慶華
第一章 新學科的召喚
第一節 繆斯出場見證後
藝術緣何而起,始終是好異者所關心的課題,卻又儘無能探得真切,以致蹉跎至今它仍然停留在「事出有因,查無實據」的階段,而徒讓其他人跟著揣測紛紛。
即使如此,在眾臆度中還是會有某些較合理則的說詞躍居顯眼位置,如「天縱英才」/「天啟英才」一類源出觀,就各自佔有難以駁斥的地位。前者(指「天縱英才」)的先天具備特性,一向不勞繁徵;後者(指「天啟英才」)的後天感應特性,也不乏實證基礎,彼此都冒有天才實名又暗中在互別苗頭(誰說的比較實在)。所謂:
學問有利鈍,文學有巧拙。鈍學累功,不妨精熟;拙文研思,終歸蚩鄙……必乏天才,勿強操筆也。(顏之推,1978:20)
有天才的人、詩人、哲學家、畫家、音樂家都有一種我不知道是什麼的特殊、隱密、無從規定的心靈的品質;缺乏這種品質,人就創作不出極偉大、極美的東西來。(華諾文學編譯組編,1985:118引狄德羅語)
這一「必乏天才,勿操強筆」/「(缺乏天才)人就創作不出極偉大、極美的東西來」的考索,就反面提撕了前者的說法,幾乎難可移易,畢竟相似的論調已多到數不勝數(寒哲[L. J. Hammond],2001;波恩-杜貞[M. Bohm-Duchen],2004;約翰遜[P. Johnson],2008;陶伯華等,1993;張毅清等,2011),想否定它還得花費不少力氣。又所謂:
對許多靈學研究者來說……許多通靈藝術作品都令人印象深刻;不但是作品本身,更因為它們所呈現出來的風格和原創的偉大藝術家非常接近。不僅如此,有些通靈藝術作品不管是在風格的多樣性和質量的比例上,都令人嘖嘖稱奇。(劉清彥譯,2001a:50~51)
這一「神成藝術家」的見識,就正面驗實了後者的說法,有同感者自能指證歷歷;而依所累積的偌多案例(赫伯金[B. Hopkins],2004a;蘭德爾[D. K. Randall],2013;桐生操,2004;林在勇,2005;欒保羣,2013;南山宏編著,2014)來看,也由不得人不信。
上述二說各自所結穴的天才實質,演現後都有藝價標高的特徵(縱是一為「與生俱來」一為「感靈而有」)。這在不分彼此的具力差異(或較量說法的實在性)時,就都歸給神靈(或鬼靈)的眷顧,當那些人獨蒙榮寵而被鑠定啟導出眾了。只不過前者已無從追踪(誰也沒辦法尋繹出當事人與生俱來多少才份),但剩後者不斷在向人暗示外靈介入藝術創作的高昂興致。
此一高昂興致,從古希臘時代詩藝興起以來,就沒少過在摻和顯能且旁衍擴及其他領域。如柏拉圖(Plato)的文藝對話集〈伊安篇〉提到詩人是一種充滿磁力且長著羽翼的神聖物,除非受到啟示,否則寫不出詩來,因為讓他吟出詩句的不是技藝而是神的力量(柏拉圖,1986:36~38)。這往前諸證荷馬(Homer)的史詩在每部開卷都留有一段向文藝女神繆斯(Muses)祈求靈感的話(荷馬,2000a;2000b)已是不假;往後察考眾藝術門類間有逞才立異跡象的比數仍多(肯納[T. A. Kenner],2009;視覺設計研究所,2009;並木伸一郎,2016),使得現存的一切審美經驗很難不為它保留一個超常的變項。
這在後人還將該變項分由九個繆斯所掌控:卡利俄珀(Calliope),主司史詩;克利俄(Clio),主司歷史;厄拉托(Erato),主司抒情詩和贊歌;歐忒耳珀(Euterpe),主司長笛;墨爾波墨涅(Melpomene),主司悲劇;波呂許謨尼亞(Polyhymnia),主司演劇、音樂和舞蹈;忒耳普西科瑞(Terpsichore),主司抒情詩和跳舞;塔利亞(Thalia),主司喜劇;烏拉尼亞(Urania),主司天文(克里斯托[D. Crystal]主編,2000:708)。雖然詩人或其他藝術家仍然可憑己力自鑄偉貌,但在眾靈掩至強為左右希巧事成真的情況下,人的本事究竟還存剩幾分就不好說了。
正由於有繆斯出場見證,而讓古希臘時代一度繁茂的藝術(貝洛澤斯卡亞[M. Belozerskaya]等,2005;蘇利[S. A. Souli],2005;閣林製作中心編,2010a)人控色彩淡薄了許多,致使後來陸續在其他地區發現(或早或晚)的類似案例(佳慶編輯部編譯,1984;閣林製作中心編,2010b;閣林製作中心編,2010c)也無不要同等看待(只是背後的神譜不一樣而已),相關的解會才能恰到好處。此外,如果有什麼因應對策必須研練出來,那麼也得先探知這一波的機遇如何方可底定。
第二節 藝術從此得關連靈異
眾藝術中或許屬詩的成製難度較高,特別能滿足繆斯藉以炫技的需求,馴致有柏拉圖文藝對話集〈伊安篇〉所說的「(詩神就像磁石)她首先給人靈感,得到這靈感的人們又把它遞傳給旁人,讓旁人接上他們,懸成一條鎖鍊。凡是高明的詩人,無論在史詩或抒情詩方面,都不是憑技藝來做成他們的優美的詩歌,而是因為他們得到靈感,有神力憑附著」(柏拉圖,1986:37)。神力附在人身上使他迷狂(狂歡)而吟唱出詩(歌),這詩(歌)有韻節和優美詞句等就一起顯揚了詩神高超的才藝。
類似的感靈情況(或說神靈的入戲興致濃厚),已甚為普遍。如另一〈斐德若篇〉所載,連人誦讀詩及論斷愛情等也會有神靈憑附著(柏拉圖,1986:159、163)。而依所歸納,神靈憑附的迷狂可分成四種:「預言的、教儀的、詩歌的、愛情的。每種都由天神主宰:預言由亞波羅,教儀由達奧尼蘇斯,詩歌由繆斯姊妹們,愛情由阿弗若第特和愛若斯。」(柏拉圖,1986:205)如此一來,藝術不關連靈異也難。
這種關連,依實情不僅上述神附(被借體)一類,還有夢感/通靈對接/自煥等多種狀況(詳見第四章)。它早已在人類社會觸處可見效驗著(西爾瓦[F. Silva],2006;穆尚布萊[R. Muchembled],2007;法林頓[K. Farrington],2007;麥克肯恩[C. McCann],2009;白川靜,1983;周策縱,1986;張開基,2000;劉清彥譯,2001b;金沛星編著,2014);但遺憾的是「研究者和懷疑論者通常會以壓抑的創作能力或潛在的第二人格解釋這種通靈藝術創作的現象。也許我們永遠無法得知這種事發生的原因和方法。跟其他那些超自然現象相較,這種靈異現象不但完全沒有傷害,還可以產生許多美麗的藝術作品」(劉清彥譯,2001a:54)。當中有甚多尚待釐清的問題,自然也隨這一還只是表顯的憾事常存了。
基本上,藝術為審美對象所繫,勾動人的情緒深且久遠。它跟知識對象所繫的哲學/科學或道德對象所繫的倫理/宗教比起來,特別有一種神祕的魅力(魔力)。這種魅力,曾被讚嘆連連卻又渺不知來由。所謂:
從蘇格拉底(Scorates)到偵探小說家錢德勒(A. B. Chandler)筆下的惡棍,每個人都為美而心折。古羅馬詩人奧維德(Ovid)稱美是「諸神的贈禮」,全世界的人都在追求美的魔力。美一直是道讓人屏息的謎,它的光彩奪目,讓許多藝術家動容。科學已經告訴我們,美是多種元素構成的奇怪之物,非大部分人所能理解;研究人員現在仍在探索美為何有如此大的力量,美到底是什麼東西。(麥克奈爾[D. McNeill],2004:7)
這美惑說不啻代大家道出了心中那一難以言喻的痴迷感受。甚且有人還戲謔的述及他「有一股既瘋狂又崇高的欲望,想要把美給宰了」(丹托[A. C. Danto],2008:94引查拉語);而愛到極點連命也不顧了「數百年來,藝術史學家一直對這幅畫〈蒙娜麗莎畫像〉深感不解……1852年,法國一位年輕藝術家在寫完以下文字後,從巴黎旅館四樓的窗戶躍身而下。他寫到『多年來,她的微笑令我相當掙扎,現在我寧可死去』」(韋斯曼[R. Wiseman],2008:76)。這都一致的沉浸在美中而無法自拔。
對於藝術這一美物,向來被討較創作時儘關連著心理/社會/經濟/文化等層面而無暇(或不知)旁顧其他(索羅斯比[D. Throsby],2003;海布倫[J. Heilbrun]等,2008;亞歷山大[V. D. Alexander],2009;朱光潛,1988a;陳秉璋等,1993;丁亞平,1996)。即使有人知道藝術創作有潛伏期「但發生在『暗』處者,不容作正常的分析,而且喚起古怪的神祕感來遮蓋天才的作品:人們於是得有必要訴諸神祕論,祈求繆斯的聲音來解釋」(契克森米哈頓[M. Csiksentmihalyi],1999:121);然而一旦進入後設思辨層次卻是逕直的論及上述那些變項,跟他處有關藝術哲學的設想相去不遠(丹納[Hippolyte-Adolphe Taine],2004;貝維拉達[G. H. Bell-Villada],2004;凱斯特[G. H. Kester],2006;夏呂姆[Jean-Luc Chalumeau],2007;姚一葦,1985;曾祖蔭,1987;張法,2004)。殊不知藝術最奧妙難解的部分莫不要跨向靈界找答案(現實界已無處可著力),而相關論述乏能或忌諱稍事牽涉,這所喪失的不僅是那現成解數徒遭埋沒,更是進益藝術管道的恐將永遠尋索無門。
深入一層看,藝術創作所依恃的才,凡是有與生俱來的,也幾乎都得靠神靈的愛惜護佑,方能維持在創作平臺上的慣使無礙(或說才的施展想適得其所而不致亂套,很難沒有神靈在終極上或關鍵時刻予以愛惜護佑)。這有個例子可以佐證:相傳黃帝史官倉頡造字時「天雨粟,鬼夜哭」,前人的注解以為「倉頡始視鳥迹之文,造書契,則詐偽萌生。詐偽萌生,則去本趨末,棄耕作之業,而務錐刀之利。天知其將餓,故為雨粟。鬼恐為書文所劾,故夜哭也」(高誘,1978a:116~117)。這以天神(自然靈力特強者)會憐憫和鬼靈會駭怕來看待倉頡造字一事,很明顯嫌消極且無所本(更何況它還倒果為因:就是人本就會詐偽,文字不過是方便為所利用而已;但它卻反過來以為有了文字才行詐偽,不啻顛倒了因果關係)。同樣是臆測,為何不轉積極而把「天雨粟」視為是天神對倉頡能造字的獎賞而將「鬼夜哭」當作是鬼靈對原同類卻比自己強甚的倉頡能造字的感佩(喜極而泣)(周慶華,2006a:79)。理由就在於「人情」通「神情鬼情」可如此類推以得:依中國傳統氣化觀型文化明示,造字一事所以可能(即使沒有倉頡這個人,我們仍然可以推得文字一類被造物的受造歷程),就是人稟靈(精氣)的結果;由於人稟靈,內蘊有造字的潛能,所以在他努力發用後經過神靈的鑑識肯定(神靈本身就有這個能耐,才會降下粟米獎賞造字的人),接著連那些活著時潛能不彰或欠深的鬼靈也要感佩,從而能夠成就一件輾轉醱酵真善美的文化偉業(周慶華,2009:53)。
上面這一解,使得才會/神護的關係可以順理成章的建立起來,而藝術原有或應有的雙重保障(天才/天佑)也終於有了著落。因此,在漢武帝時代曾發生過的一件公案(帶美類藝術)「孝武帝時,聚會占家問之:『某日可取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叢辰家曰大凶,曆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辯訟不決。以狀聞,制曰:『避諸死忌,以五行為主。』」(司馬遷,1979:3222)便不難援例而得以了解:就是五行家已先比對過兩造的五行無相尅情況,才研判娶婦一事可成(乃「天作之合」);而漢武帝也相信(或想賭一把)既然是「天作之合」,那神靈也當要護佑二人的美事到底才有理則(何況還有會看天象的天人家/太一家在旁邊附和可以壯膽),所以就放心付諸行動了。這不就是那雙重保障說的再現麼!
可見與生俱來的才藝已經關連靈異,而該才藝能持續不輟或轉生光華,更是離不開靈異(神靈從旁愛惜護佑或別為挹注),寖假二者乃合而為一難分彼此了。於是「藝術從此得關連靈異」一理就具有必然性,不再是機遇或偶現一類的泛泛意見(如前引眾著作中常會流露的)所能輕易取代。
|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靈異藝術學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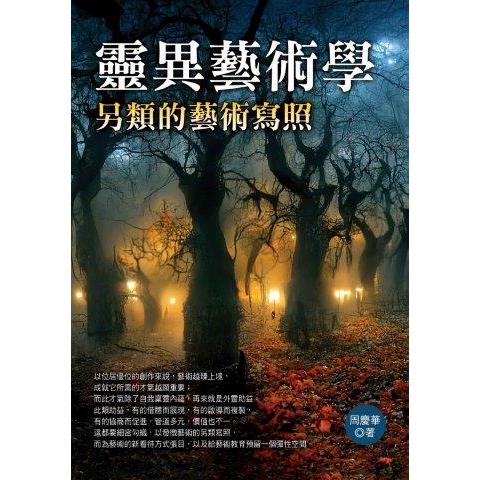 |
$ 196 ~ 252 | 靈異藝術學【金石堂、博客來熱銷】
作者:周慶華 出版社:華志文化事業 出版日期:2023-01-04  共 6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6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靈異藝術學
靈異藝術學
以位居優位的創作來說,藝術越臻上境,成就它所需的才氣越顯重要;而此才氣除了自我稟靈內蘊,再來就是外靈助益。
此類助益,有的借體而展現,有的啟導而複製,有的協商而促進,管道多元,價值也不一。這都要細密勾織,以發微藝術的另類寫照,而為藝術的新看待方式張目,以及給藝術教育預留一個彈性空間。
筆者等論綱及其細目設定並據為暢論的,無疑能自成一門可名為「靈異藝術學」的新學科(既是科別又能當書名)。規模已具,理解藝術又增多一殊異途徑。
有此一殊異途徑,便能進一步從所貞定的「跨域差異的察覺」/「相仿效或相涵化的可能性辨識」/「美感益世的從新出發」等文化意義而繁衍出「靈異藝術學成立後的學科調整」/「靈異藝術學伸展時的兩界互動蘄嚮」等新希望,一門新學科終於嫣然底定。
此一神祕機能原穿透力甚強,卻一向被世人所漠視,導致所有對藝術生發演變的理解難以透徹入微。
如今從新開談,引入靈異變項,察考它的來龍去脈,並且評估它的成效及其所蘊涵的文化意義,為一門新學科的成立盡特大心力。
作者簡介:
周慶華
文學博士,曾任臺東大學語文教育研究所所長,現已退休。
出版有《佛學新視野》、《走訪哲學後花園》、《文化治療》,《後宗教學》、《死亡學》、《靈異學》、《後佛學》、《生態災難與靈療》、《身體權力學》、《反全球化的新語境》、《新時代的宗教》等六十多種。
章節試閱
序:另類的藝術寫照
從來藝術都以一高華姿態面世,予人特多審美享受,為世上知識經驗/道德經驗以外第三大經驗。此經驗著重在趣味的營造和炫異,事涉美醜價值的估定取捨,已跟前二者所關連的真假/善惡市值競逐有日,甚至在被恆久需求性上還要略勝一籌。
然而,由此一藝術總綰的審美經驗,卻因世人僅當它但存活於現實中而鮮知別有來自靈界相關機制的控勒,致使藝術從產出到接受一直為意外變項所左右,無法給予有效的觀照解決或填補罅漏,徒然造成一門藝術學「鷹視缺位」的莫大遺憾!
以位居優位的創作(產出)來說,藝術越臻上境,成...
從來藝術都以一高華姿態面世,予人特多審美享受,為世上知識經驗/道德經驗以外第三大經驗。此經驗著重在趣味的營造和炫異,事涉美醜價值的估定取捨,已跟前二者所關連的真假/善惡市值競逐有日,甚至在被恆久需求性上還要略勝一籌。
然而,由此一藝術總綰的審美經驗,卻因世人僅當它但存活於現實中而鮮知別有來自靈界相關機制的控勒,致使藝術從產出到接受一直為意外變項所左右,無法給予有效的觀照解決或填補罅漏,徒然造成一門藝術學「鷹視缺位」的莫大遺憾!
以位居優位的創作(產出)來說,藝術越臻上境,成...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後全球化思潮叢書企畫/i
序:另類的藝術寫照/v
第一章 新學科的召喚/1
第一節 繆斯出場見證後/1
第二節 藝術從此得關連靈異/6
第三節 靈異藝術學跟著要立案/14
第二章 概念界定/19
第一節 靈異/19
第二節 靈異藝術/31
第三節 靈異藝術學/43
第三章 靈異藝術成學的緣起/57
第一節 理論和現實的需求/57
第二節 權力欲望的發用和文化理想藉以寄存/64
第三節 反向立說姑予期待實現/69
第四章 靈異藝術可能的分布/79
第一節 夢感類/79
第二節 醒時被借體類/85
第三節 通靈成就類/93
第四節...
序:另類的藝術寫照/v
第一章 新學科的召喚/1
第一節 繆斯出場見證後/1
第二節 藝術從此得關連靈異/6
第三節 靈異藝術學跟著要立案/14
第二章 概念界定/19
第一節 靈異/19
第二節 靈異藝術/31
第三節 靈異藝術學/43
第三章 靈異藝術成學的緣起/57
第一節 理論和現實的需求/57
第二節 權力欲望的發用和文化理想藉以寄存/64
第三節 反向立說姑予期待實現/69
第四章 靈異藝術可能的分布/79
第一節 夢感類/79
第二節 醒時被借體類/85
第三節 通靈成就類/93
第四節...
顯示全部內容
|











![114年一書搞定機械力學概要[國民營事業] 114年一書搞定機械力學概要[國民營事業]](https://media.taaze.tw/showLargeImage.html?sc=14100121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