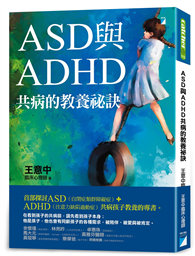陰陽眼、通靈人、特異功能,不管怎麼稱呼她,結果都一樣,
哈珀總是能準確找到屍體,如果離得夠近,甚至能聽得見屍體「說話」
勇奪紐約時報暢銷榜TOP10、亞馬遜銷售恐怖小說類TOP3
全美熱賣超過50萬本,版權售出十餘國,佳評如潮,好讀推薦!
一般人被強烈的閃電擊中,多半非死即傷,但哈珀.康納莉與眾不同,
她變得可以感應死亡、靠近死亡,甚至是體驗死亡……
史上最特殊的「私家偵探」哈珀.康納莉,擅長的不是破解謀殺案,而是尋找屍體,以及感應死者生前最後一刻的所有情境。哈珀在十五歲時慘遭雷擊後,便擁有可以「聽取」死亡的特殊能力,她與英俊瀟灑、處處留情的繼兄托利佛以尋找屍體維生。雷擊讓她擁有異能,但同時也帶走了她面對閃電的勇氣。幸好有托利佛一路陪伴,讓她能安然度過每個雷雨夜。
哈珀與托利佛為了一個年輕女孩失蹤案件,來到充滿古典風情的鄉下觀光小鎮薩尼,孰料完成委託後竟被捲入一連串的謀殺疑雲當中,還被困在表面祥和靜謐、實則暗潮洶湧的薩尼鎮無法抽身,而且多次遭遇致命攻擊,甚至連托利佛都無端被送進監牢裡。
看來除了火速解決纏身的瑣事、撥空與英俊的小鎮警官談談戀愛之外,哈珀還得趕緊運用「天賦」,幫托利佛重獲自由,並讓自己從一團泥淖當中脫身……
作者簡介
莎蓮.哈里斯(Charlaine Harris)
1951年11月25日生於埃及,早期創作類型為推理、懸疑、驚悚、玄怪,後於曼菲斯的羅德大學進修,跨足大眾文學並獲獎無數,成功跨足羅曼史、推理、驚悚、犯罪及超自然小說,成為第四位進入美國Amazon百萬俱樂部的成員。對此,哈珀.康納莉系列在美國熱賣功不可沒。而南方吸血鬼系列(A Southern Vampire Novel)則是她至今銷售最快速之著作。目前系列銷售全美已突破一千萬冊,創下全系列同時登上紐約時報排行榜的空前紀錄。
工作時喜歡聽音樂,電影「臥虎藏龍」原聲帶是她的最愛之一。
作者官網:www.charlaineharris.com
譯者簡介
非語
政大西洋語文學系畢業,專職翻譯。
譯有《阿根廷,別為我哭泣!》、《祕密沒說完的事》(方智出版社);《愛與規範不衝突》(遠流出版社);《天氣改變了歷史》(究竟出版社);《禁忌界線》、《那樣的美麗》、《你不在以後》(臺灣商務出版社);《失蹤》、《簡單放下,天天度假》(高寶出版社)等。



 共
共  2012/12/18
2012/12/18 2012/06/05
2012/06/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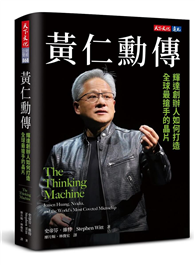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https://media.taaze.tw/showLargeImage.html?sc=111006978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