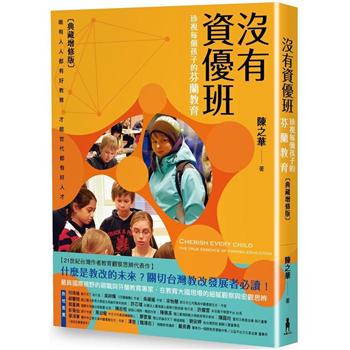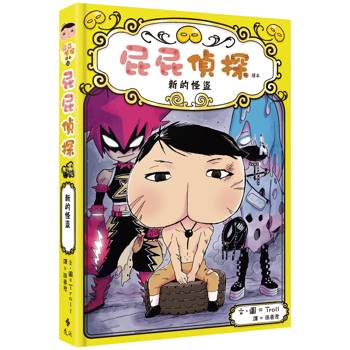「文學的歷史本身已比一般歷史更富詮釋空間,口述歷史突出的主觀性也許更添爭議,然而眾『說』紛紜,互相比對參照下所呈現的複雜性,也許更貼近文學歷史的本質。追尋歷史的結果,每每都指向當下眼前,這一系列的訪談,期望在未來的歷史裡更見意義。」──盧瑋鑾、熊志琴
「香港文化眾聲道」系列的誕生,緣於二〇〇二年展開的「口述歷史:香港文學及文化」研究計劃。計劃由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文學研究中心主持,盧瑋鑾教授和熊志琴博士投入十多年時間,向數十位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文壇及文化界前輩進行口述歷史訪問,並結集成書,繼二〇一四年的第一冊後,今年推出第二冊。訪問內容全面、詳盡,受訪者的創作歷程、參與的文學活動、對同時期作家的評價、對所在組織的了解、對時局和政治的看法等都是記錄的範疇。記錄者廣泛蒐集並保存第一手資料,為讀者完整、真實地呈現數十年來香港的文化、政治與歷史的互動。這些原始材料經記錄者嚴謹整理和查證,並補充大量注釋和附錄,有助填補文獻記錄的空白,為學者和研究者提供珍貴資料。一般讀者也能從書中讀出趣味,通過記錄者與受訪者的一問一答,進入五、六十年代的香港社會,感受當時的文化氛圍。
《香港文化眾聲道2》受訪者包括羊城、羅卡、吳平、陸離、張浚華、陳任、古兆申、黃子程、陳炳藻、金炳興。
|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香港文化眾聲道(2)的圖書 |
 |
$ 600 ~ 684 | 香港文化眾聲道(2)
作者:盧瑋鑾、熊志琴 出版社:三聯書店(香港)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7-04-07 語言:繁體書  共 4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4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文化
 文化是由古羅馬哲學家西塞羅首次使用拉丁文「cultura animi」定義,原意是「靈魂的培養」,由此衍生為生物在其發展過程中積累起跟自身生活相關的知識或經驗,使其適應自然或周圍的環境,是一群共同生活在相同自然環境及經濟生產方式所形成的一種約定俗成潛意識的外在表現。
文化是由古羅馬哲學家西塞羅首次使用拉丁文「cultura animi」定義,原意是「靈魂的培養」,由此衍生為生物在其發展過程中積累起跟自身生活相關的知識或經驗,使其適應自然或周圍的環境,是一群共同生活在相同自然環境及經濟生產方式所形成的一種約定俗成潛意識的外在表現。 對「文化」有各種各樣的定義,其中之一的意義是「相互通過學習人類思想與行為的精華來達到完美」;廣義的文化包括文字、語言、建築、飲食、工具、技能、技術、知識、習俗、藝術等。大致上可以用一個民族的生活形式來指稱它的文化。
在考古學上「文化」則指同一歷史時期的遺蹟、遺物的綜合體。同樣的工具、用具、製造技術等是同一種文化的特徵。文化和文明有時在用法上混淆不清。
現今中文裡文化一詞的意思,借自於日文和製漢語中「文化」之義,其所表達的概念、集合與意涵和華夏古籍的原義相差甚遠,應避免望文生義。
網際網路成熟的發展使原先相對疏離的個人或組織可以很容易經由社群網站,建立許多新的基於價值觀、理想、觀念、商業、友誼、血緣等等非常錯綜複雜的聯繫,由此發展出特定社群意識的網路文化,這種網路文化聯繫瞬間的爆發力,對特定議題及選舉所造成的影響已經是新興不可忽視的力量。
![]() 維基百科
維基百科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香港文化眾聲道 2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盧瑋鑾(1939-)
原籍廣東番禺,出生於香港。筆名小思、明川。1964年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中文系畢業,獲文學士銜後任中學教師多年。1973年赴日本,任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研究員。1978年任香港大學中文系助教。1979年任教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1995年起任教授。2002年7月退休,任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文學研究中心主任,2008年轉任香港文學研究中心顧問。著有《香港文蹤──內地作家南來及其文化活動》、《香港家書》、《一生承教》、《一瓦之緣》等。
熊志琴
香港中文大學哲學博士,現任教於香港公開大學,兼任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文學研究中心名譽副研究員。編有《文學與影像比讀》(與盧瑋鑾合編)、《經紀眼界──經紀拉系列選》、《異鄉猛步──司明專欄選》;編校《淪陷時期香港文學作品選:葉靈鳳、戴望舒合集》、《淪陷時期香港文學資料選》;另有口述歷史訪問紀錄《雙程路:中西文化的體驗與思考(1963-2003)──古兆申訪談錄》(與盧瑋鑾聯合編著)、《結緣兩地──台港文壇瑣憶》(鄭樹森訪談錄)等。
盧瑋鑾(1939-)
原籍廣東番禺,出生於香港。筆名小思、明川。1964年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中文系畢業,獲文學士銜後任中學教師多年。1973年赴日本,任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研究員。1978年任香港大學中文系助教。1979年任教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1995年起任教授。2002年7月退休,任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文學研究中心主任,2008年轉任香港文學研究中心顧問。著有《香港文蹤──內地作家南來及其文化活動》、《香港家書》、《一生承教》、《一瓦之緣》等。
熊志琴
香港中文大學哲學博士,現任教於香港公開大學,兼任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文學研究中心名譽副研究員。編有《文學與影像比讀》(與盧瑋鑾合編)、《經紀眼界──經紀拉系列選》、《異鄉猛步──司明專欄選》;編校《淪陷時期香港文學作品選:葉靈鳳、戴望舒合集》、《淪陷時期香港文學資料選》;另有口述歷史訪問紀錄《雙程路:中西文化的體驗與思考(1963-2003)──古兆申訪談錄》(與盧瑋鑾聯合編著)、《結緣兩地──台港文壇瑣憶》(鄭樹森訪談錄)等。
目錄
前言
訪問記錄
——羊城
——羅卡
——吳平
——陸離
——張浚華
——陳任
——古兆申(附:古兆申、黃子程對談)
——陳炳藻
——金炳興
附錄
——本冊相關報刊資料
——後記
——人名索引
——鳴謝
訪問記錄
——羊城
——羅卡
——吳平
——陸離
——張浚華
——陳任
——古兆申(附:古兆申、黃子程對談)
——陳炳藻
——金炳興
附錄
——本冊相關報刊資料
——後記
——人名索引
——鳴謝
序
前言
這一系列訪談緣起於「口述歷史:香港文學及文化」研究計劃。此計劃從二○○二年開始,是當時剛剛成立的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文學研究中心的主要工作項目。及後我們先後放下中心的實際職務,但計劃並沒有因此結束,我們繼續進行訪談、整理記錄,至今已逾十五年。
以口述史的方式紀錄前輩對香港文學發展的種種回憶,意義不僅在於提供歷史事實,更在於呈現歷史參與者的個人理解及感受,重新喚起被遺忘的人物及細節,從而開啟不同面向的研究角度、引發深入的專題研究。我們立意借鑑口述歷史的研究方法,期望在採集史料的同時,也獲得某種研究成果。可是正統的口述歷史研究,需要投入龐大的人力物力,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台灣中央研究院都以特定部門和專業團隊進行工作,我們的能力自然無法比擬。不過,儘管力量微薄,但因著其他史料整理工作的經驗,以及對受訪前輩的尊敬,我們從未敢對訪問工作掉以輕心。
許多香港作家長期以來發表作品眾多,但結集出版成書的甚少,甚至未曾結集出版,因此也從未進入研究者的視野,作品的內涵被忽略,而文學寄生於報刊所揭示的作家與文壇、社會的互動關係也被遺忘─這些在一般論述所錯失的人與事,正是我們所要尋訪的。
訪談之前的準備工作,大多從翻檢昔日報刊開始,我們盡量搜集和了解與受訪者相關的材料,然後擬定訪談大綱。部份受訪者並不以「寫作」作為文學實踐,而以編輯、文化機構負責人、政策執行者等身份在文化界發揮影響力,為訪談而準備的材料搜集範圍更廣,搜集起來也更不容易,但我們也希望通過訪談,呈現他們在香港文學發展歷程中較隱性而卻極重要的位置。至於訪談名單的擬定,受訪者的重要性固然是前提,但絕非唯一的考慮,實際訪談名單的敲定還牽涉時機、地域、人脈等因素。因此,並未在本系列出現的前輩,絕不代表地位「次要」,他們與部份截至出版而訪談記錄仍未能達成授權共識的受訪者,我們都期待將來續有訪問和跟進出版的機會。
認真而嚴肅的口述歷史訪談,往往都不能限於一、兩次會面,礙於種種條件限制,我們無法對每一位受訪者都進行多次漫長訪問,但都盡可能因應不同情況作面談或書面的追問、續訪。訪談整理成文字稿,從初稿到定稿的審訂過程中,受訪者或直接以文字補充,或提供口頭、文獻資料作參考佐證,充實訪談內容,凡受訪者所補充的按語,均以()標示。另一方面,我們也向相關人士查詢,翻查報刊、書信、文件、檔案等文獻資料,所得資料以附注形式作補充或以﹝﹞標示。報刊或機構簡稱首次出現也以﹝﹞交代全名,以後從略,每篇均獨立處理。訪談定稿得到受訪者授權始公開發表,出版前更添上人物小傳,增加「本冊相關報刊資料」及「人名索引」等附錄,輔助闡釋之外,更期望可藉此呈現較廣闊的歷史圖景。出版因篇幅所限,受訪者一些與文學、文化工作不直接相關的經歷不得不省略,內容過於重複之處也有所刪節,但為求盡量保留訪談原貌,文稿一般不會按訪談內容重組。一切改動,均在已得到授權的定稿上編輯。
無疑,口述歷史作為研究方法,取得豐碩成果的同時,也備受質疑。口述歷史的可靠性,無可否認也不能避免因受訪者的年紀、身體狀況、記憶力、情緒、個人主觀等等因素影響,也受訪問者與受訪者關係、說話時機是否適合等客觀條件左右。訪談準備再充分、資料查證再嚴謹,似乎都無法彌補口述歷史的某些先天缺陷。然而,受訪者如何理解、選擇、詮釋、以至「改編」歷史記憶,其實正好呈現了歷史事件中「個人」的角度,填補了客觀資料之不足。口述歷史的主觀性最受詰難,但這也正是口述歷史最精彩可貴之處。何況每一種研究方法、每一種材料都有本身的限制,能否發揮口述歷史的長處,關鍵還是在於讀者、研究者的閱讀角度與研究態度。
訪談計劃開展以來得到不少前輩及同道支持,首先感謝多位受訪者付出心力、時間和信任,其中好幾位在接受訪談後離世,未能讓他們及見訪談出版,我們至為歉疚。多位受訪者在接受訪問之外,還授權讓所負責之刊物全文上網,並捐贈大批珍貴書刊以及富歷史價值之手稿、信件、相片等文獻資料,讓後學得以從這些第一手資料認識歷史,所有捐贈均已移送香港中文大學大學圖書館系統。此外,訪談工作得以開展,不同機關和朋友都在行政上、經濟上提供了支援,謹此鳴謝(名單詳見書末)。
唐德剛教授曾經指出,哥倫比亞大學的中國口述歷史學部「譽滿全球,而謗亦隨之」,十多年來真正完成的只有一部中英雙語的《李宗仁回憶錄》和只有英語的《顧維鈞回憶錄》,其餘多位民國要人的口述歷史雖「工作經年,最後都是半途而廢」,可見口述歷史工作之困難(參唐德剛〈張學良自述的是是非非〉)。我們的研究規模與實力自不可與「哥大」同日而語,但勉力為之,也悉力以赴,訪談未及盡善之處,敬請各方指正。文學的歷史本身已比一般歷史更富詮釋空間,口述歷史突出的主觀性也許更添爭議,然而眾「說」紛紜,互相比對參照下所呈現的複雜性,亦也許更貼近文學歷史的本質。追尋歷史的結果,每每都指向當下眼前,這一系列的訪談,期望在來未的歷史裡更見意義。
這一系列訪談緣起於「口述歷史:香港文學及文化」研究計劃。此計劃從二○○二年開始,是當時剛剛成立的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文學研究中心的主要工作項目。及後我們先後放下中心的實際職務,但計劃並沒有因此結束,我們繼續進行訪談、整理記錄,至今已逾十五年。
以口述史的方式紀錄前輩對香港文學發展的種種回憶,意義不僅在於提供歷史事實,更在於呈現歷史參與者的個人理解及感受,重新喚起被遺忘的人物及細節,從而開啟不同面向的研究角度、引發深入的專題研究。我們立意借鑑口述歷史的研究方法,期望在採集史料的同時,也獲得某種研究成果。可是正統的口述歷史研究,需要投入龐大的人力物力,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台灣中央研究院都以特定部門和專業團隊進行工作,我們的能力自然無法比擬。不過,儘管力量微薄,但因著其他史料整理工作的經驗,以及對受訪前輩的尊敬,我們從未敢對訪問工作掉以輕心。
許多香港作家長期以來發表作品眾多,但結集出版成書的甚少,甚至未曾結集出版,因此也從未進入研究者的視野,作品的內涵被忽略,而文學寄生於報刊所揭示的作家與文壇、社會的互動關係也被遺忘─這些在一般論述所錯失的人與事,正是我們所要尋訪的。
訪談之前的準備工作,大多從翻檢昔日報刊開始,我們盡量搜集和了解與受訪者相關的材料,然後擬定訪談大綱。部份受訪者並不以「寫作」作為文學實踐,而以編輯、文化機構負責人、政策執行者等身份在文化界發揮影響力,為訪談而準備的材料搜集範圍更廣,搜集起來也更不容易,但我們也希望通過訪談,呈現他們在香港文學發展歷程中較隱性而卻極重要的位置。至於訪談名單的擬定,受訪者的重要性固然是前提,但絕非唯一的考慮,實際訪談名單的敲定還牽涉時機、地域、人脈等因素。因此,並未在本系列出現的前輩,絕不代表地位「次要」,他們與部份截至出版而訪談記錄仍未能達成授權共識的受訪者,我們都期待將來續有訪問和跟進出版的機會。
認真而嚴肅的口述歷史訪談,往往都不能限於一、兩次會面,礙於種種條件限制,我們無法對每一位受訪者都進行多次漫長訪問,但都盡可能因應不同情況作面談或書面的追問、續訪。訪談整理成文字稿,從初稿到定稿的審訂過程中,受訪者或直接以文字補充,或提供口頭、文獻資料作參考佐證,充實訪談內容,凡受訪者所補充的按語,均以()標示。另一方面,我們也向相關人士查詢,翻查報刊、書信、文件、檔案等文獻資料,所得資料以附注形式作補充或以﹝﹞標示。報刊或機構簡稱首次出現也以﹝﹞交代全名,以後從略,每篇均獨立處理。訪談定稿得到受訪者授權始公開發表,出版前更添上人物小傳,增加「本冊相關報刊資料」及「人名索引」等附錄,輔助闡釋之外,更期望可藉此呈現較廣闊的歷史圖景。出版因篇幅所限,受訪者一些與文學、文化工作不直接相關的經歷不得不省略,內容過於重複之處也有所刪節,但為求盡量保留訪談原貌,文稿一般不會按訪談內容重組。一切改動,均在已得到授權的定稿上編輯。
無疑,口述歷史作為研究方法,取得豐碩成果的同時,也備受質疑。口述歷史的可靠性,無可否認也不能避免因受訪者的年紀、身體狀況、記憶力、情緒、個人主觀等等因素影響,也受訪問者與受訪者關係、說話時機是否適合等客觀條件左右。訪談準備再充分、資料查證再嚴謹,似乎都無法彌補口述歷史的某些先天缺陷。然而,受訪者如何理解、選擇、詮釋、以至「改編」歷史記憶,其實正好呈現了歷史事件中「個人」的角度,填補了客觀資料之不足。口述歷史的主觀性最受詰難,但這也正是口述歷史最精彩可貴之處。何況每一種研究方法、每一種材料都有本身的限制,能否發揮口述歷史的長處,關鍵還是在於讀者、研究者的閱讀角度與研究態度。
訪談計劃開展以來得到不少前輩及同道支持,首先感謝多位受訪者付出心力、時間和信任,其中好幾位在接受訪談後離世,未能讓他們及見訪談出版,我們至為歉疚。多位受訪者在接受訪問之外,還授權讓所負責之刊物全文上網,並捐贈大批珍貴書刊以及富歷史價值之手稿、信件、相片等文獻資料,讓後學得以從這些第一手資料認識歷史,所有捐贈均已移送香港中文大學大學圖書館系統。此外,訪談工作得以開展,不同機關和朋友都在行政上、經濟上提供了支援,謹此鳴謝(名單詳見書末)。
唐德剛教授曾經指出,哥倫比亞大學的中國口述歷史學部「譽滿全球,而謗亦隨之」,十多年來真正完成的只有一部中英雙語的《李宗仁回憶錄》和只有英語的《顧維鈞回憶錄》,其餘多位民國要人的口述歷史雖「工作經年,最後都是半途而廢」,可見口述歷史工作之困難(參唐德剛〈張學良自述的是是非非〉)。我們的研究規模與實力自不可與「哥大」同日而語,但勉力為之,也悉力以赴,訪談未及盡善之處,敬請各方指正。文學的歷史本身已比一般歷史更富詮釋空間,口述歷史突出的主觀性也許更添爭議,然而眾「說」紛紜,互相比對參照下所呈現的複雜性,亦也許更貼近文學歷史的本質。追尋歷史的結果,每每都指向當下眼前,這一系列的訪談,期望在來未的歷史裡更見意義。
盧瑋鑾、熊志琴
二○一四年五月初稿
二○一七年一月修訂
二○一四年五月初稿
二○一七年一月修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