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被罩在一片玻璃桌墊下,天空在裡面,深海也在裡面。
──〈離島的離島〉
他們找尋第二故鄉
他們挖掘土底的月亮
他們退而求其「刺」
掛了各科病號
穿過各種顏色
在凝固前
將刺排成圓形
冉冉升起成一種語言
豔陽高照,世界一片膠著,經濟衰退、溫室熱融,偏居一隅的他們在做什麼,能做什麼?
只有一個朋友的川金,總是幫助別人脫身自己卻困在那裡。意外繼承了家園和田產,卻做各種苦活,應對繁瑣人情,他們說她像駱駝,天塌下來有她頂著。
飄洋過海經營民宿之前,他們的婚姻早已判死。要攤牌,還是「先去晃一晃?」他們選擇後者,一個帶著海邊的祕密調適返鄉心情,一個積極展開新生活,直到女兒也有了祕密。
阿燦和燦嫂,鄉里警告要保持距離的人。兩人也從都市回到島上多年,長得好看,到處打雜、寄居,後頭黏著很多閒話。但阿燦卻有一種無中生有的歡喜,能讓荒地生出許多野果來。
翻新《流水帳》的溫柔淘洗,遷蕩《雲山》的雋永迴旋
她以水流雲行之筆,寫活現代人的迷途與拋荒
她為那些熟稔親切卻未曾真正被記住的人物風景,留下心靈停駐的痕跡。音聲色感無一不是鄉愁,卻無法真正歸返。話中有話,景中有景,慨嘆藏在不動聲色的應答中,節制而犀利,一針一線細膩勾埋,將綿密錯綜的故鄉生活細節,重新剪綴成嶄新的五彩斑斕,闢拓無人打理的嶼徑,凝縮月移水色浮擾心頭千種滋味,人情小事自然有秩地散落在適可而止的天地間,餘留如詩的韻致。
一趟夢遊般的返鄉之旅,他們與某島,某人。
以單數和偶數兩組人物故事交織成一條人生的髮辮、返鄉的繩索。他們努力經營著一種平靜的「有機」生活,安定中持續飄移,晃蕩、出走、回頭望;返鄉人與故鄉人的關係,既緊張又鬆弛,維持著荒謬的和諧。
細緻靈動的文字,巧妙疊砌故鄉繽紛的地景色系:烏趖趖、烏罵罵、白蒼蒼、白泡泡、紅吱吱、青泠泠、青恂恂、黃兮兮、黃錦錦......
作者簡介:
陳淑瑤
來自澎湖,現居台北,她在書裡描寫迷濛的木麻黃。已出版《雲山》、《潮本》等作品。
章節試閱
第三章 骨科
軍醫院來了一個三十多歲的骨科醫生,人好好,風評在鄉里傳開,在地資深的骨科主任一比就完蛋了,大家「都馬」改掛那個年輕醫生,連準備要飛去大城都動手術的人「馬都」不去了;可惜他不是在地的,總有一天會調走,隨時「馬都」會調走,還在考慮換人工關節的人不敢再猶豫了,換好一腳另一腳不敢再拖了……跑醫院的中年兒女把握機會口耳相傳。
陳淑在她阿母將換第二隻腳的膝關節前來拜託川金,她用盡說詞無法說動川金,整張臉趴在桌上磨擦,終於講出不能夠獨自看護阿母的真正原因,她好怕處理排泄物,上次她被嚇到了,趕緊戴口罩穿手套時,情況整個失控。她雖然生過兩個孩子,但大部分是婆婆在照料,且大人和小孩是不一樣的。
川金沒答應。陳淑拖著腳步走了,她一回來就四處去做傳銷,累癱了。川金將她忘記帶走的墨鏡和藥罐子送到她家去,她已躺上床,全身覆滿她忙著銷售的負離子產品,帽子、眼罩、圍巾、護腕、護肘、護膝、衛生衣、衛生褲、手套、襪子……乍看好像受了重傷。看來她真的非常之相信這層東西具有再生能力,可預防並且醫治任何疾病,就像嫦娥相信靈丹。
這些有的像膚色毛呢,有的像米白紗布的東西,到底怎麼加進陳淑說的負離子,跟加持一樣的玄。她送過幾樣給川金,都是她用零碎的珍貴負離子面料做成的,聽說是踩她婆婆的裁縫車車製的,一只內襯負離子的囗罩,一條圍脖子的小方巾,兩片胸罩襯墊,一條護腰,川金全塞進枕頭套貼頭殼那一面。
她小時候很怕鬼,現在還怕?睡覺留一盞燈,側躺弓腳,像隻大白兔,只差屁股後面一團兔尾巴,潔白的兔尾巴,不是髒掉的。這幅孤寂睡兔的景象讓川金決定和她去醫院。
在醫院那些天,陳淑照樣全身貼裹負離子,那成了她的另一層皮膚,外面披一件水藍印花罩袍,像在海灘度假,四處走動,結識朋友。有個護士小姐鼻子很挺腳很細很長,像一隻白腳鷺鷥,陳淑和她聊她的白長褲。她說擔心有東西或者是風鑽進去,褲管越改越窄,護理長休假時她乾脆穿白褲襪上班,在走廊不知不覺就踮著腳尖好像跳芭蕾,惹得同事伸手打她屁股,還笑她沒屁股。陳淑皺眉說應該趁年輕改善體質長點肉,試試看加一層像肌膚一樣的負離子……。
阿母說這個叫阿芝的護士小姐是我們村的,她爸你們可能不認識,她阿公你們就知道,牽一台自己組的牛車,四個輪子四個大小,好好一隻牛兒被那台車弄得身軀歪一邊,腳跛跛,行路慢躊躇,一條路都給他們占去……。
阿公的行徑像蠢蛋,陳淑引導阿母言歸正傳,喔人家她是護校畢業的,有牌的護士……陳淑拿出一件負離子質料的小可愛送人家,摸著她冰冷的手說:護士當久了從裡到外都變成冰棒。
等待病患手術的時間,川金全程坐在開刀房外的椅子上,她想學陳淑那樣找話跟陌生人說,也試想回答他們可能提出的問題,可是沒有人看見她,想跟她聊天。
好幾個人拿鐵鎚還什麼的一直在那敲,聽那聲活欲驚死。阿母講起開刀房裡的情形,跟上次一模一樣一字不差,簡直是鐵匠直接在她身上打造一隻新腳。汰換骨骼的膝蓋包紮成一大球,血層層滲透紗布,痛苦的逗點使痛苦加劇,可能是上次預支了,這次沒痛成那樣,鮮血在白晝的天空凝結成一朵小紅霞。
早晨護士帶來若有似無半粒軟便的藥丸,她們心照不宣不打算用它。心裡雖然嚴陣以待,陳淑依舊東逛逛西轉轉,回病房瞧一瞧時,只聽見川金在簾帳內叫:出去!你出去!她所擔憂推卸的事便搞定了。
住院期間陳淑與一位探病家屬因認錯人而立在電梯前面倚著漆黑的玻璃帷幕長談,站到腳都僵了,又到樓上佛室在法師的墨寶下把故事說下去。那女人問她為什麼穿一身木乃伊,不聽她講解,主動要求試用,過去藥物最多僅能讓她睡四個鐘頭,一輩子比人家少睡一半,罩上軟軟的負離子,像搖籃托著,竟然連續睡八個鐘頭,眼睛變得炯炯有神!她以懺悔的口吻向陳淑招認,我把你看成一個已經死了很久的同學,電梯門一開看到她,我腳都軟了,她是我記憶裡第一個不是老了才死掉的人,其實以前我不怎麼喜歡她……。
回去之後陳淑渲染整個過程的順利,包括她的業績和川金那令人高枕無憂的執行能力,置換人工膝關節的阿母第三日就下床了,五天半就出院了,比她自己看護提早兩天。將此效率歸功於一個古怪好友的幫助,比親力親為更令人羨慕。她塞給川金一萬塊紅包誇口成兩萬。
沒有銷售的意思,但那套歸咎與歸功的思考和說話模式再度奏效。有一旅外的同鄉友人打川金的主意,要陳淑介紹,錢可以再加,快出院時她才飛回去接手,陳淑說就怕有錢也請不到。沒想到川金一口答應,她一年上百日坐著矮凳論斤秤兩剝牡蠣,去年還給颱風飄搖的蚵棚砸傷,不這樣賺錢不行,之前的積蓄全都投在遠方與妹妹合買的房子了。
拖了四個月陳淑才告訴友人,她那做事很有一套的兒時玩伴終於答應了,你就叫她「林小姐」,六、七天她還走得開,人家是勞心勞力的人,沒必要少跟她多話,記得掛簡醫師。
川金照料的都是七老八十的婦人,一律叫阿嬤,男性不接。她們約好了碰面了,好像機器人,一個腳遲,一個面癱,疼痛來時有血有肉有了真實感。開第一隻腳,通常先動左腳,痛到不能忍受,麻醉科醫生將止痛藥的劑量調到不能再高,川金來回奔走搬救兵取冰袋。一口家用冰箱專門冰藏各種吃健康吃快樂的食物,各個獨立成島不連接別人的品項,看別人的食糧刺激不了食慾也半飽了。上層冷凍庫冰袋交錯,她討厭掐冰袋陷入冰沙的感覺,冷眼判斷冰凍程度,堅硬的都被挑走了,剩下幾隻軟弱的被打敗的。需要好幾隻,自各個角度敷貼冰鎮脫胎換骨的腳肢,怕它腐爛。動作好像撫摸母牛乳房,她蹲身查看垂掛在床下橡皮管內尿液的活動情況,訓練病人自主排尿,等醫生一句話,明天可以出院了。
出門前幾天她開始找月亮,她想知道她不在的時候它是圓了哪塊缺了哪塊。她又回到起點,坐在開刀房外盯著房門,等待白衣天使出來叫喚:某某某的家屬,這段時間她記誦病患名字出生年月日,好幾次忘記又想起之間,她總是看見那條魚。有一回蚵寮的女人給她送來一條魚,掛在門把上,附近野貓垂涎三尺脖子伸得若長頸鹿,咬到弓曲最低點魚的脊背,膠袋屑、碎魚鱗掉滿地,破洞見骨,鮮血斑斑。
出院返家,她趕緊恢復家園面貌,時不時懷疑不是這樣不是那樣,什麼被偷偷改變了,好像不管綑幾層紗布,血硬是穿透出來。夜裡她感覺屋子像被盜的墓穴,像那些被光明正大換了骨頭卻未抽掉神經的腳頭屋。她躺在床上想著那隻潔白的大白兔好像快要睡著了。她起來尋找姪子小時候玩水那些套在手腳上的充氣塑膠,他們這裡藏那裡放以為明年夏天還用得著。她用它們來做冰袋,甚至將一個非常小的游泳圈灌水,扭成「8」字形塞入冷凍庫。她自製的冰袋怕護士發現,包了毛巾撐墊在膝彎下,確定那像北極熊一身白的女人暫時不會進來,才讓它們爬上膝頭,一床冰山。
陳淑適時來電探知她的感受,體重輕狀況好又不囉嗦的患者,家屬也不囉嗦者,第二肢九折優惠。有的則藉口推辭受理第二肢,陳淑拿捏定奪。她的底線就是川金的底線,她知道如何確保她倆的價值和友誼的價值,目標是一雙金筷子,不是折得斷的木筷。
川金違背了所有原則,接下一條她抬過最笨重的腿,照護左腳時搞得一塌糊塗,前功盡棄她跑去站在體重機上頭面壁嘔氣,那指針不住地搖晃抖動,路過的護士喊:那台壞掉了啦!不只這樣,阿嬤話多如牛毛,來訪親朋沒完沒了,好像蒼蠅來到肉砧上。但她答應了。陳淑想要求病房升級,她拒絕。多話的人不能讓她住單人房,雙人房也不要,三人房最合適,有一種制衡。行前預先補充睡眠保留體力,陳淑寄來包裹,有B群、椰棗、腰果、薑糖、蔓越莓,小包裝的葡萄原汁。
三床都是庄腳人,庄腳人生病拖著泥土駐院,軍醫院裡多的是這種人,市區病患與他們共處一室,感覺在地的醫療品質永遠提升不了,有能力去到大都市,做一名遠方來的鄉下人,雖然落寞倒也心甘情願。多年前川金跟工廠請假在大醫院裡照顧切除子宮肌瘤的姑姑,姑姑不許川金說出她來自何方,且告訴隔壁床的太太,她買房子給兩個姪女住。
中間的病床躺著一個無病呻吟的婦人,留院查明病因,終如醫生猜測在她背上找到恙蟲叮咬的一個點,她好不服氣要護士拍給她看,明明最近都在幫孫媳婦做月子,根本沒下田,掃墓也沒去。川金壓根忘了阿爸臨去時交代,若有疲倦人不爽快,頭先要想到是被蟲咬到,不能當作感冒。
川金拉開舊衣服兩隻長袖子鋪填躺椅與牆壁間的縫隙,牆壁拿毛巾抹過,人蜷曲在躺椅上面,額頭鼻尖抵著牆壁,溫暖那塊冰涼,背後哀聲惡氣,不知道為什麼她突然嚇一跳,身軀像一瓣筊翻落躺平,眼睛找尋那條受難的腿,腿上那團紗布像一道雪崖依然在那裡。
恙蟲害的婦人多留了兩夜方准出院,川金早在擔心與窗邊那床病人獨處了。陪病的妻子知己知彼,護士一走,便有意無意的將中間病床的簾幔拉上。兩人在門口或走廊碰見,眼神呆空,憑感覺知悉那身影,不打招呼。浴間雖有一口加蓋的大垃圾桶,那女人很有衛生道德,總是一個結又一個結的打,把丈夫的紙尿褲緊包在塑膠袋內,再拿到棄物間。川金會在她忙這事時抽身外出,一則讓她自在,一則實在受不了那死裡求生的腐臭。
川金在這裡照護行刑的腿超過十床,始終話少表情少,談一次天就記得陳淑的同村小護士也不大認得她,大家都以為她是病患的女兒。一個戴瞳孔變色放大片的俏護士看病患劇痛趨緩丟給川金一瓶乳液,說:乾成那樣!走到門口又囑咐:先熱敷一下才擦得上去!
膝頭冰敷,腳板熱敷,一截要麻木一截要柔軟。先亡離苦的左膝一道傷疤像烤焦的蚯蚓黏在上面,川金用被子將它覆蓋起來。小腿都是斑點紋路灰白的皮膚屑,像揉著一條馬路。腳掌僵硬皸裂,被丟在草叢風吹雨打無數年的石膏模差不多是這樣。
這雙腳像植物又像礦物,不停按摩它稍有軟化的跡象。阿嬤對突如其來的伺候欲拒還迎,哼個兩聲欲說什麼又靜了會兒,終於表明便意來了。浮盪的乳液果酸刺激著呼吸道,她做好心理建設和防護措施,上場還是手忙腳亂。她結實屏住一口氣,兩手一起用力舉起了母象,然而飆了高音卻卡在那裡下不來,這時有雙手從右邊幫助頂起來,她傾了一下,趕緊再全神貫注取出一隻手來做事,一切一切等完成這事再說。
除了說聲謝謝,未能再表示什麼,兩人各自在病房兩邊接招。川金這床探病聲剛止,那頭來了病人的兒子和三個發育中的孫兒女,大家一起看電視,斷續交談,偶有笑聲。爸爸一聲令下:頭轉過去,三個孩子面壁不動。阿嬤正在為躺在床上的阿公換尿布;那些細微的動作聲就是,揚起的臭氣就是。
川金瑟縮在被子底,被子內裡是用一件好幾萬塊的負離子截切車製成,陳淑說兒子大了,單人被嫌小,但負靜電還很強,她有一台機器能測得出來,川金入院一定帶這件被子當金鐘罩。其餘身上穿的床上鋪的全是舊衣物,有阿母留下的,房東和工廠同事給的,一嶺一嶺的舊時光,穿過鋪過即丟棄在病院。
較慢躺下去那人躺下去之前熄燈。陰暗中川金一直聞見釋迦。腳步聲停止在簾外像一波直立的浪令人害怕,咕嚕發問:那個……那個……川金坐起身,床尾一襲白袍,兩隻鏡片發光,簡醫師來跟她們說一聲,明天星期五他要去離島做巡迴醫療,星期一才回來。
意思是她們明天出不了院了,川金楞在那兒。用兔子的腳跑出烏龜的時間,比起上一隻腳,這隻腳進展順利,卻得晚兩日出院。
鄰床病人呼叫妻子,間歇喂了幾聲,改喚「查某」。這裡唯獨他不是查某。躺下不久的妻子毫無反應,哪可能睡這麼死,想也知道是裝睡。川金怕再聽到更不堪的辱罵,出去窗廊邊踱步,眼睛不時望向病房門口,護士啣著一車醫療用品進去,不久又走出來。
下午川金在茶水間倒水,水流一停,誰在問誰,你都只喝白開水?她楞楞的想混過去,說話的女人又問:昨晚我是不是睡得很死?
同病房的看護妻面對面找她講話令她害怕。陳淑找人講話為推銷負離子產品,她找人聽她講故事。她今天精神較好,昨晚她吃了安眠藥強迫自己睡,不這樣她會一直醒著,像走廊那些虛冷的日光燈,沒有人按開關就不會熄滅。我不知道要怎麼睡覺,她說。去年兒子潛水出事也是在這間醫院走的,她說「也是」,故事裡沒有其他人走了,指的是床上的男人吧。他的病不斷復發,早已是尾聲了,走是遲早的事。去年冬天她開始看身心科,必須得看,藥是醫生開的,必須得吃。她一直欲找人問,她服藥之後有沒有發生什麼事,她怕發生事。她一愛睏就像填進海底一樣,她知道。又說這次住進來都不知第幾天了,不數了,離家前她在屋子後面種了一些東西,黑白亂種,想來想去也不記得種啥……這藥就像殺草劑一樣,你不要的也殺,要的也殺……這次沒有吩咐人去幫忙澆水,他們會說她多事,身顧不了命了還種菜,她有在注意,兩三日就落一點雨,都是落在日欲暗時……
川金臉扭向廊邊的玻璃窗,窗外和廊內一片枯白,再轉過來面對她不知道在歡喜什麼的臉,川金說:那你要不要回家看看?
她受寵若驚又反反覆覆做不了決定,突然眼淚掉下來,從口袋掏出鎖匙掐在掌中怕它發出聲音,說鎖匙都隨時帶著。
川金啜完那杯冒煙的熱水開始等那個女人歸來。她知道自己太心急了。她倒滾沸的水回來,待降溫再喝,而不直接取溫水,她不信任溫水,給病患的水也得熱水放溫再喝,水蒸氣在杯蓋上結滿水珠,一傾水如雨下。醫院的熱開水比外面都燙,一杯慢口喝完要十幾分鐘。她愈聚精會神接水,愈感覺背後有人,那個女人在問,你都只喝白開水?
她不知不覺加快倒水的速度,放緩喝水和憋尿的時間。病床上男人喚女人的呼求愈來愈長愈來愈弱好像橡皮筋快斷了卻不是斷在緊繃狀態。妻子仍舊沒有名字,糊裡糊塗的一個呢喃,沒有咬字。
護士來理會他,他未求助護士。川金照看的肥嬤叫她,汝好心去幫伊看一下,可憐啦,是不是欲換尿墊仔。
川金只是頻頻探察窗外。她待過窗邊的床位,陪病躺椅嵌入窗框下一道拳頭深的凹槽,人像隻蝙蝠斂掛在那。密閉的窗外有一片大大的平台,清晨起身她扭頭張望,玻璃像進了露水,不同的室內外溫差泛起不同程度的茫霧,平台上直立一支白桿子,旗桿或者是傘插,總感覺外面站著一個人。
(未完)
第三章 骨科
軍醫院來了一個三十多歲的骨科醫生,人好好,風評在鄉里傳開,在地資深的骨科主任一比就完蛋了,大家「都馬」改掛那個年輕醫生,連準備要飛去大城都動手術的人「馬都」不去了;可惜他不是在地的,總有一天會調走,隨時「馬都」會調走,還在考慮換人工關節的人不敢再猶豫了,換好一腳另一腳不敢再拖了……跑醫院的中年兒女把握機會口耳相傳。
陳淑在她阿母將換第二隻腳的膝關節前來拜託川金,她用盡說詞無法說動川金,整張臉趴在桌上磨擦,終於講出不能夠獨自看護阿母的真正原因,她好怕處理排泄物,上次她被嚇到了,趕緊戴...
目錄
第一章 揮單
第二章 怨偶
第三章 骨科
第四章 稀樹
第五章 眼科
第六章 離島的離島
第七章 魚騷
第八章 魯娜藍得
第九章 不速之樹
第十章 黑岸
第十一章 風水擇日
第一章 揮單
第二章 怨偶
第三章 骨科
第四章 稀樹
第五章 眼科
第六章 離島的離島
第七章 魚騷
第八章 魯娜藍得
第九章 不速之樹
第十章 黑岸
第十一章 風水擇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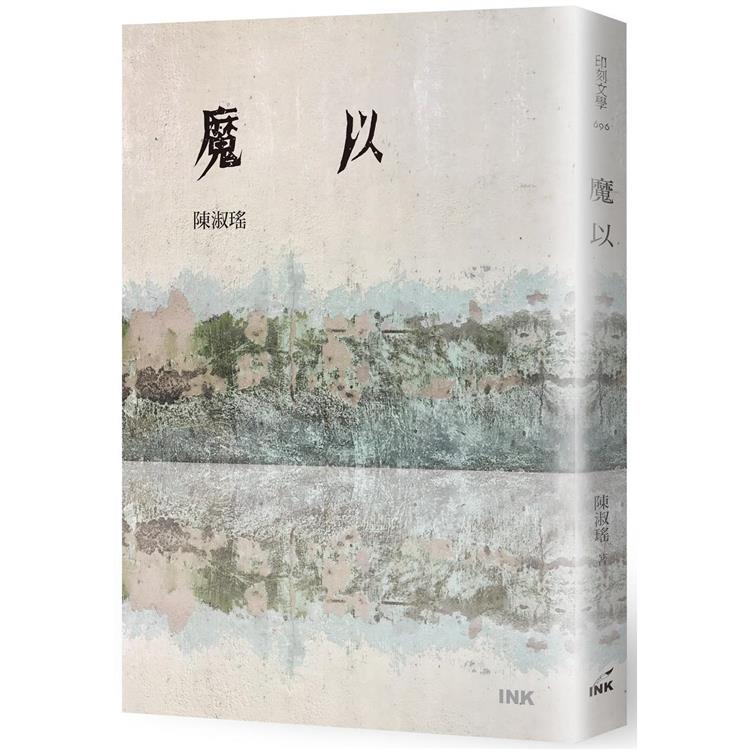
 共 7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7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