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誰,喚回了脫軌的黑劍會浪子?
一本死了都要閱讀的好書,
一段死了都要愛的禁忌戀情──
危情、深情、激情……黑劍會五部曲,致命愛情的首選!
紐約卡德威爾市的黑夜裡,戰爭仍然在吸血鬼與獵殺者間持續著。傳說,吸血鬼世界有一個神祕的組織──黑劍會,是由六個一心保護自己族群的戰士所組成,每一個黑劍會戰士都具有不同的能力,其中,布烈特之子──維蘇斯,擁有預見未來的超凡能力,每每搶在危難之前阻止悲劇的發生。而這一次,他也將捍衛族群,阻擋冷酷狡猾的掠奪者襲擊……
冷酷無情,卻又聰明絕頂的布烈特之子──維蘇斯,身上背負著一個毀滅性的詛咒與能夠預見未來的超凡能力。他在父親的戰士營裡長大,身為見習生,他受盡折磨與虐待。在成為黑劍會的一員後,他對感情不感興趣,專心一致地投入與賴失寧組織的戰鬥中。但當他受了嚴重的傷,而受到一個人類女外科醫生──珍.威特康的照顧後,他被迫得面對內心的傷痛,並首次品嘗到生命中真正的歡愉,直到無從選擇的命運將她奪走……
作者簡介
亞瑪遜書店暢銷作者J. R .沃德(J.R.Ward)
目前與全力支持她的丈夫,還有寵物黃金獵犬住在美國南方。
從法律學校畢業後,她便進入波士頓的醫療機構上班,隨後又在醫療研究中心服務許多年。
寫作一直是她的最愛,一整天待在電腦前寫作,旁邊又有心愛的狗陪伴,再來上一壺咖啡,就是最完美的一天。
譯者簡介
羅秀純
外貿人才養成班畢業,曾任職外商公司擔任總經理秘書。後因喜愛寫作,投入文學創作,至今十餘年,曾出版數十本愛情小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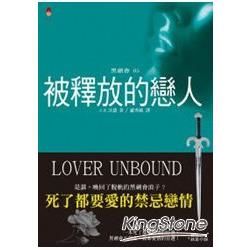
 共
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