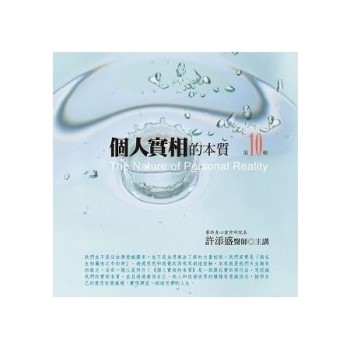軟弱,是種罪惡?暴力,是種救贖?
一個受到家暴的母親,與一個慘遭霸凌的女兒,還有一個你無法苛責的犯罪案件
讓人錯愕也令人滿足、叫人難忘卻又毛骨悚然的一部作品。「雪麗,乖女兒,」她說,「不要害怕,他只想要錢而己。只要我們按照他的吩咐去做,他就走,不會對我們怎麼樣。」
我不相信她的話,從她的手抖個不停,喉嚨又哽得快說不出聲音,我分辨得出來,她也不相信自己講的話。貓一旦進了老鼠洞,不傷害老鼠一下,是不會走的。我知道事情會有什麼樣的結果。
雪麗和母親的個性十分相近,都有著老鼠般逆來順受的性格,她們行事低調、習慣隱藏於人後;她們膽小羞怯,慣於承受而不反抗。她們都曾是暴力底下的受害者。在經歷過一場身心俱疲的離婚官司後,一個失婚的中年女性,帶著臉上有著霸凌留下的傷疤的女兒,以及一筆少得可憐的存款,避居至鄉下一幢與世隔絕的偏僻農莊,準備重拾自己的生活。她們以為終於找到藏身之處,以為這世上種種嚴苛的現實層面不會再侵擾到無力與之對抗的老鼠。然而,在雪麗十六歲生日的前夕,有人闖入她們隱匿的堡壘,打破了得來不易的安寧世界。接下來發生一連串令人震驚又毛骨悚然的事件,雪麗的世界整個翻轉過來,母女倆受到前所未有的試煉。她們的生活如脫韁野馬般失了控,情勢緊張到瀕臨火線,雪麗不禁在想:如果她和媽媽其實不是小老鼠,那麼她們會是什麼呢?
作者簡介:
戈登‧芮斯Gordon Reece
戈登.芮斯在英國牛津大學基布爾學院攻讀英國文學,曾任教於溫布頓的國王學院學校和埃塞克斯的布倫特伍德學校。他在取得文學碩士學位後,轉攻法律,接受律師養成教育。他住過西班牙和澳洲,目前定居於英國。他的著作包括為業界與教育出版社寫的圖文書、漫畫和圖像小說。《2隻老鼠》是他第一本長篇小說。
譯者簡介:
韓良憶
住在歐洲的美食旅遊作家,樂於烹調、旅遊、閱讀、看電影、聽音樂、散步,過簡單的日子。著有十多本繁體書,簡體書已出版三本,譯作更多,包括《柳橙不是唯一的水果》、《黑暗中的人》、《如何煮狼》等,不勝枚舉。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這本勾人心弦、無懈可擊的小說,讓人錯愕也令人滿足,它是那種讓你邊讀邊想「這故事當然一定得寫出來」的原型小說。我覺得本書令人難忘、氣氛十足,又叫人毛骨悚然。
──蘇菲.漢娜(Sophie Hannah),《被偷走的女兒》作者
媒體推薦:
正因為兩位女主人翁性格的缺陷,這個令人膽戰心驚的故事反而更加精彩。
──《書商》
這本勾人心弦的青少年小說有可能成為經典……芮斯的文字簡潔卻意味深長,深具力道,巧妙地遊走於複雜的主題之間,從而成就了一本不落俗套的心理驚悚小說。
──《衛報》
十六歲可以是叫人痛苦的年紀,如果你是過度敏感的女孩,尤其難受。戈登.芮斯在他第一本長篇小說中,精準地捕捉到這樣的感受,而這本小說早已讓讀者連連讚嘆其行文技巧,這位男作家居然可以深入其少女主人翁的內心,還有她那位同樣不堪一擊的母親的內心……作者這本由內心出發的首部長篇小說,讓人讀了很難不投入他紥實而精湛的技巧織就而成的緊張氣氛中……這真是傑出的處女作小說。《2隻老鼠》肯定會是讓人爭相討論的一本書。
──《每日快報》
懸疑……兩位女主人翁的性格之複雜之缺點重重,有趣到果真令人手不釋卷。
──《地鐵報》
如細火慢燉般,緊張的氣氛慢慢凝聚增強。
──《每日郵報》
這本驚悚小說如單獨一顆簡單大方且完美無瑕的鑽石……嚴密聚焦又令人難忘的故事,一路直搗黃龍,奔向令人震撼又滿意的結局,這顯示出只有差勁的作品才需要次要情節。
──《星期日快報》
名人推薦:這本勾人心弦、無懈可擊的小說,讓人錯愕也令人滿足,它是那種讓你邊讀邊想「這故事當然一定得寫出來」的原型小說。我覺得本書令人難忘、氣氛十足,又叫人毛骨悚然。
──蘇菲.漢娜(Sophie Hannah),《被偷走的女兒》作者
媒體推薦:正因為兩位女主人翁性格的缺陷,這個令人膽戰心驚的故事反而更加精彩。
──《書商》
這本勾人心弦的青少年小說有可能成為經典……芮斯的文字簡潔卻意味深長,深具力道,巧妙地遊走於複雜的主題之間,從而成就了一本不落俗套的心理驚悚小說。
──《衛報》
十六歲可以是叫人痛苦的年紀...
章節試閱
第一章
我媽媽和我住在離小鎮約莫半小時路程的農莊裡。我們可是費了好一番工夫,才找到符合我們各項要求的住家:坐落於鄉間、沒有鄰居、三間臥房、前後有院子、屋子有點歲數(必須有「個性」),但同時也得具備各種現代化設施──務必要有中央暖氣系統,因為我們倆都怕冷。一定要僻靜,沒人打擾,說到底,我們是兩隻老鼠,我們要找的並不是家居住宅,而是藏身之處。
房屋仲介帶著我們看了無數房屋物件,但是我們只要是透過林梢看得見鄰舍的屋頂,或者聽得見遠處隱約的車聲,便會交換一個心照不宣的眼神,把這房子自我們的清單中刪除。當然,我們還是會把屋子上上下下都參觀一遍,耐心傾聽仲介解說種種一目了然、不必多說的事情,好比,這是主臥室,這是另一間臥室,這是浴室。我們覺得要是不這麼做的話,未免有點唐突失禮,仲介可是開了好長一段路,載我們來到鄉下。而且,想要叫我媽對這個抹著髮膠、身上的手機還不時振動的狂妄小伙子施出鐵腕(達倫,我們看夠了,謝謝,我們沒有興趣),還不如乾脆叫她飛上月球算了。老鼠絕不唐突,老鼠從來沒有鐵腕,因此我們花了不少個星期六,參觀根本就不感興趣的房地產。
不過,仲介終究帶著我們來到「忍冬小屋」。
它並不是我們看過最漂亮的農莊,房屋正面砌的是褐磚,窗戶小小的,屋頂鋪的是灰石板,煙囪被煙燻得污黑,看來不怎麼像鄉間住宅,倒比較像城裡的房子。然而,這裡的確偏僻得不得了,周遭是大片大片的農地,最近的鄰居坐落在半哩多以外。只有一條單線道通往小屋,並且迂迴難行,彎彎曲曲,環繞著整片地產。路上有多處急轉彎,險象環生,道路兩旁有樹籬,遮蔽了視線,讓人感覺起來像迷宮,而不是公共道路。達倫告訴我們,難得有車子開上這條路,駕駛們可不想被迫尾隨龜速行進的農作機具,這話我們聽進耳裡,總算有一次相信了他。我們必須拐進林蔭夾道的車道,再開上好一段路,才能達到房屋前面,路面坑坑疤疤,左側還有個大彎,加深了我們對忍冬小屋的印象,那就是──這裡距離人跡常至的道路太遠,因此這世上種種嚴苛的現實層面不會侵擾到我們。
最幸福的是,這裡很安靜。元月初颳著大風的一天,當我們爬出達倫那輛四輪驅動的汽車時,我首先注意到的就是那一片靜默。當樹梢的鳥兒停止吱吱喳喳,達倫暫時閉上嘴,不再滔滔不絕地講著那些推銷辭令時(我真喜歡這幢房子,我可不是隨便說說而已,要是有辦法,我想明天就搬來住),它就在那裡;這世上最美妙的聲音──那徹底悄然無聲的靜默,就在那裡。
屋主姓詹金斯,夫婦倆年歲已高,他們在門口迎接我們,兩人一頭油膩的白髮,雙頰紅潤,穿著厚實的開襟毛衣,手裡握著一杯茶,雖然現場並沒有人講出什麼特別風趣的話,他們卻不時爆出呵呵笑聲。詹金斯先生說,因為太太的健康因素──按照他的說詞,是「心臟不大舒服」──萬一有什麼差池,他們可不想住在這「鄉下地方」,因此不得不搬回城裡。他說,離開這裡,他們心裡可難過了,他還請我們放心,說他們在這小屋中度過了三十五年的美好歲月。是啊,三十五年的美好歲月,詹金斯太太跟著重述,好像自己不過就是丈夫的應聲蟲罷了。
他們按照慣例,領著我們參觀屋子,場面不免尷尬:因為有太多的人想擠進狹小的走廊和樓梯平台,每到一扇門前,大夥就喃喃有詞,彼此謙讓,一陣混亂(您請──不,您先請)。我們從一個房間走到另一個,我感覺得到詹金斯先生一再盯著我瞧,想弄清楚一個羞怯的中產階級少女,臉上怎麼會有那麼多難看的傷疤。他們帶著我們穿過廚房,走進後院時,我鬆了一口氣,我可以落後大夥一步,避開那雙窺探的藍眼睛。
詹金斯先生是個園藝高手,他決定要讓我們明白這一點,一路展示後院裡的果樹、菜田和他的兩間工具棚,我們一腳高一腳低地跟在後頭。那兩間工具棚之乾淨、之井然有序,讓我大開眼界,每一種工具都各自掛好,連他倆的手套都按兩人的名字「傑瑞」和「蘇」,各自以名牌標示好。他讓我們看他臭氣四溢的堆肥,得意地說:「這個呢,正是令我自豪又喜悅的美物。」又領著我們參觀他們搬來此處時種下的兩行絲柏樹,如今樹高已逾十公尺。在他詳細解說樹皮有多麼健康時,我小心打量茂密的枝葉,樹後除連綿到天邊的大片青翠農田外,其他什麼也沒有。
詹金斯先生尤其為他的前院感到自豪,寬闊的草皮修剪得像滾木球場一般工整,草地周遭圍繞著數不清的花草和灌木叢,儘管隆冬景物蕭瑟,草木各處仍零星露出鮮明的色彩。「重要的是,種植冬天仍會開花的植物,」他對我媽媽說,「還有許多多年生的植物,不然的話,冬天就毫無色彩了。」媽媽想轉移話題,說她不大懂園藝,詹金斯先生卻以為她言下之意是要請他當場指點一二,好彌補她知識的不足。他開始長篇大論地說明各種型態的土壤。「說到這塊土壤,」他說,「它含有石灰質,有一點乾,有一點『飢渴』,需要大量的農家糞肥、腐葉、庭園堆肥、草根土……」他喋喋不休,我聽不下去了只得走開,「腐葉……人造肥料……石灰岩地層……」我想我一度聽見他講到「乾血」,但想必是自己聽錯了。
我繼續走,那討厭的聲音在我身後逐漸消失,變成單調咕噥的聲響,這時我發覺自己走到小徑的盡頭,草地中央有一大片橢圓形的玫瑰花壇橫阻在跟前。玫瑰花枝遭到無情的修剪,被截斷的花莖伸向天空,好像舉著殘臂在抗議。這副景象看來淒涼,被翻起的土壤堆成一座小山,讓我聯想起剛挖好的墳地。
我環顧院中其他植物和樹叢,發覺自己幾乎連一種也不認得。如果我想成為作家,當然就一定得認識這些植物。作家似乎都認得花草樹木之名,這讓他們發起言來比較擲地有聲、莊嚴神聖。我打定主意,等我們搬進來後(我從我媽一臉陶醉的表情便已看出,這裡將是我們的新家),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學會庭園中每一種花草樹木的名字,不單是俗名而已,還要認識拉丁學名。
當我回到我媽身旁,詹金斯先生再也按捺不住好奇心了。
「親愛的,妳是怎麼了?」他問,一隻手不經意地揮了揮,表示他指的是我臉上的疤痕。
我媽本能地把我拉近她身邊,替我回答。
「雪麗出了點意外,在學校裡出了意外。」
第二章
媽媽動用離婚分到的錢買下忍冬小屋,那筆款子少得只能養活老鼠。信不信由你,我爸是專門經手家事法的律師,他在一年半以前拋妻棄女,投入他秘書的懷抱,那女的可年輕了,比他小三十歲,有張淫蕩的娃娃臉,總是不吝露出胸前的事業線(她只比我大十歲!而我難道得把她當成我的「新媽媽」嗎?)。財務和「育兒」事宜讓離婚官司拖了大半年才塵埃落定,爸爸打起官司來,簡直把媽媽當成懷有深仇大恨的宿敵,而不是結髮十八年的妻子,他想方設法要拿走她的一切,其中甚且包括我。
媽媽一步步退讓,放棄領取他養老金的權利,放棄贍養費,甚至因為他的賭氣要求,而歸還他結婚多年來送給她的部分禮物,但是她拒絕放棄我。法官判定我是「格外聰穎」的十四歲女孩,有能力自行決定想跟誰住。由於我渴望留在媽媽身邊,我爸的監護權聲請被駁回。當他明白無法藉由把我帶走而懲罰媽媽多年的忠誠奉獻時,立刻和「佐依」移居西班牙。他先前還一副很想要我跟他同住的慈父模樣,那會兒卻不告而別,從此音訊杳然。
房屋以快得出奇的速度過戶,我們在元月底搬進忍冬小屋。那是個詭譎多變的冬日,天空這一刻還烏雲密布,下一刻卻陽光普照,彷彿春天提早到來,可是過了一會兒又是陰霾蔽天,寒風刺骨,下起一陣陣冷雨。
搬家工人體臭難聞,他們穿著沾著污泥的靴子,嚼著口香糖,懶散地在小屋走進走出,不時大聲暗示幹這活兒讓他們好口渴,「在所不惜,就想喝杯茶」。媽乖乖地端了一托盤的奶茶出來,還按他們的吩咐加了三、四顆方糖,他們就坐在碎石車道上喝茶抽煙,身子靠在茶櫃上,而他們本該把這些櫃子搬進屋裡。有個工人看到她在盯著鋼琴一側瞧,那兒被他們撞出一個很大的凹痕,就快活地扯高嗓門說:「美女,不是我們弄的,本來就凹了。」她急匆匆跑回屋內(老鼠最怕衝突場面),他們放聲大笑,可開心了。
他們威嚇她以現金付帳──包括他們一面喝著她的茶,一面模仿她「上流」口音的那半個小時在內──最後,他們總算走人了,留下掛在花葉上的煙蒂。
拿樸實舒適的忍冬小屋,來交換城裡那幢我已住了差不多一輩子的豪宅,我一點也不覺得遺憾。當爸媽打起離婚官司時,那屋子便已不再是我的家,它在那之後變成了「婚姻居所」,是貴重財產,雙方律師有如詭計多端的棋手,各顯神通,想據為己方所有。婚姻居所永遠不會是幸福的家。
對我而言,那裡有太多回憶,有甘有苦。我說不上來什麼比較苦,是爸爸在我七歲時打扮成耶誕老公公的模樣,雙手輕輕捧著一隻在微微打著哆嗦的金黃色倉鼠呢,還是七年以後,酩酊大醉的爸爸,真的踢倒房門,只因為該輪到他接我共度週末,而我不肯跟他走;是爸媽在結婚十五週年紀念日當天,在客廳中當著親友的面,隨著艾力.克萊普頓的〈今夜多美妙〉的歌聲,面貼面翩然起舞,還是三年後,爸爸兇巴巴地一把將我媽推開,害她跌坐在地上,折斷一根手指。就在那同一間客廳裡面……
還有一個理由讓我慶幸自己離開了「婚姻居所」,這個理由連對我自己都不想承認,就是儘管爸爸是這麼對不起我們母女倆,可是血緣關係很難切斷,我就是禁不住想繼續愛著爸爸。婚姻居所處處都留有一些痕跡,讓我想起他的另一面,想到他可以有多麼親切可人,我們以前有多麼開心。我六、七歲時,他在山毛櫸樹上替我蓋了樹屋;我上中學前,他在我臥室中裝設了好漂亮的書架,還有他從倫敦替我買回來的那些皮面精裝的「經典童書」(鼓勵我立志當作家的是爸爸,是他種植了那種籽)。他以前總愛在車庫做運動健身,裡頭仍隱約留有他的汗味,那兒有面老舊的鏢靶,我們常玩擲鏢遊戲,玩得樂不可支。
不過,說不定最叫人辛酸的事,就是只要一照鏡子,見到爸爸那雙淡褐色的眸子正盯著我看,便會想起他。我一直比較親媽媽,不怎麼親爸爸,可是當我們共享天倫之樂時,好比在我年幼時,他把我高高地舉上天,彷彿想在耀眼的陽光下看穿我的身子,在這樣的時刻,不知怎的,那滋味甚且更加美好。
當然,這件事我沒對媽媽講,以免讓她傷心。可是,只要我們還住在婚姻居所,那狡詐難擋的誘惑便不會消失,如果我和媽媽為了種種小事起爭執,那誘惑就會忽然增強。我希望搬家以後,這股特洛依木馬式的感覺會減弱,終至消散無形。
忍冬小屋是個令人精神一振的新開始,我喜歡廚房裡的老式櫥櫃、赤陶地磚和磨砂處理過的松木桌子。不論外頭天氣有多麼陰沈,這裡總是溫暖又舒適,所以我們後來就都在廚房裡用餐。我喜歡客廳與飯廳沒有隔間、一氣呵成的設計,如此一來,即便我們各忙各的,我卻始終能感覺到媽媽就在附近。我喜歡用粗糙、凹凸不平的灰石砌成的壁爐、塗了亮光漆的壁爐台和仿都鐸式窗戶那小巧秀氣的菱形。我喜歡破舊的木樓梯,從頂端算來第四階,腳步一踏上去,不管落在哪裡,都會大聲發出咿咿呀呀的聲音。我喜歡我的臥室裡外露的屋梁和內嵌式的窗邊座椅,我坐在那兒就著光看書,一看便是好幾個小時,那光線之純淨、清澈,是我以前沒看過的。我喜歡一早起來拉開窗簾,看到的淨是翠綠和鮮黃的阡陌,一望無際,直到天邊,而不是市郊千篇一律的紅磚「高級住宅」,每一戶外頭的車道上都停著一輛雙B轎車。我最喜愛的一件事,就是我可以搬把椅子到後院,坐覽天上的雲朵彷彿火山岩燈的溶蠟般,緩緩幻化各種形狀。
我盯著天空瞧時,就愛想像自己活在一個比較簡單又純真的年代,最好是尚無人類以前的時代,那時地球還是一大片開闊的綠色樂土,而殘酷──只為了享受傷人的樂趣而傷人──仍是完全未知的事物。
第一章
我媽媽和我住在離小鎮約莫半小時路程的農莊裡。我們可是費了好一番工夫,才找到符合我們各項要求的住家:坐落於鄉間、沒有鄰居、三間臥房、前後有院子、屋子有點歲數(必須有「個性」),但同時也得具備各種現代化設施──務必要有中央暖氣系統,因為我們倆都怕冷。一定要僻靜,沒人打擾,說到底,我們是兩隻老鼠,我們要找的並不是家居住宅,而是藏身之處。
房屋仲介帶著我們看了無數房屋物件,但是我們只要是透過林梢看得見鄰舍的屋頂,或者聽得見遠處隱約的車聲,便會交換一個心照不宣的眼神,把這房子自我們的清單中刪除。當...
作者序
《2隻老鼠》提出了一些難以解答的道德問題,你是否相信邪不勝正?還是說,其實應該是適者生存?
我認為如今已少有人把這世界看得如此黑白分明了,我懷疑即便是超人自己也不見得就會相信邪不勝正。能懷有那樣的信念固然很好,但是我認為我們看得已夠多了。就算是「善惡正邪」的定義,也不再是一拍兩瞪眼──為了行「善」而施「惡」舉,算不算邪惡呢?在《2隻老鼠》書中,母女倆捲入了一個考驗著兩人道德準則的情況,此舉具有逐步腐蝕人心的影響力,終而造就但願是出人意表的結局。我是分階段寫作這本書,每寫完一個段落就寄給我的經紀人黛比.葛洛文過目,請她給我意見。我記得她說,當她讀到最後一個段落時,說:「我不敢說自己認識這兩個人了。」而在某個層面上,這正是這本小說的重點所在。透過「適者生存」這個角度來看這本書會很有意思。儘管情況不利於這對母女,但是事情多少可以說是,她們證明了自己是存活下來的適者。此一觀點顯然比邪不勝正更接近於我的意圖。
你有多認同雪麗母女倆?對她們性格中像「老鼠」的那些層面又認可到哪種程度?
我得開門見山地說明,我定義中的如老鼠般的人類,並不見得是羞怯或拙於社交到不行的人,雪麗和她的母親其實在很多不同的方面都是聰明有才華又成功的人。對我而言,她們之所以成為「老鼠」,是因為她們無法處理在言語或身心上與人抗衡的局面。而世上卻有那麼多人似乎是越戰越勇,這讓她們身陷險境卻沒有招架之力。雪麗和她媽媽有很多「像老鼠一般」的性格,好比嗜讀如命、崇尚知性、喜愛古典音樂、守法、談吐優雅、有禮貌,幾乎是英國中產階級文化的特性。我的出身背景基本上是工人階級,我知道自己在抨擊依我看實在是「很沒氣魄」的這些性格。記得當年在校時,有份成績單對我的評語是,「激烈反智」,我也依然記得因為很氣自己必須戴眼鏡,而把鏡片砸碎。所以,在某種程度上,中產階級文化在英國給人「像老鼠一般」的印象。一九八五年,當漢密爾頓出版社退了我第一本童書的稿子時,我以為通往寫作生涯的那扇大門從此關上了,我當時的反應想來可以說明一切,我想去從軍。
《2隻老鼠》歸根結底是一本非常授能給力的小說,可是你是從哪裡得來靈感,而會寫出如此廣泛探討人性黑暗面的書呢?
我想我大概總是在寫探討「人性黑暗面」的故事吧,即便在我還是學生時就是這樣,不盡然是恐怖故事,比較像是驚悚故事,總是免不了繞著暴力行為和某種扭曲的心靈打轉。如果要我夫子自道,從事自我心理分析的話,我可以說,這一部分是個人的經歷使然,還有一部分和影響我最深的書籍有關。我九歲時,我姊夫給了我一袋美國漫畫書,除了有超級英雄當主角的書,還有好幾本《怪異與驚嚇故事集》。這幾本恐怖和科幻的故事書改變了我的人生,我立刻迷上這些黑暗的通俗故事,在學校寫作文時,滿紙都是那一類囈語。我真的相信這些書教了我寫作之道(大家往往低估了漫畫書,有很多其實寫得很好)。它們也讓我對情節和靠情節推動的故事有很好的胃口,故事的結尾通常都會有反諷又黑暗的轉折。
《2隻老鼠》描繪了霸凌會對人造成怎樣可怕的影響,你覺得這是個很難寫的問題嗎?
老實講,我不覺得霸凌很難寫。我寫的題材越是尖銳極端,我就越是投入,我想你感覺得出來,《2隻老鼠》在觸及那些段落時換了檔。我是在想到別人讀到的反應時,才覺得霸凌題材難寫。我很清楚文字對讀者可能會造成多大的衝擊,書中的霸凌情景是那麼陰暗,我不得不說,我曾怯步不前,躊躇著該不該與人分享。我希望不要有人誤以為《2隻老鼠》是文以載道、反霸凌的書。我對那些非常重要的小說的作者沒有一絲一毫不敬之心,可是《2隻老鼠》並不是那樣的書,我也不是那一類的作者。書中之所以有霸凌,是為了在雪麗的心中製造心理火藥,到了第十四章的結尾終於引爆。
世界各地都有出版商對這本有很大的興趣,你對這樣的迴響感到意外嗎?
對於大家對《2隻老鼠》有正面的迴響,我並不覺得意外。這本書打從一開始,便得到讀者的熱烈反應,讀者要麼熬夜,要麼閉門不出,非要先把書看完不可。人們如此認真投入到這素材當中,想要談談這本書,想要討論各種問題,想要告訴我他們在那種情況上會怎麼做,凡此種種都鼓勵了我。
《2隻老鼠》提出了一些難以解答的道德問題,你是否相信邪不勝正?還是說,其實應該是適者生存?
我認為如今已少有人把這世界看得如此黑白分明了,我懷疑即便是超人自己也不見得就會相信邪不勝正。能懷有那樣的信念固然很好,但是我認為我們看得已夠多了。就算是「善惡正邪」的定義,也不再是一拍兩瞪眼──為了行「善」而施「惡」舉,算不算邪惡呢?在《2隻老鼠》書中,母女倆捲入了一個考驗著兩人道德準則的情況,此舉具有逐步腐蝕人心的影響力,終而造就但願是出人意表的結局。我是分階段寫作這本書,每寫完一個段落就寄給我的經紀人黛...


 共
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