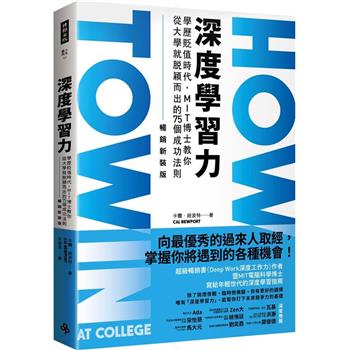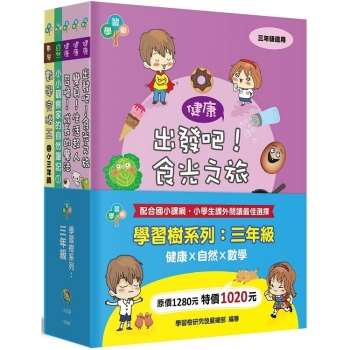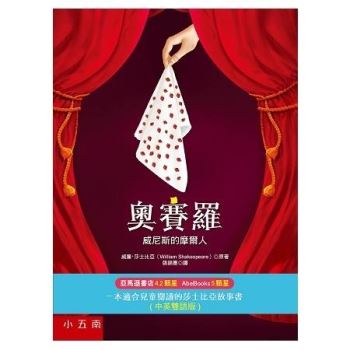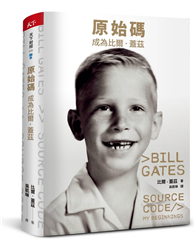爸爸與鏡頭
爸爸拍的照片很少是成功的,我指的是他晚年之後掌鏡的作品。
事實上,爸爸從很年輕就接觸攝影。在我還未出生的時候,媽媽說台東永樂街的家裡已經有暗房,爸爸會自己沖洗照片。媽媽學生時代因為代表高雄女中跟屏東女中賽球而認識彩英阿姨,終身結為至交。彩英阿姨也是年輕就愛攝影,聽說後來我們家沖洗的工具,阿姨用得比爸爸多。三十幾歲後一直到六十五歲退休,爸爸因為工作忙碌已很少接觸相機,等晚年有空,他對晚輩手中拿的新時代產品有了一點敵意,也很陌生。但兩個女婿都很愛攝影,他對他們簡直有點煩,怎麼相聚的時候,他們的相機從不離手。
爸爸是很喜歡相機、顯微鏡、羅盤這些東西,但不知道為什麼,我們會給他買顯微鏡,買放大鏡,買各種各樣的羅盤,卻沒有人送他一台相機。我們不送他相機的理由跟整天阻止他吃蛋的心情似乎有一點接近,好像大家都不怎麼信任爸爸。
記得好久好久以前,爸爸曾經想要接受新式簡便相機。有次姐姐一家跟我們一家在聖荷西的公園烤肉,爸爸想幫我們大家拍個合照。他對照相這件事的觀念與眾不同,一是絕不以獵物的眼光補捉鏡頭。兩家大大小小十幾個人在遊戲與享食中要成軍已是不易,但爸爸的基本要求是照片中的每一個細節都要很清晰完美。所以一群像小猴般的孩子們在過久的對焦中終於潰不成軍,一哄而散。從此,大家對爸爸的兩件事開始敬而遠之:一是阿公要照相,二是阿公的禱告。
爸爸到現在還沒有受洗,但十幾年前開始,媽媽就對他傳教。起先爸爸是不肯的,因為他說自己心中的神只有我當時已經過世的祖父母。但,慢慢的,他也會去教會。我感覺所有屬於宗教的生活活動,爸爸最喜歡出聲禱告。
我認為爸爸之所以不排斥禱告的原因,是因為他難得有發言的機會。平日家中有我們幾個愛說話的孩子們和口才便給的媽媽,非常不擅言詞的爸爸在年輕時很不愛說話,更不愛社交活動。他老了之後才剛開始了解交談的快樂,每次才要細細回想,娓娓道來之前,反應快、記憶好的媽媽總會攔截在前說:「這個我來說比較清楚。」但謝飯禱告不一樣,媽媽因為急於讓爸爸早一點進入教會生活,只要爸爸願意開口禱告,她很樂意讓出這個講話的機會。
爸爸的禱告真太有趣了,完全符合陳之藩謝天的概念和暢所欲言的自由。我們在聖荷西那天,不只拍照因為對焦太久而群情躁動,謝飯禱告時,也因為族繁不及備載而燒焦牛排。原因是,爸爸實在是很好的一個人,他真心感謝我們能齊聚在美國的恩賜,又在這樣一個晴天麗日中享受美食。於是,就從姐夫家的家人提起,再談到我的夫家,又想起哥哥們不能同來。總之,話還沒講完,我們就先聞到烤肉架上陣陣催人的焦味。這次,是我那凡事精明務實的母親先從莊重的謝飯禱告中不顧一切的抽身,接著我們全都呼應而上。於是原本圍聚成圓圈低頭的眾家人,只剩還在點名的爸爸兩掌交握,一片真心誠意的代替我們大家感謝這豐盛的一餐。此後,每到重要聚餐,大家似乎比較期待由媽媽來帶領禱告;她會根據當天桌上的食物宜冷宜熱來決定禱告詞的長短。
爸爸看著大家拍照也難免有手癢難耐的時候,但他終究是很客氣的人,只有過幾次問我們借相機,或建議要幫我們拍幾張照片。但,就如我一開始提及,爸爸的拍照很少有成功的作品。這有可能是八十幾歲的眼睛不夠好,更有可能是因為緊張,而且對新式相機的陌生,於是只求在匆匆按下快門前我們大家不要再一走了之。
但我喜歡爸爸按下四次快門之後,才幫我跟Eric在美術館中拍下一張清楚的照片。我更喜歡在梨花大學那一天,Eric麻雀在後地捕捉到爸爸幫我們拍照的可愛模樣。
共遊之道
因為有十二年的時間沒有長住在台灣,島內旅行對我來說反而比出國旅遊更珍貴。好多風景區我沒有去過,好多縣市只是行程的過站。陌生之地還來不及拜見,舊地而能重遊就更不敢奢望。因此,當朋友邀約要去一趟日月潭時,我心中充滿了奢侈的愉快。雖然知道那兩天一定是還是有很多工作得做,但何妨帶著工作去旅行;也許,在山明水秀之地工作起來,品質與效率會更好。
回想上一次去日月潭已經是二十幾年前了!我們和新婚不久的學弟妹雪梅、瑞琪夫妻去度了一個三天兩夜的湖邊消遙遊;那時他們還沒有孩子,我們把孩子託給了爸媽。訂的飯店因為剛開始營運,設備很新,住客很少,無論住宿、用餐、設施或服務,都細致地表達了飯店的宗旨。浮在水上的大木屋二十幾年來聽說已有很大的改變。
飯店隨著歲月與旅人的腳步往前走,通常只有兩種結果,一是在人來人往的雜沓磨損中耗損掉自己當年的意氣風發,讓滄桑之感停在空間的角落和陳舊的氣息當中。另一種是用日日夜夜的精緻維護,把穿梭過歲月所累積的識多見廣,蘊釀成一種新飯店永遠無法營造出來的篤定與風韻。我不知道當年投宿的飯店走上的是哪一條路,因為,這次旅行的主辦者不是我,而是三對夫妻朋友中一位熱心的友人。
我們的日月潭之旅一開始就憂心忡忡,這是一趟乘興計劃卻未能盡興而歸的遺憾之旅。
出發前一天,主辦的朋友打電話說另一對朋友不參加了,因為他們夫妻一番大吵之後,太太離家出走了,到現在都還下落不明。聽了真擔心,我提議取消這次的旅行,但電話那頭的朋友很為難的說,不行呢!她已經代墊了所有房間的費用,而飯店不接受取消退款或延期。我一聽就說:「不要擔心,我們還是照原定計畫出發,也許明天他們夫妻和好之後就會出現在飯店。」電話中,我們還開玩笑說,也許那會是他們的小蜜月之旅呢!
抵達日月潭之後,我發現自己腦中竟撿不回二十幾年前曾來過的印象。是我的記憶衰退得這麼快,還是日月潭這段日子以來的變化真的太多了?總之,到處都是人,湖上都是船,遊客的衣彩在湖光山色之間上紅抹綠,好不熱鬧。
進飯店安頓下來之後,離家的朋友還沒有下落,更糟糕的是,聽說他們家的兩個孩子也還沒有接到媽媽的任何電話。這使朋友之間在憂慮之上更添一層不安,但我們當中誰也沒有說出心中的愁緒,只想為彼此打氣,就說:「既來之,則安之,好好享受大家在忙碌中特別擠出來的兩天吧!」但心事重重的抑鬱之感像無形的罩紗那樣在我們的談話之間隱約揚動著。也許是這樣,那天與客房一起提供的套餐到底有哪些菜,我現在竟一樣也想不起來。
回到房裡,我想藉工作安頓四面張望的心思,打開電腦等待著開機時,才好好把房裡的規劃與陳設細細地打量一次。房間外望的景色很好,我總是起得早,期待明天清晨可以坐在陽台上看日月潭慢慢在晨光中甦醒的模樣。那一夜,我睡得很差。我想有兩個原因,一半當然是因為睡前還沒有好消息讓我們解除心中的掛念;另一半是,與床靠得太近的那只浴缸深深困擾了我。
我不喜歡室內有透明的浴室隔間,或開放在房間的浴缸。雖然我懂得這位設計者想讓房客無論在陽台晝寢,在床上夜寐,或在浴缸泡澡時都能觀湖看山,但是,這對我來說卻很不舒服也不大合理。睡睡醒醒翻轉了一夜,我果然是天未亮就起來守著日月潭的早安。但,我的朋友比我起得更,當我從陽台上俯瞰那片美麗的泳池時,她已在晨曦微探的水波中往來好幾趟晨泳了。
旅行回來後的隔天,才聽說朋友去弟弟家住了幾天後,終於回家與先生言歸於好。雖然高興她的安然無事,但心中也是難免氣怒的。夫妻吵架意氣用事是家務事,讓一幫朋友為此擔心到這樣的地步,讓他人的旅行遮雲罩霧,對她擔心掛念實在是不夠厚道。
但這並不是我第一次感覺到朋友一起出遊大不易。
二十年前,我們也曾跟兩家朋友到歐洲一遊。我們是直接約在海德堡見面。Eric和我先把孩子安頓在瑞士之後,再分別與與從美國和台灣出發的友伴會合。孩子小的時候,我們不喜歡帶她們旅行太久,但其他兩家都各自帶著年齡較大的孩子同行。那一路,爭執不少,一為吃住的標準而吵,二為各自教養孩子的標準不同而有意見。前者觸及金錢,後者觸及情感,兩件都是敏感事,牽動了每一個人的神經,讓一趟原本應該輕鬆愉快的旅行變得好辛苦。
計畫行程與代訂所有房間的朋友一向喜歡住得好、吃得好,連水都要喝得好;但從美國來的朋友卻不想在旅行的吃住上過度花費。他們一到海德堡,得知房價後就反應花費太高,這讓一手安排行程的朋友覺得自己吃力不討好,很不開心。
我們是最後一對趕來會合的夫妻,正喜滋滋的要分享我們從義大利進德國轉車的故事,沒想到迎接的是兩對吵到幾乎不肯說話的朋友。一個說:「他們倆收入都這麼好,又不是付不起!」另一個說:「付得起也沒有打算這樣用錢。」這些爭吵後來一路影響著我們旅行的心情,在用餐與活動的決定上更猶豫不決,不知道該如何兼顧。
那次的經驗讓我學到兩件事:
一是旅行不一定要呼朋引伴、成群結隊。另一是,如果決定要同行,大家應該要先討論對預算的看法,要彼此尊重才能找出不委屈的解決之道。
預算是個人的自由,也是應該受到尊重的想法。朋友一起出遊,尊重的廣度與深度會考驗友誼與智慧。
渾然一鍋東北味
坐船遊完松花江之後已過兩點,大家都餓了,但還是期待能吃到一點真正的東北味。這一天,我們除了租車之外也請了當地的嚮導。她聯絡了一下,帶我們到一家午市已散,凌亂尚未整好的餐廳去。三層樓有好幾個包廂的餐廳裡並沒有見到什麼人,但一樓的散座桌桌杯盤狼藉,看起來中午生意很不錯。不過,環境與人員看起來都很疲憊,也許,忙亂過還沒能打起精神來收拾。
我們被帶到一個包廂,房裡的圓桌很大,桌子中間的一只鐵鍋也很大,這個房間平常應該可以坐到將近十七、八個人吧,圓型座位與一邊的牆相接的部份還打成鋪,大概是仿炕。哥哥下樓去點菜,他是美食與飽食主義者,想必這一餐也簡單不到哪裡去。
進門後,大家看到餐廳環境的品質心照不宣,沒有人露出對這一餐有太高期待的神情。實在是好餓了,在等待中,送來的炸蝦餅和小菜倒是助了酒興。在東北喝常溫啤酒已是我們餐餐的開胃共好。
一連開了好幾瓶雪花啤酒之後,好不容易來了一個穿著黑底滾紅邊廚師服,頭戴紙高帽的年輕人,他來開鍋。我們饑腸轆轆,興奮以待,先前只看到一個大鍋,卻不知要吃什麼。大鐵鍋早有人來用小火預熱了,廚師倒下不少油之後,先下甜麵醬和豆瓣醬,他用一只大杓在鍋裡來回畫著八字,醬料融在油裡生香,又陸續加了乾椒、花椒和大把大把的蒜苗和薑、蔥。香味很快散開,煙霧從鍋邊嬝嬝迴旋而上。另一位服務員送來了一個不銹鋼的大盤,盤上有好幾斤的魚,三種都是松花江上的野生魚。其中的鳇魚,油多到讓人懷疑到底夠不夠新鮮。膩在皮肉之間的簡直就是一層奶油。廚師接著把魚分次放入已經爆到很香的鍋底去煎。鳇魚切成分而不斷的魚片,中型的白魚劃著整齊的刀口,頭尾相連整條下鍋。魚一下鍋,就在熱得鬧跳的油中生出了香氣。雖然很濃,但聞著一點都不膩,也沒有腥味,只覺得這一鍋必然味道厚足,精采可期。
媽媽聞著、聞著,身不由己地伸長脖子。我知道她是因為桌太大,看不清楚鍋裡的變化,但聞著這香氣又覺得一定要把廚師的手法和所加的材料都觀察得更清楚才能回家複製這份美味。
媽媽和我雖然還沒有吃到成品,但因為我們都是廚房裡身經百戰的老手,又在海邊住過很長的一段時日,這一鍋聞到此時,心中已確定不只是好,還一定會非常好!持續著「活到老學到老」的精神,媽媽從延頸的凝神,終於忍不住站起來觀摩,她專注嚴肅的英姿,可以唬人說是八十五歲的鍋灶總監。
魚都放入鍋裡煎香之後,少量的油汁再度滾起。廚師又下了一大碗料酒和一碗加了老抽的胡麻醬,他放下好幾片山東大白菜之後,傾壺倒下淹漫所有材料的高湯,然後拿起一個厚達四、五公分的木頭蓋,嚴嚴地把那一整大鍋的食材與味道都隔絕在鍋裡。煙霧不見了,香味也與我們暫別。我們比進門前更餓,但這次,每個人的眼睛盯向鍋蓋時全都帶著熱切的期待。
鍋蓋再度掀開時,散出的香氣真是難以形容,夾起那本來以為不夠新鮮的鳇魚,我才了解牠的不同凡響。原來,松花江不只是名字美,她的魚產也不負江名。
那晚,我在報紙中讀到今年大水庫鳇魚盛產,以鳇魚為食的棕頭鷗,竟因為如此而只吃魚眼睛。原來食物鏈裡也有美食鏈。
| FindBook |
有 3 項符合
旅行私想(首批限量蔡穎卿老師親筆簽名扉頁版)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352 |
主題旅遊 |
$ 360 |
休閒旅遊 |
$ 360 |
休閒旅遊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旅行私想(首批限量蔡穎卿老師親筆簽名扉頁版)
【首批限量蔡穎卿老師親筆簽名扉頁版】
旅行時,我們從心靈往外望,看見別人的生活與身外的世界。
一次一次的旅行過後,
感覺自己與生活有一種天長地久的誠懇相守,
一種糟糠生活絕不相棄的真情。——Bubu
我們一再出門旅行,是為了重新尋回生活的美好。
從12歲離家求學開始,
旅居過幾個不同國家、城市。
Bubu可算是經驗豐富的旅者。
數不清多少次的出門旅行,
不論是短暫的身心出走,
或家人朋友另一種形式的聚首;
甚至是任務在身,為工作遠行……
驟然的空間轉換,
使得綿密的日常生活有了不同的風景與節奏。
旅行歸來,生活有了更深的意義。
這是一場Bubu的私旅行,細膩分享。
延伸閱讀:
媽媽是最初的老師
我的工作是母親
廚房之歌
作者簡介:
蔡穎卿
1961年生於台東縣成功鎮,成大中文系畢業。目前專事於生活工作的教學與分享,期待能透過書籍、專欄、部落格及實作與大家共創安靜、穩定的生活,並從中探尋工作與生命成長的美好連結。
著有《媽媽是最初的老師》《廚房之歌》《我的工作是母親》《漫步生活——我的女權領悟》《從收穫問耕耘,腳踏實地談教育》(天下文化);《在愛裡相遇》《寫給孩子的工作日記》《Bitbit, 我的兔子朋友》《小廚師——我的幸福投資》(時報出版);《我想學會生活:林白夫人給我的禮物》、《50歲的書桌》(遠流出版);《廚房劇場》《空間劇場》(大塊出版);《我想做個好父母》(親子天下)。
章節試閱
爸爸與鏡頭
爸爸拍的照片很少是成功的,我指的是他晚年之後掌鏡的作品。
事實上,爸爸從很年輕就接觸攝影。在我還未出生的時候,媽媽說台東永樂街的家裡已經有暗房,爸爸會自己沖洗照片。媽媽學生時代因為代表高雄女中跟屏東女中賽球而認識彩英阿姨,終身結為至交。彩英阿姨也是年輕就愛攝影,聽說後來我們家沖洗的工具,阿姨用得比爸爸多。三十幾歲後一直到六十五歲退休,爸爸因為工作忙碌已很少接觸相機,等晚年有空,他對晚輩手中拿的新時代產品有了一點敵意,也很陌生。但兩個女婿都很愛攝影,他對他們簡直有點煩,怎麼相聚的時候,...
爸爸拍的照片很少是成功的,我指的是他晚年之後掌鏡的作品。
事實上,爸爸從很年輕就接觸攝影。在我還未出生的時候,媽媽說台東永樂街的家裡已經有暗房,爸爸會自己沖洗照片。媽媽學生時代因為代表高雄女中跟屏東女中賽球而認識彩英阿姨,終身結為至交。彩英阿姨也是年輕就愛攝影,聽說後來我們家沖洗的工具,阿姨用得比爸爸多。三十幾歲後一直到六十五歲退休,爸爸因為工作忙碌已很少接觸相機,等晚年有空,他對晚輩手中拿的新時代產品有了一點敵意,也很陌生。但兩個女婿都很愛攝影,他對他們簡直有點煩,怎麼相聚的時候,...
顯示全部內容
作者序
旅行的意義
旅行時,我們從心靈往外望,看見別人的生活與身外的世界。
我從旅行中學到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對相遇的美景與好事都心懷感謝,但不能眷戀;一生眷戀心,去了一地就想要搬去一地。這種願望當然多半都不會實現,但比願望落空更遺憾的,是在不知不覺中失去了對原有生活安定的感受;而安定,是一種從心靈環境看到自己的美。也許,我們一再出門旅行,就是為了尋找這樣的看見。在一次又一次的旅行過後,感覺到自己與波瀾無驚的生活竟有著一種天長地久的誠懇相守;一種糟糠生活絕不相棄的真情。
如果旅行不是專指為遊玩而出門,那我...
旅行時,我們從心靈往外望,看見別人的生活與身外的世界。
我從旅行中學到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對相遇的美景與好事都心懷感謝,但不能眷戀;一生眷戀心,去了一地就想要搬去一地。這種願望當然多半都不會實現,但比願望落空更遺憾的,是在不知不覺中失去了對原有生活安定的感受;而安定,是一種從心靈環境看到自己的美。也許,我們一再出門旅行,就是為了尋找這樣的看見。在一次又一次的旅行過後,感覺到自己與波瀾無驚的生活竟有著一種天長地久的誠懇相守;一種糟糠生活絕不相棄的真情。
如果旅行不是專指為遊玩而出門,那我...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旅行私想:謝謝天地接納我
自序 旅行的意義
輯一 跟著回憶去旅行
不是,我是失敗的人
記不起來與忘不掉的事
兒時記憶,故人往事
新港、新港
爸爸與鏡頭
夢想不老
一樣生活兩樣情
共遊之道
輯二 世界的旅人
風裡的白布,布裡的精神
渾然一鍋東北味
世界最高的游泳池和我們衣櫃最貴的游泳褲
窗口的巴黎鐵塔
讀懂生活讀懂書
小酒館裡
一夜情(一)
一夜情(二)
挽救婚姻的美食青
青鱗仔
金門,三得與三記
金門一,建築之美
金門二,生活之靜
金門三,生命強韌之美
輯三 人情‧旅事
入鄉隨俗
距離
帶著...
自序 旅行的意義
輯一 跟著回憶去旅行
不是,我是失敗的人
記不起來與忘不掉的事
兒時記憶,故人往事
新港、新港
爸爸與鏡頭
夢想不老
一樣生活兩樣情
共遊之道
輯二 世界的旅人
風裡的白布,布裡的精神
渾然一鍋東北味
世界最高的游泳池和我們衣櫃最貴的游泳褲
窗口的巴黎鐵塔
讀懂生活讀懂書
小酒館裡
一夜情(一)
一夜情(二)
挽救婚姻的美食青
青鱗仔
金門,三得與三記
金門一,建築之美
金門二,生活之靜
金門三,生命強韌之美
輯三 人情‧旅事
入鄉隨俗
距離
帶著...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