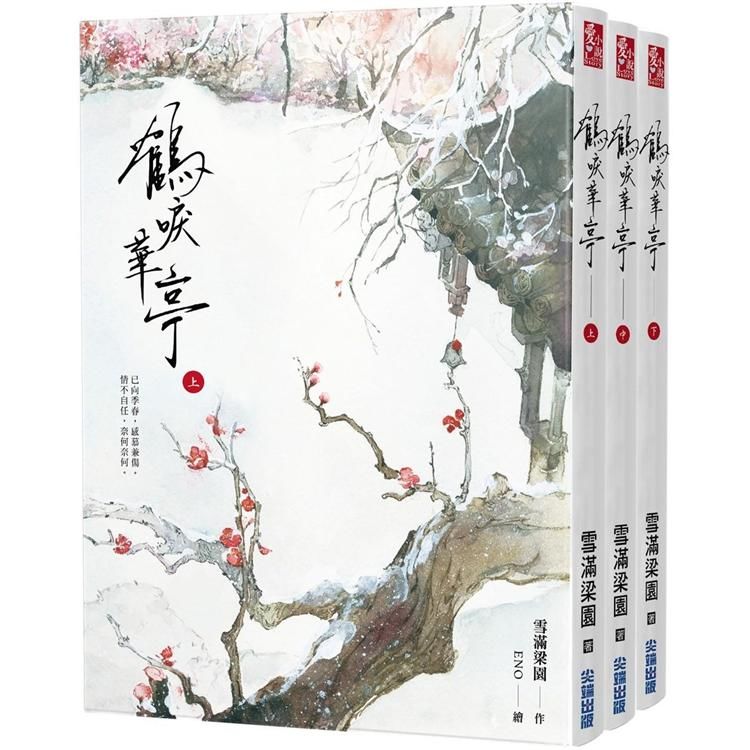「人都會死,可在死之前,不也要先活著嗎?」
被父親兄弟忌憚的孤高太子╳身懷祕密的洗衣宮女,遊走於刀尖之上的宮廷戀情!
這是一場地位天差地別,只有尊嚴勢均力敵的情感博弈。
兩個無法交付真心,卻是這世上最能理解彼此的人,在深深宮廷,時時提防對方,又寂寞入骨地,相伴。
劇情百轉千迴,挑戰你智商、讓你懷疑自己是文盲的超燒腦作!
愛情不是他們生活的唯一,卻是他們唯一的生活。
君臣父子,孰先孰後?煢煢獨立,何枝可依?身懷小怯卻有大勇的男人作為君王的選擇是──愛是救贖,但他卻無力去愛。
‧博大深邃,波瀾壯闊的「晉江第一官推」!
‧豆瓣超高評分8.5!
‧當當網連續五年上榜,永遠的首頁暢銷!
‧連載五年,再修改五年,臻於完美的古言權謀經典!
‧與《琅琊榜》並稱,出版前再度修訂,重磅面世!
‧騰訊年度巨作!作者雪滿梁園親自操刀改編成電視劇!
‧「《鶴唳華亭》良心作/考究/還原」讚聲不斷!掀起超高討論度,甫開播評分就直衝高分,年度良心必追大劇預定!
‧由《錦繡未央》羅晉、《劍王朝》李一桐、《你和我的傾城時光》金瀚等演技派主演!
‧高能反轉,計謀燒腦,好評直追《琅琊榜》!
(上)
太子蕭定權是年少慕艾宮人們口中的傳說,天之驕子俊美的輪廓填補了青春寂寥的芳心,但同樣有名的,是他御下嚴苛,性情乖戾,還失愛於君父,忌憚於兄弟,動輒被皇帝叱罵不忠不孝、毫無心肝。蕭家天下,僅僅是離他很近,她們離他,也是如此。
只有她不同。犯了錯卻因此得到太子青眼的浣衣宮女阿寶,於眾人稱羨中一步登天,成了最受寵的顧才人,可沒人能無緣無故在東宮面前露臉,她為何而來,定權不知,只好折了翅膀,放在眼前看管,卻不意從她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齊王與他之爭已如水火,一封寫給舅舅顧思林將軍的手書,坐實了太子預政弄權之名。當年教他君子之道的老師以身死換他冠禮成人,如今鎮邊數十載的舅舅為他稱病請辭。忠烈以鮮血為他鋪平東宮寶座,他卻坐視不理,因為君子,即是人君,他心狠手毒,犧牲不該犧牲的,好保衛他該保衛的──百姓蒼生。
(中)
長州軍事不利,太子倚仗的舅家閉門去職;近臣當天子及百官面反水,告他干政亂法。此番齊王出手,鐵了心要釜底抽薪,將他斬草除根;縱然事有可疑,但為了打壓外戚收歸軍權,父皇是否也想過乾脆犧牲他?畢竟太子先是皇帝的臣子,才是皇帝的兒子,盡忠方是盡孝。
囹圄之中,定權只許阿寶陪伴,想像春暖時一同去南山觀覽鶴飛綠水,幾乎怕打碎暗室中溫馨的時光。殿下嚮往溫暖,嗜甜怕冷,是個極度驕傲潔癖,聰明多疑,卻也寂寞入骨的男人,可在這深宮,誰能甜他,他又能允許誰暖他呢?
面對至親,定權近乎死板地嚴守儲君的禮際與法度,自絕於和樂天倫,然而他容忍的仁慈成了進逼利劍;自傲難以模仿的書法「金錯刀」變為罪證……陷網密密,無路可逃,望著方寸青天,阿寶說不清自己心意,更猜不到結局,只因她也在局中。命運讓他們是敵非友,幸能相知,不能相惜……
(下)
長門寥落,羊車不至,顧才人被東宮冷落,已經四年了。這期間太子絕地反擊,迫使二哥齊王之藩──卻發現五弟趙王深藏不露,手段更高一籌,他既沒敗,必要你死我活。兄友弟恭、父慈子孝,在萬里江山面前,全奢求不得。
再見阿寶時,定權終於知道了她的來意,這是兩人最親近卻也最遙遠的時刻。他已失去所有可珍惜之物,唯餘一注汙血,數根癡骨,還有這份令人猶豫徘徊的感情。社稷為他己任,他英明賢能,是嫡長天驕,同時也是個會冷會痛,會哭會笑的凡人,但身為一人之下的威嚴主君,孤獨與愛,都不可示人。
朝堂天下,無外乎是,穿上錦繡便是王侯,戴起枷鎖便是罪囚,華麗轉眼翻覆成蒼涼。政治是全身家性命的博弈,與他對決的皆是至親,被當成棋子拋棄的卻是萬民,他辜負眾多,活在人間,卻渾不似人,如何才能對得起那些用生命拱衛他的忠良?此情,又是否可待?
作者簡介:
▋雪滿梁園
不是個做大事的人,就是個做事的人。
章節試閱
鶴唳華亭(上)
蕭定權正垂目,無聊地把玩著手中一柄高麗紙摺扇,待小黃門跑近,懶散開口問道:「找到人了?」小黃門頓從怒目金剛化作低眉童子,柔聲答道:「是,殿下。是浣衣所的宮人。」定權單薄的眼瞼抬了抬,從泥金扇面後抬起頭,側眸望了望身旁一個宮裝麗人,言語之中不乏委屈:「如今的西苑真住不得了,妳看看,連洗衣裳的奴子都會犯上了。」麗人微微一笑,盈盈眉眼頓如流光溢彩一般,對這抱怨並不回應。
李侍長平素聽聞過這位主上的脾氣,嚇得連連叩首道:「是這賤婢冒犯了殿下,罪該萬死。這也都是因為臣管教不嚴,還望殿下念她年幼無知,初來乍到,開天恩恕我兩人的罪愆。」一旁顧氏不語許久,此時卻突然插話:「不干侍長的事,我一人做事,一人承當。」李侍長怒斥:「打脊奴才,妳是王風教化外長起來的嗎?桌上擺個瓷瓶還生著兩只耳朵,妳就不知道『千歲』兩個字怎麼寫,聽也是聽過的吧?還你長我短,妳怕人不知道妳長了這口牙嗎?」
定權教她的罵詞逗得一哂,轉眼看看顧氏,見她不知緣何也一臉委屈,竟然微覺有趣。他此日心情本不算壞,便笑笑對李侍長道:「罷了,妳帶回去,該打該罰,好生管教。若有再犯,妳就是同罪。」
李侍長萬沒想到一樁血淋淋的官司,居然輕飄飄判了下來,見顧氏不言語,忙推她道:「還不快謝恩?」顧氏跪在一旁,任憑李侍長幾次三番地催促,卻始終不肯張口。定權本已起身欲走,見狀便又駐足,微微一笑道:「她一定是在想,既要罰她,她憑什麼謝我,是不是?」顧氏不肯作聲,李侍長恨極怕極,忙在一旁幫襯描補道:「殿下,她從未見過貴人玉容,這是嚇傻了。」定權笑問:「是嗎?剛不還說了話的嗎?」見顧氏依舊沉默,又笑道:「妳看,她並不肯承妳的情呢。」李侍長正不知當如何辯解,定權已經陰沉了面孔,怒道:「把杖子取到此處來,好好教訓這個目無尊卑的奴子。」
適才的小黃門擦了一把冷汗,連忙答應著跑開,片刻便帶過了一手中捧著木梃的內侍。定權站起身,慢慢踱到顧氏身邊,用摺扇托起了她的下頷,細細打量。顧氏不意他的舉止忽然如此輕浮,一張面孔漲得通紅,驀地別過了臉去。
定權嘴角輕輕一牽,也不勉強,放手對李侍長道:「妳說她是教化外人,我看她倒是一身骯髒骨氣。便是到了垂拱殿天子面前,御史臺的那群酸子們怕都要輸她幾分氣概。若是如此,只怕冒犯了她,她未必心下就服氣。」又笑問顧氏:「是嗎?」亦不待她回答,復又坐下,指著李侍長下令:「杖她。」
兩旁侍者答應一聲,走上前便要拉扯李侍長,嚇得李侍長忙連天求告。顧氏剛剛復原的臉色又是一片血紅,咬牙點了兩下頭,方低聲求告:「小人知道錯了,祈殿下開恩寬宥。」定權由少及長,從未遇見這種事,眼見她連耳根脖頸都紅透了,懷疑地問:「當真知道了?」顧氏飲泣道:「是。小人以後再不會犯了。」此事原本並非大事,話既到此,定權也覺得索然寡趣,懶得再作深究,起身揮手道:「交給周常侍發落吧。」
李侍長叩謝完畢,見顧氏一味垂首不語,生怕再惹怒太子,忙扯她衣袖道:「阿寶,還不快謝恩?」定權已走出了兩步,聽到此語,忽然轉身,突兀問道:「妳叫什麼名字?」李侍長忙答道:「殿下,她叫作阿寶,珠玉之寶。」定權愣了片刻,又問道:「是姓什麼來著?」李侍長又代答道:「姓顧,回首之顧。」
兩旁侍者見定權佇立原處,沉默不言,不知緣由,亦無人敢動作,良久才又聞他吩咐:「交給周常侍。」眾臣連忙答應,便要上前拿人,卻又見定權轉身,吩咐那麗人道:「叫周循查查她是哪次遴選進宮的,妳也費心調教調教她,叫她日後到報本宮去侍奉。」
麗人應了一聲,跟隨在定權身後,走出幾步,又回首顧盼。恰逢阿寶亦抬頭,見她素絲單襦,罨畫長裙,頭戴假髻,上無珠飾,額上頰畔卻皆裝飾著翡翠花子,通身裝扮既異於貴嬪,亦異於宮人。察覺到她的打量,麗人的脣角浮現出一絲淺淡笑意,亦含溫柔,亦含嫵媚,如有憐憫,如有諷刺。
待太子一行走遠,李侍長早已癱軟在地,兀自喘息了半日,才勉強爬起身,又扶起了阿寶,問道:「不礙事吧?」阿寶方一點頭,李侍長劈頭便是一掌,怒道:「到底怎麼回事?」阿寶沉默了半日,方敷衍答道:「小人只想無人時到苑內四處悄悄看看,不知怎麼就撞上了。」
她語焉不詳,李侍長自然大起疑心,然而再三盤問,來來去去也只是這三兩句話,初時只覺得她性子執拗,不識好歹,難免又開口罵了兩句。再打量她半晌,若有所悟,搖頭道:「罷,罷,各人有各人的緣法。今天我一心還想替妳開脫,看來只是多事。好在妳的事再不歸我管了,只是休要守著一條道走到黑,以後去了前殿,妳若依然如此,只怕有神佛加持才能全身而退了。」說罷嘆了口氣,仍舊找回了丟下的衣匣,也不再理會阿寶,獨自送到了郭奉儀處。
待阿寶慢慢緣來時路折回居處,浣衣所的一干內人不知從何處已得知了消息,早據守在院門內,見她露面便一擁而上,七嘴八舌問起這事的前後經歷,阿寶仍如前回答。眾人自然不甘心,退而求其次問道:「那殿下的模樣呢?妳看清了沒有?」阿寶搖頭道:「我沒敢抬頭,也不曾看見。」眾人見她神情漠然,已經擺出一副不是池中物的嘴臉,自覺氣悶無趣,眾口嘵嘵了幾句「高飛上枝頭」、「苟富貴,勿相忘」的譏刺言語,三三兩兩各自散開。卻聽阿寶低聲道:「我只看到了他的身邊,有個美人,穿戴和旁人都不相同……」
一個平常好議論的宮人聞言回頭,朝她笑道:「那想必就是我們素日裡說的蔻珠娘子了。」走出了幾步,忽又高聲笑道:「不就是拾了她的牙慧嗎?還要在這裡裝什麼幌子?」另一人隨口接道:「只怕牙慧還是要接著拾,她若肯開善心點化一二,能度出個正果也未可知。」前者冷哼道:「她自己還是孤魂野鬼,連個人身都沒修成,拿什麼度別人?」
內人們雖然嘴上說得不堪,依舊把這當成件極重大事件,聚在一處議論不住:「不想她平日一聲不響,臨事倒果真有些手段。」、「那個陳蔻珠好歹是內人出身,聽說相貌也極美,更何況自殿下元服遷居便近身服侍,也就不說了。可殿下又看上了她什麼?」、「所以我剛說人不可貌相……」
眾人研究半晌,終無成論,便有膽大者引領眾人前去諮詢李侍長。李侍長一腔憤恨,終得以盡數宣洩:「正是我竟日慣得妳們個個皮輕骨賤,尊卑不明,如今才得的現世果報。妳們一個個只管自去求死,不要連累我一世為人不得下場!」見眾人面面相覷,啞口無言,又勒令道:「日後年未滿廿五的,一律不許再當外差。」
隔日,果然有便人攜西苑內侍首長周循之命前來浣衣所提調,一干同僚未受半點澤被,反遭池魚之殃,憤憤然無一人前往送行。
蔻珠本日已換了團領袍,腰上黃外加束革帶,一副尋常內人的裝束,見到阿寶,拉著她的手笑問:「新衣服可還合身?」左右看了看,又道:「妳來得太急了些,只好先領了現成最小的一身,可穿著還是大了。袍子往上折折,帶子束緊些,且耐煩穿幾日吧,我就知會有司替妳量身新做。」阿寶推辭:「不必煩勞娘子,這樣子就很好了。」蔻珠面色一滯,又笑道:「妳這麼叫我,可不是替我惹禍?看年紀我必虛長妳幾歲,妳不嫌棄,叫我聲姊姊也可以,直呼我的大名也可以,我的名字他們早說給妳知道了吧?」見阿寶柔順點頭應承,又笑道:「衣服的事情,卻由不得妳。妳願意替殿下儉省,只怕殿下未必應允。不瞞妳說,殿下平素在這些事上有些留心,妳這幾日還且休到他面前去走動,免得惹他罵妳,彼此都不痛快。」又促膝向她細細傳授了許多太子行止的好惡習慣,又詢問了她來歷、家人等語。阿寶一一記下,亦一一回答。
蔻珠所言不虛,報本宮的規矩果然瑣碎繁冗,首樁麻煩便是太子愛潔成癖,不但以身作則,一日三櫛,更要推己及人,凡舉案上、几上,乃至內臣、內人頭上腳下,目所能及之處,皆要不染纖塵。平素眾人只能見縫插針不停揩抹替換,阿寶亦領悟到當時在浣衣所時差事繁重的原因。
眾人所言亦不虛,太子的脾氣的確不能以「和善」來形容,眾人鎮日戰戰兢兢,在殿內時連大氣都不敢多透一口,生怕一事不慎,便招惹到了這尊碾玉魔羅。阿寶某次將煎好的茶湯進奉,不慎濺了一、兩點在几案上,太子正在寫字,忽將手中筆狠狠一擲,一幅將成法書登時一塌糊塗。滿殿人皆跪地請罪,雖定權提腳出殿半晌,亦無人敢率先起身,直到蔻珠親來傳喚,此事方解。
日日皆有人因小過遭黜罰,日日皆有新面孔接替進入,此處不似浣衣所,根本無人好奇太子殿下何以一時心血來潮揀拔了這樣一名低階宮人。人事的更替,在眾人眼中早已經習以為常。只是阿寶不久後便察覺到,這似乎並非單單源自於太子的焦躁易怒。
秋去冬臨,時迫冬至,定權正在暖閣的書房內撰寫文移,忽有內臣入內報道:「殿下,詹事張大人求見。」定權急忙擱筆,吩咐:「快請進來。」一面加衫整冠,又令左右退出。
阿寶行至書房門前,見一個衣紫橫金,面目頗具文士氣象的中年官員被周循親自引進,隨即閣門緊閉,再無一人近前,不由心生好奇,悄悄問蔻珠:「貴人姊姊,這人是誰?殿下待他怎麼這麼客氣?」蔻珠擺手示意她先勿多語,直到出了殿門,方低聲回答:「這是當今的吏部尚書張陸正大人,兼領詹事府正詹職,殿下平素最看重的就是他。」阿寶點點頭,便不再多語。
周循將張陸正引入書房,見禮讓座後,定權隨口問道:「張尚書是從部中來,還是從府中來?」張陸正答道:「臣自府中來。」又道:「為部中事。」定權頷首問道:「如何?」張陸正答道:「齊藩向戶部舉薦了一人,樞部兩人。臣同右侍力諫,總算壓掉了樞部的兩個,一人轉工,一人外放,想來過兩日便會有敕書。」定權又問道:「朱緣呢,此事他又是什麼態度?」張陸正道:「朱左侍告病,這幾日未至部中。」
定權點點頭,喚他字道:「孟直費心了。」又嘆氣道:「齊藩仗著一向聖眷隆厚,這些年愈發不將本宮放在眼裡了。先皇后在時還好,如今怕是陛下也早存了易儲的念頭,我的處境也是愈發難了。」張陸正勸慰道:「殿下不必懷憂自擾,殿下畢竟是先帝最愛重的嫡長孫,陛下就是不作他想,這個層面總是還要顧及的。」定權冷笑道:「我做這儲君,無非是憑著先帝餘蔭──且我自忖一向並無大的罪過。至於說什麼嫡長,如今齊藩的生母才是中宮,他才是陛下心裡頭的嫡長,我這孤臣孽子,倒不知當把這副業身軀往何處去安插了。」
張陸正已經許久不聞他作這等牢騷私語,一時無言,半晌才勉強應對道:「殿下慎言,陛下與殿下終是父子同體,舐犢之情也總是會存放幾分的。」說罷自己也覺這官話無聊無味,實在難以動人,又道:「臣等總也是誓死擁戴殿下的。」定權聞他此語,倒似頗有幾分動容,道:「孟直,我總是依靠著你們的。」頓了頓又道:「只是父子不父子的話,今後就不要再提了。」張陸正不知道他是否這幾日入宮又受了氣,無話可說,只得回道:「臣遵旨。」
定權又問道:「李柏舟空出來的位置,齊藩有什麼舉動沒有?」張陸正答道:「陛下一直說沒有合適的人選,還待遴選。臣聽朱左侍說,齊藩那邊倒是薦過兩個,陛下並未應允。」定權思忖片刻,道:「將來我總還是要想辦法推你入省的。」張陸正搖頭道:「此事需從長計議,以靜觀天心為上。如今省中風波惡,臣一時是真不敢涉足的。」定權點頭道:「我省得,你放心。」默然片刻又道:「只是枉擔了如此惡名,平白給了他人如此口實,若最終又是為人作嫁,我實難甘心。」
張陸正無言以對,只得偏轉話題,談及新尋到的幾枚晉人手帖,果然才引起定權興致,細細向他詢問究竟是真跡還是前朝摹本。張陸正笑答來日奉上請他親自辨別,再說起冬至當日群臣至延祚宮謁東宮的朝賀儀,這便無非老生常談,說了半日,才告辭出去。
冬至次日,卯時未到,定權便起身,預備入宮去向皇帝請安。蔻珠和阿寶服侍他穿戴公服,見他滿臉憂鬱之色。阿寶至此間三月有餘,已經知道他平素最為難之事就是面聖,每逢此時無名火最盛,也著意比往日多加了幾分小心,免累及眾人受無妄之災。一行人直到目送他出了殿門,為他人簇擁而去,方鬆了口氣,有了禍水東引的快意。
定權乘軺車直到禁城東門東華門外,入門後北向,轉入了前廷與中廷相交的永安門,便見從一旁走過兩個著單窠紫袍,戴烏紗折上巾的人來。年長者二十三、四歲,眉宇之間頗有英武氣象,本已圍黑鞓方團玉帶,鞓上還加一枚玉魚,顯是加恩越級的御賜之物,正是定權的異母兄長齊王蕭定棠。一旁同行的少年,按親王服制佩金帶,眼角眉梢稚氣尚未消盡,卻是與齊王同為當今中宮所出,年內新晉封趙王的五皇子蕭定楷。
兄弟三人見過禮,定棠遂笑問:「殿下這是去給陛下請安?」定權笑答:「正是,既遇到大哥和五弟,不妨同行。」定棠點頭道:「如此最好不過,免得『各自為政』,陛下還要分三次說教。」定權笑道:「就是此話。」一路上兩人低聲說笑,定楷默然跟隨在後,倒是一派兄友弟恭的和睦景象。
及至今上正寢晏安宮外,三人禁聲整肅儀容後,恭立於簷下。少頃,便有內臣出殿通傳天子召見,將三人引入暖閣。
冬至方過,按制旬休,七日內不設早朝,皇帝起得也比平素稍晚,此時方準備用早膳。見定權等人入內,笑道:「想來你們也還沒用過早膳,就陪朕一起吃吧。」忙有宮人前行移案布箸,通傳膳所,為三人在皇帝座下設席。
三人謝恩後分坐,未及舉箸,便聞簾櫳擺動,衣香襲人,閣內含笑轉出一個靚妝貴婦,著大紅短上襦,碧色銷金長裙,雙裙帶長垂至地,高髻未冠,髻上一轉插著十數支花頭金釵,額上兩頰皆貼珍珠妝飾的花鈿,身後簇擁著五、六個錦衣麗服的妙齡內人。
貴婦進了暖閣,左右一顧盼,頓覺脂粉榮豔,顏色驕人。定權三人忙又站立見禮,誦道:「皇后殿下萬福。」皇帝卻無舉動,只是笑道:「妳總算是插戴好了,我們可都不等妳了。」
皇后趙氏睨了皇帝一眼,一雙妙目仍不失清明靈動,猶可想見當時風華。趙氏直走到皇帝案前,方向他虛虛一拜,笑道:「妾齒長矣,忝居小君之位,不事嚴妝,恐汙陛下聖察。」皇帝笑道:「聖察也好,聖鑑也罷。既然是朕的子童,怎麼會老?」皇后微微紅了紅臉,半含嗔道:「陛下,哥兒們可都在跟前呢。」皇帝笑道:「子童對小君,這話引子可是妳先挑的頭。」三人待帝后同席入座,方又重新坐下。
定權見此情景,心知昨夜皇后同宿在晏安宮中,不知緣何,心下漫生出一陣淡淡的厭惡。
皇后落座後悄悄看了他一眼,笑問:「太子一早便從西府過來,可是辛苦了。」定權微一躬身,答道:「臣不敢。」皇后又向齊趙二王笑道:「你們也是,大冷天氣,難為一大早就起來,就多用些吧。大哥兒喜歡鰣魚,正好今日你爹爹這裡有,算是你的口福,只是仔細多刺。」又轉問定楷:「五哥兒喜歡什麼,叫你爹爹賞你。」定楷笑道:「我隨大哥。」
皇帝看著定楷屏退宮人,自己邊挑刺邊慢慢食魚,隨口笑道:「今日無朝,私服即可,何必穿得這麼繁瑣?」定楷投箸答道:「臣等不知陛下賜食,所以未及更衣。」定棠看了看上首定權,笑道:「我們知道殿下一定隆重,是以不敢造次。」皇帝聞言,目光一轉從定權身上掠過,便不再提起此節。轉口復問定棠前日去京郊犒軍的詳情,又問定楷近日出閣讀書之事。
定權見他們夫妻、父子,一派雍雍穆穆,獨襯得自己如同外姓旁人般,只覺骨鯁在喉,隨意吃了幾口,也如同嚼蠟,難辨滋味。皇后含笑看看席間,吩咐內人:「太子愛吃甜食,把梅子薑、雕花蜜煎送去給他,請他嘗嘗。」定權起身道:「臣謝皇后殿下。」皇帝不由面色一沉,譏刺道:「你既然具服前來,為著這些許小事又向你母親用官稱,何不將全套戲作足,也顯得更莊重些?」
定權沉默片刻,果然避席跪拜,重新行禮道:「臣謝陛下,謝皇后殿下。」皇后見皇帝面色愈趨難看,連忙笑勸道:「這是節下,陛下便疼疼哥兒們,好好的又來嚇唬他們做什麼?」又對定權道:「三哥兒快起來,你爹爹是嫌你太過多禮,一家人私底下如此,反倒覺得生分拘束了。你這孩子也是老實過分了,竟然聽不明白。」皇帝置若罔聞,冷眼看了定權片刻,將手中金箸啪一聲撂在食案上,道:「不用擺出這副向隅的態度,你不想留在這裡,無人強你所難。」定權微微一愣,躬身恭謹答道:「是,臣告退。」
餘下幾人見他轉身出了殿門,不由面面相覷。半晌皇后方喚宮人新取了筷子,重新放入皇帝手中,低聲勸道:「陛下又是何苦,太子又不是存心。」皇帝怒道:「妳大可不必替他說話,他就是故意做來給朕看的。妳看他那副嘴臉,天下人都虧欠了他嗎?他眼裡頭可還有朕?」皇后嘆了口氣道:「啼笑皆不敢,做你的兒子,才是真難呢。」
四人接著用膳,一時默默無言,氣氛尷尬。定棠、定楷又偷偷互看了一眼,各自將一枚鰣魚放入了嘴中。
鶴唳華亭(上)
蕭定權正垂目,無聊地把玩著手中一柄高麗紙摺扇,待小黃門跑近,懶散開口問道:「找到人了?」小黃門頓從怒目金剛化作低眉童子,柔聲答道:「是,殿下。是浣衣所的宮人。」定權單薄的眼瞼抬了抬,從泥金扇面後抬起頭,側眸望了望身旁一個宮裝麗人,言語之中不乏委屈:「如今的西苑真住不得了,妳看看,連洗衣裳的奴子都會犯上了。」麗人微微一笑,盈盈眉眼頓如流光溢彩一般,對這抱怨並不回應。
李侍長平素聽聞過這位主上的脾氣,嚇得連連叩首道:「是這賤婢冒犯了殿下,罪該萬死。這也都是因為臣管教不嚴,還望殿下念她年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