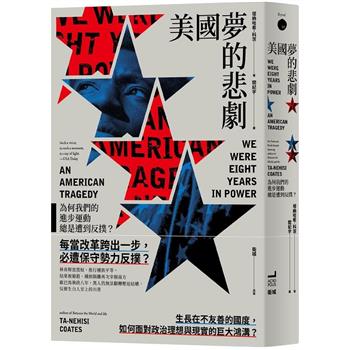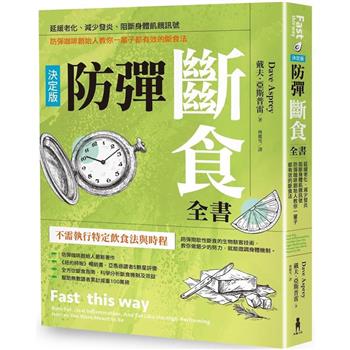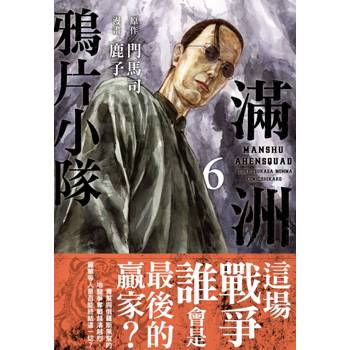第一章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且說阮雲絲將鍾南叫進來,就將屋中所有的丫鬟全都攆了出去,吩咐芳草親自把守著大門,一個人也不許進來。頓時,屋中只剩下鍾家兄妹和芸娘以及她自己四個人。
「妹妹,妳這是……」
芸娘也疑惑了,卻見阮雲絲面上露出笑容,接著笑容就漸漸擴大,到最後,乾脆忍不住得意大笑起來,笑得捧腹彎腰,一隻手直捶著桌子,根本就是笑的停不下來了。
「妹妹……妹妹,妳怎麼了?」
芸娘大吃一驚,只以為阮雲絲是驚怒之下氣瘋了,忙奔上前來抱住她,卻見阮雲絲已經慢慢止了笑,然後搖頭對芸娘道:「妳啊妳啊!素日裡我就不讓妳灌輸他們兄妹這種思想,妳偏不聽,如今可好,哈哈哈……那女人和我那七妹妹,可算是讓妳給坑苦了,哈哈哈……」
「壞了,雲絲真是氣瘋了,這可怎麼辦?」
芸娘急得眼淚都掉下來了,阮雲絲這話雖然聽上去條理分明,但卻是無理之極,不是氣瘋了,還能有什麼解釋?
「胡說,妳才氣瘋了呢!」阮雲絲卻是笑得眼淚都出來了,伸手一抹眼睛道:「好了好了,你們聽我細說,到時候就明白了,唉!也是我,真真氣糊塗了,又總想著將來替秀丫頭的婚事做主,以至於剛聽見這件事,只顧著怒髮衝冠,竟完全沒有反應過來……」
一語未完,就聽門外芳草道:「姑娘,林家派媒婆過來提親了。對了,說是小公爺身邊的小廝掃書家裡人派她過來的。」
「原來掃書本來是姓林的。」阮雲絲點點頭,對芳草道:「放她進來吧!」一邊說著,就正色對鍾南道:「這事兒真是巧了,媒婆子竟是這個時候上門兒。南哥兒,你妹妹的親事,我和你嫂嫂已經定了下來。她和小公爺身邊的掃書兩情相悅,你可覺著有意見?」
鍾南愣了一下,看向妹妹,見她臉紅紅的低著頭,他沉吟了一會兒,便鄭重點頭道:「全憑姐姐和嫂嫂做主。」
阮雲絲點頭,復又笑道:「既如此,芸娘是秀丫頭的嫂嫂,你是她哥哥,這媒婆來說婚事,自然就該和你們說……」
不等說完,就聽鍾南急道:「姐姐,這怎麼成?我們兄妹兩個都是妳的人,自該妳做主……」話音未落,便聽阮雲絲咳了一聲,悠悠道:「糊塗,我是你們什麼人?正經姐姐嗎?不過是你們在我家裡住著,把我當姐姐一樣,但這種婚姻大事,我就是外人,怎麼能做的了主?」
話音落,芸娘和鍾秀的眼睛全都亮了起來,若是到這個地步,她們還不明白阮雲絲打得什麼主意,那可真是蠢笨如牛了。
唯有鍾南,因為不知道事情的來龍去脈,還在那裡奇怪呢!心想嫂子早都說過,我們雖然表面上不是姐姐的奴才,但其實就是,早在姐姐當日付了銀子的時候,我們這一家人就等於是賣給她了,既如此,這件事情自該姐姐做主,怎麼她卻不肯?難道是怕費嫁妝?呸呸呸!鍾南,你真是個豬狗不如得東西,姐姐多少錢都為你們兄妹兩個填了,你怎麼可以這樣想?可……可這是為什麼啊?
可憐毫不知情的鍾南小哥兒因為自己心裡一句無心話,便把自己罵了個狗血噴頭,以至於媒婆進來都說了什麼,他也沒聽進去,只知道跟著嫂嫂點頭答應,然後看著那個媒婆歡天喜地的去了。
這裡阮雲絲心下大定,對鍾南道:「好了,把帳本拿過來給我看看,另外,這一次賣布得的錢不用充進侯府中了,你帶一部份回去發分紅銀子和工錢,以及買米麵肉蛋分發鄉鄰。剩下的留在我這裡,過了年我就打算把京城的雲溪織染廠也建起來,一邊還要為鬥錦大會做準備。是了,南哥兒這次回去,挑最上等的生絲買幾千斤,把我訂下的色譜中一百零六個顏色盡皆染了,你知道的,鮮亮的顏色,尤其是紅、綠那幾種由淺入深的,格外多染些,冷僻的顏色就少染一些,這個我到時候也會給你個大體數目。」
鍾南點頭記下來,接著阮雲絲又問了廠子裡的情況,又和他合計了分紅銀子的數目,又說了下老李家製作織機的情況,還有李懷風又做出了一台印花機,又添了六塊凸版等等之類的雜事。
眼看著就晌午了,阮雲絲便留鍾南在枕香閣用了飯,又對他道:「過年的時候兒就過來吧!秀丫頭和你嫂子都在這裡,沒有把你扔在鄉下過年的道理。廠子從臘月二十就停工,工人們都忙了一年,也該歇歇,讓樓蘭、黃鶯回去和她們丈夫打聲招呼,他們離廠子近,看著別出事就行了。」
鍾南也一一答應下來,接著便告辭離去。這裡阮雲絲送他出門,回來後忍不住又笑起來,對芸娘道:「太太那個人,拚命找一切機會想打壓我,如今她倒是攀上了一條粗大腿,睿王府的小王爺,呵呵!當真是身份顯赫啊!只不過她也太小瞧了我,哼!不把我放在眼裡是嗎?想彰顯自己身為太太的權威是嗎?好啊!我們就看到時候是誰下不來台。」
芸娘奇異道:「我如今自然是明白妹妹的打算了,只是真奇怪,那位侯爺夫人,我也見過兩面的,看上去是個刻薄精明的女人,她這次做事怎麼卻這般冒失?」
阮雲絲冷笑一聲,叫過鍾秀道:「這些日子裡,有沒有人刻意打聽過妳的生辰八字?」
鍾秀想了想,忽然驚訝道:「姐姐怎麼知道的?上個月青竹就問過我,我當時也沒在意,就告訴她了。」說完卻聽阮雲絲冷冷道:「只是問過妳的八字嗎?她就沒問點別的?例如妳和我究竟是什麼關係?」
「姐姐當真是神了。」鍾秀驚訝笑道:「竟連這個都知道。可不是,那日她還問我,怎麼叫姑娘姐姐,難道是認了乾姐妹不成?我就……」
「妳就和她說,不是認了乾姐妹,是當日你們兄妹兩個遇難了,危急關頭正是我出了銀子幫你們還了帳,從那時起,你和你哥哥便等於是賣身給我為奴了。只是雖如此,可我又喜歡大家親近一些,所以你們就叫我姐姐,但實際上卻是我的奴才,是不是?」
鍾秀瞪大眼睛道:「天啊!姐姐,難道……難道妳那天偷偷聽了我們說話?不然……不然怎麼知道的這麼清楚?」
阮雲絲笑容滿面,轉頭對芸娘道:「我說妳把我們家太太坑苦了,妳還不承認。妳聽聽聽聽,這都是素日裡妳灌輸給南哥兒和秀丫頭的思想,如今人家一來打探,這傻孩子就把這話給端出來了。結果讓人家生了誤會,真把他們兄妹當成了我的奴才,既是我的奴才,婚事自該由我做主,而我們那位刻薄精明的太太,名義上還是我的繼母呢!自然就更能做得了主了。」
芸娘和鍾秀這才恍然大悟,接著鍾秀就頹然道:「可……可我真就是姐姐的奴才啊!從妳救下我們那一刻起……」
不等說完,就見阮雲絲擺擺手,然後到門窗處張望了一圈,確定沒有別人,這才小聲歡快笑道:「傻丫頭,這不過是你們嫂子不聽我的,非要對你們耳提面命這些話。妳以為奴才是想當就當的?你們把自己看做奴才,我可沒有這樣想。更何況,說是我的奴才,賣身契何在?連賣身契都沒有,算什麼奴才?妳自然就是個自由人,妳的婚事,除了妳哥哥,誰也沒權力做主,就連芸娘,也只勉勉強強有這個資格,畢竟她又不是妳親嫂子。」
芸娘和鍾秀這才恍然大悟。芸娘又是驚奇又是好笑,低聲道:「這……果然是這樣,只是……只是妳們府裡那位太太,她……她怎的也不問問清楚,就敢冒冒失失做這樣的決定?」
阮雲絲冷笑道:「俗語說,吃一塹長一智。可她吃了那麼多的虧,也沒學會一點兒為人處世之道。哼!這次的事情,對她來說,也的確是料想不到。她從小也是官宦人家的出身,之後嫁進侯府,更是婢僕如雲,哪裡想得到竟有人自稱奴才,卻沒有賣身契呢?更何況,我素日裡和秀丫頭一起織錦,她又手腳勤快,動不動就幹這個幹那個,落在有心人眼裡,這些都是奴才會做的事情,若秀丫頭的真實身份不是我的婢女,怎麼會幹這些活兒?她們這些豪門朱戶中人,有一個算一個,又哪裡知道普通百姓的情義和生活?著了道兒也就不足為奇了。最可笑的事,那母女兩個一心一意要給我當頭一棒,這事兒竟然是做的滴水不漏,大概只等著下了聘禮,事成定局,到時候冷眼旁觀看我的笑話兒呢!我的人,卻是做不了主,讓別人來迎娶了秀丫頭,這可不是丟臉之極。」
芸娘和鍾秀都恨恨道:「這母女兩個好歹毒卑鄙,越是如此,越不能讓她們如願。」
阮雲絲冷冷道:「聰明反被聰明誤,機關算盡,卻算了卿卿性命。哼!這一回,可是她們自找的。我已經讓哥哥去告訴那位小王爺了,他及時收手也就罷了,若是還執迷不悟,到時候鬧得天大笑話,可是與我無關。」
「可……萬一到時候她們就一口咬定了秀丫頭是妹妹的奴婢怎麼辦?畢竟這丫頭曾經親口和別人這樣說過啊!芸娘擔憂的張口,卻聽阮雲絲笑道:「我的奴婢?成啊!把賣身契拿出來我看看,有賣身契,我才承認她是我的奴婢。」
「那,萬一她們誣陷姐姐把賣身契撕了呢?」鍾秀也開始擔心了,這可是關係到自己的終身幸福。
「賣身契撕了?那也無妨,當地保長和裡正家可應該有記錄在案的。你們沒經歷過,不知道這件事,舉凡貴族人家蓄養奴僕,人數姓名籍貫都需要官府記錄在案,鄉下也一樣,這些東西都改由保長或裡正保存,且還要送去官府存檔一份兒,哼!此種事情,豈是他們紅口白牙就能顛倒是非的?』
阮雲絲說到這裡,就站起身冷笑道:「在我這裡做耳報神?哼哼!」說完叫進芳草,冷冷吩咐道:「將那個青竹,打十板子攆出府去,日後不許再錄用。」
「是。」芳草答應了一聲,她心裡也知道這青竹犯了什麼事兒,因此忙下去安排了。這裡阮雲絲眼看著天到晌午,她心頭大事解決了,便微笑道:「好了,命人傳飯。」
※
「太太,這事兒不對勁啊!怎麼三姑娘那邊還是沒有動靜?論理,她早就該跑來問太太了,這種時候兒,難道還能穩坐釣魚台?」綵鳳坐在佟夫人的對面,有些心焦的道。
「由她去。青竹不是說了嗎?剛知道這個消息的時候兒,那蹄子氣得差點兒吐血,人都差點兒瘋了。之後忽然又喜笑顏開的。哼!若真不把這件事情放在心上,怎麼又把青竹攆出了府去?分明心中是恨比天高。如今不過是為了故弄玄虛,讓我們摸不著頭腦,把這件婚事再給退掉,到那時,不但她們得了意,我們也是連小王爺都得罪了。綵鳳啊!我如今方知道,若是不掌著權力,在這府中著實是寸步難行。等著吧!我不但要把那個丫頭嫁出去,就連那沒教養的女人,哼!我一樣也要把她嫁出去。」
綵鳳笑道:「這個自然的,婚姻本就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三姑娘逃過了一次婚,萬萬不敢再逃第二次了。」不等說完,就聽佟夫人惡狠狠地道:「哼!她想逃第二次?她逃得出去嗎?難道這一回我還沒防備,給她逃跑的機會?做夢。」
見她的面孔都猙獰了,綵鳳不由噤若寒蟬,也不敢說話,心道太太心裡恐怕恨死三姑娘了。也是,從她回來後,太太在這個家裡更加連點地位都沒有了,若是我,我也恨。
正想著,忽然又聽佟夫人輕聲道:「劉三出去探聽消息,到現在還沒回來嗎?哼!廢物,不就是一個前夫嗎?竟然到現在都沒打聽出來,這都多長時間了?」
綵鳳忙又安慰道:「太太別急,劉三就一個人,又不敢大張旗鼓的打聽,手裡也沒幾個錢,打聽這種事情自然要花些工夫的,想來也就快要有回信了。」
話音落,就聽一個丫鬟在門外道:「太太,睿王府打發了一個婆子來,說要問太太幾句話。」
佟夫人皺皺眉頭,心道不是才下了聘禮嗎?怎麼又過來了?卻又不敢不接待。於是迎出去,卻見那婆子站在院裡,冷冷淡淡道:「我們小王爺打發我過來,只是想知道,這件事太太是一定做得了主的嗎?怎麼阮小侯爺又和我們小王爺說,讓趕緊退婚,別等到時候來抬人卻抬不到,小王爺說了,他可丟不起這個人。」
佟夫人笑道:「妳回去和小王爺說,放心好了,過幾天直接來抬人就是。哼!一個奴才秧子,小王爺這樣看重她,給了這麼多聘禮,又親自許她做姨娘,還想怎麼著?」
那婆子又看了佟夫人幾眼,點點頭道:「好,有夫人這句話,我們小王爺就放心了,到了日子抬不到人,我們小王爺可唯妳是問。」說完轉身去了,竟是連屋裡都沒進。
這裡佟夫人氣得臉色發青,恨恨道:「真是不懂規矩,這還是王府裡出來的人呢!就這樣不懂事?」說完卻聽綵鳳又道:「太太,這事兒還是慎重些吧!」她怒氣沖沖的哼了一聲道:「什麼慎重?讓明蝶去告訴她一聲,就說聘禮已經收了,庚帖也都換過了,讓她趁早兒把賣身契準備好,我不信,就算我在家裡沒了立足之地,難道竟連這麼一件小事也做不了主了?哼!故弄玄虛,我倒要看看,這話挑明了之後,她還要怎麼弄玄虛。」
於是阮明蝶就去了枕香閣,很快便回來了,對佟夫人道:「那女人真好笑,到現在了,說什麼鍾秀的事情她不管,太太既給她許了人家,這亂攤子就得太太收拾。哼!我真不信了,她自己如今住在侯府裡,就是侯府的人,她的奴才難道就不是這侯府裡的人了?只是娘親,您確實要謹慎些,那女人性格剛強,知道了這樣事,不知怎麼恨呢!當日她既能自己逃婚,今日說不得就能撕毀了鍾秀的賣身契,來個魚死網破。」
佟夫人冷冷道:「撕毀了賣身契就成了嗎?哼!奴才們賣身,那是在各個地方都記錄在案的,她以為撕毀賣身契,我們就沒辦法了,到那時,難道不能讓小王爺去查?只要查實了,她便是要吃不了兜著走。無妨,讓她折騰去吧!青竹當日是問的清清楚楚,那丫頭自己親口說過,是她的奴婢,哼!這還能怎麼有假?何況她素日裡,幹的何嘗不是奴婢們才幹的活兒,妳放心,這一次,管保叫那女人翻不了身。」
阮明蝶心中隱隱約約有一種不太好的感覺,卻又不知這種感覺是從何而來。畢竟她身為侯府小姐,也想不到一個奴婢,竟然會不簽下賣身契這種事,因左右思想了,只覺著萬無一失,恐是自己和母親接連在那女人的手下吃虧,因此心中方惴惴不安罷了,想到此處,就又覺著放寬心了。
其實阮明蝶也算是個聰明的女人,佟夫人雖然不甚精明,但好歹也是仗著丈夫寵愛在這侯府中縱橫了二十年,其狠毒刻薄虛偽更是彌補了智商上的不足。
但是就連阮雲絲都沒想到,這一次的事情,她們母女二人竟會蠢到如此地步,竟還會以為自己在故弄玄虛。
究其根底,就是深植在兩人腦海中的主奴觀念太過強烈,所以認定了世上人也不可能會有人這麼好心。就算是好心,當別人主動為奴,也萬萬沒有不收的道理,不然白白供養了兩人吃喝,又不能當主子發號施令,世上有這樣的傻子嗎?
那小王爺李觀魚不過是要納鍾秀為姨娘,只因愛她貌美,為了籠絡美人之心,所以格外鄭重,還換了庚帖下了聘禮,不然的話,直接給了銀子,一頂小轎抬走就是。
即便如此,小王爺心急之下,又怕夜長夢多,也是早早定好了日子,只說五天後那個好日子必定要來侯府抬人,他實在是一刻也等不得了。
阮雲絲並不知道對方來抬鍾秀的具體日期,阮明蝶也不可能告訴她,只不過她也有她的辦法,那就是:第二天便把鍾秀給放出去了,讓阮思齊親自帶了她去國公府,找蘇吟玉,名義上是做客,暗地裡自然是避開那場紛爭,不然的話,小王爺要是公然搶人怎麼辦?難道蘇名溪能為掃書在那個時候出頭?很顯然,蘇小公爺和阮雲絲都沒有蠢到那個地步。
因此五天後,佟夫人和阮明蝶就徹徹底底的悲劇了。
| FindBook |
有 3 項符合
錦心繡手(5)的圖書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錦心繡手(5)
起點女頻累積二百三十萬人次點擊,推薦總榜第一名!超高人氣!
這天底下再也沒有再比阮雲絲前夫──張靈信,更厚顏的人了。
休書在手,他竟還有臉上門求娶。
可惡她那處心積慮想把她趕出門的嫡母,竟自做主張的為這婚事做了主。
這兩人滿心恨意千般算計,眼看阮雲絲這一次就是插翅也難飛了……
鬥錦大會中阮雲絲果然以「雙面錦」打敗了其他高手,奪下了冠軍。
這更也讓她坐實了「織女」的這個名號。
可鋒芒太露果然不是件好事。
皇上念她溫柔嫻淑、心靈手巧,竟將她賜婚予戶部吏部尚書甄言的義子──張靈信
。
一紙聖旨,讓阮雲絲暈厥不醒,整顆心都支離破碎,她知道這一次她真是板上釘釘,無路可走了。
可那正還遠在邊疆,為國浴血奮戰的蘇小公爺呢?
當他凱旋歸國,知道他心愛的女子已被皇上賜婚,又該會是怎樣的傷痛欲絕?
作者簡介:
梨花白
大陸原創網站知名新銳作家,風格輕鬆細膩,文筆流暢,人物形象美好生動,故事中的感情甜蜜溫馨。
本立志成為一名筆鋒犀利擅長寫虐戀的深沉流作者,然而受自身資質和性格所限,最終成為了一個擅長寫勵志過日子,歡喜冤家的小白流作者。
愛陳坤,愛美食,滿腦子天馬行空的幻想,經常會有神來之筆的構思橫空出世。
★ 種田文始祖黎花白,繼《妻高一籌、妾居一品》後,全新強檔宅鬥種田文
★ 暢銷作品:妻高一籌、妾居一品……等
章節試閱
第一章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且說阮雲絲將鍾南叫進來,就將屋中所有的丫鬟全都攆了出去,吩咐芳草親自把守著大門,一個人也不許進來。頓時,屋中只剩下鍾家兄妹和芸娘以及她自己四個人。
「妹妹,妳這是……」
芸娘也疑惑了,卻見阮雲絲面上露出笑容,接著笑容就漸漸擴大,到最後,乾脆忍不住得意大笑起來,笑得捧腹彎腰,一隻手直捶著桌子,根本就是笑的停不下來了。
「妹妹……妹妹,妳怎麼了?」
芸娘大吃一驚,只以為阮雲絲是驚怒之下氣瘋了,忙奔上前來抱住她,卻見阮雲絲已經慢慢止了笑,然後搖頭對芸娘道:「...
且說阮雲絲將鍾南叫進來,就將屋中所有的丫鬟全都攆了出去,吩咐芳草親自把守著大門,一個人也不許進來。頓時,屋中只剩下鍾家兄妹和芸娘以及她自己四個人。
「妹妹,妳這是……」
芸娘也疑惑了,卻見阮雲絲面上露出笑容,接著笑容就漸漸擴大,到最後,乾脆忍不住得意大笑起來,笑得捧腹彎腰,一隻手直捶著桌子,根本就是笑的停不下來了。
「妹妹……妹妹,妳怎麼了?」
芸娘大吃一驚,只以為阮雲絲是驚怒之下氣瘋了,忙奔上前來抱住她,卻見阮雲絲已經慢慢止了笑,然後搖頭對芸娘道:「...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