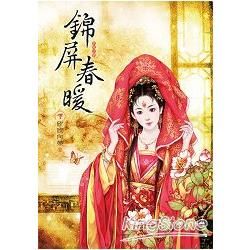第一章 計量
梅鶴鳴現如今是更加搞不清宛娘的性子了,打從這回撞了頭,竟跟變個人似的。說她冷,夜裡帳中之事也算順遂,令他這幾日心情甚好。要說她熱,平常一兩句冷言冷語,從那小嘴裡鑽出來,尖得跟刀子一樣,令他愛不得恨不得。這會兒聽聲氣倒又像吃味了似的,真真令人拿不准,卻知道哄她總沒錯。
想著,他便挨到宛娘身邊兒上道:“怎又惱了,這又是從何處而起,京裡哪有什麼爺的妻妾相好,便是有,爺如今心裡除了親親宛娘哪還容得下旁人,這味兒吃得毫無道理。”
宛娘卻不聽他的辯解,往裡挪了挪身子,刻意離他遠些道:“你也莫當我是個蠢婦一般哄我,什麼事我不知道,你嘴上抹了蜜一樣,成日哄騙與我,什麼捨不得丟不開,這會兒說要走,抬抬屁股走你的就是了,卻非要打這樣的謊做什麼?”
梅鶴鳴心裡轉了幾轉,忽然明白過來。這些日子兩人倒算恩愛,推測著宛娘這一想開,或許是對自己著了緊,這意思難不成是想跟他回京不成。
梅鶴鳴何嘗沒動過如此心思,只京裡面朋友故舊多,趕上過年,難免要應酬往來,哪有空陪她。再說,也著實不好安置,梅府,想來宛娘必然不進,外頭的宅子撂她一個人住著,大過年的孤清清,連個說話的人都沒有,豈不難過。回頭性子一上來,再跟他鬧一場,可難消受,倒不如在青州裡,還更自在些。
他想到此,便忙道:“爺哪裡打什麼謊,宛娘如今還不知爺的心嗎,只京裡人雜,恐妳不慣。妳也莫怕一個人在青州府冷清了,我已知會了陳子豐家的娘子,他那個娘子倒最是個穩重隨和的性子,又比妳大上幾歲,妳跟她相交,倒也相宜。妳若煩了,去她那裡走走,也能解解悶。爺應妳,早早回返,趕在十五之前必歸。咱們這青州府有個大熱鬧,每年正月十五的花燈節,通宿要鬧個幾日,爺回來正巧陪妳出去逛燈市。妳這身子剛好些,如今外頭寒冬臘月滴水成冰,若跟著爺去,在路上凍病了,爺可不要心疼了。”
宛娘心裡暗暗冷笑,說白了,就是不知道該怎麼安置她。妻不妻,妾不妾的,想他家不定就是個世家大族,規矩極大,便是他在這青州府裡荒唐胡為,到了京裡,勢必要收斂一二,嘴裡說得天花亂墜,不過當她是個消遣的物件罷了。
只他既吐口自己可以出門走走,倒也算掙來些福利,宛娘相當清楚,就是梅鶴鳴如今怎樣寵她,有些事也不可能讓她做主。這就是男人,這個社會的男人擁有絕對的權利,不甘心也沒輒。
梅鶴鳴見她小臉略緩,胳膊一伸把她摟在懷裡:“可不許再使性子,爺這就走了,這一走少說也是月余光景,宛娘還要跟爺彆扭什麼,今兒外頭冷呢,不如咱們早些安置了吧!”說著他便讓人整治床鋪,攜著宛娘的手入了那紫錦帳中,至次日日上三竿才起來梳洗。
剛吃了早上飯,外頭便傳了話進來:陳府的小廝柱兒捧了拜匣來,說他們家大人在府裡擺了宴席,請爺過府吃酒,也算個送行酒,周大人幾個現已在哪裡了。
梅鶴鳴知道這是陳子豐讓自己帶著宛娘過去走動,也順便見見他家女眷,日後好往來方便,便接了帖兒,讓人前頭說收拾了就過去。
回身他對宛娘道:“難為他有心,才說了就來請,今日妳跟我過去走走也好。”說著掃了一眼她的穿著打扮道:“大過年的,不好打扮得過於素淨了,挑件鮮亮喜氣的衣裳才應景兒。”
吳婆子忙服侍著宛娘換衣裳,一時收拾妥帖,出了外間。梅鶴鳴再瞧,不禁滿意的點點頭。這才多少日子,他的宛娘倒更加出落得標緻了,且如今去了怯懦之態,顧盼間銀盆一樣的小臉上眉眼盈盈,如江南的三月春水,說不出的一番嫵媚風情,真個讓人怎能不愛到骨子裡去。
梅鶴鳴從吳婆子手裡接了斗篷替她披上:“這會兒外頭冷呢,小心凍著。”攏好風帽,攜著她的手走了出去。兩人過二門直到了大門前,兩乘暖轎抬著,出了王家巷往陳府去了。
陳府所在的新橋巷,隔著王家巷不遠,過了三條街拐個彎便是了。乃是一處前後三進的宅子,陳子豐雖放了這青州通判,也算個肥差事,常有人打官司來往,求上門來,銀子也便得了不少,況且他靠著梅鶴鳴這個大財主,每每應酬,哪輪得上他使銀子,倒是回回落個輕鬆。
無奈家底兒薄了些,當年為了跑這個官兒,把家裡僅剩的那點兒物件都換了銀子送禮,上青州來時,手裡便打著饑荒呢。這宅子還是湊了銀子添置的,也掂量著在這青州也不見得就能長久,如今又從梅鶴鳴那兒得了升遷謀職的信兒,更不會白費銀子置辦新宅。故此,雖身為通判,這宅子比梅鶴鳴王家巷的宅子還要小些,倒是收拾得不差。
到了大門前,早有那幾個在外迎候著,宛娘的轎子卻沒落下,直抬了進去。有吳婆子跟著,陳夫人身邊的婆子接著,梅鶴鳴倒也放心,只叮囑吳婆子小心些,便跟著陳子豐幾個到前頭廳裡吃酒敘話。
再說宛娘,好容易出來放放風,打從上了轎子,便掀開窗簾往外瞧了一路。常日總聽李家婆娘說這青州府如何如何繁華,何曾親眼見過,便是那日來牢中探王青的時候,也不過匆匆而來,忙忙就去,哪有心思打量這青州府。這會兒看來,卻是繁盛之地,道路寬闊、房屋氣派,往來人等,即便販夫走卒穿戴也乾淨齊整,沒有絲毫困頓之相。
想想也是,古來南北往來皆靠水路通行,這青州府臨著水,交通便利,自然繁盛,自己若想跑,這通達的水路倒可優先考慮。若順水南下,出了青州府地界也不難,若南邊跟她想的那樣,逃出生天再謀個安穩。梅鶴鳴的勢力再大,也不是手眼通天,自己若能逃出這青州府,到南邊改換個名姓,不信他能找到。或許開頭會發狠的尋她,若一日兩日甚或三月四月尋不見,哪有如此大的耐心,說不得便丟開手,從此兩便了。
正想著,忽聽吳婆子在外小聲道:“奶奶到了。”說話兒轎子落下,打起轎簾,扶著宛娘出了暖轎。
說起這位陳子豐的夫人,莫怨梅鶴鳴說,卻是個賢良溫婉的婦人。乃是陳子豐得中之年,跟他同榜的進士,姓張叫張恩的嫡親胞妹,因知陳子豐尚未成親,便給妹子保了這門親事。
陳子豐那時正缺倚傍,那張恩的父親雖說只是個縣丞,可大小也是個官身,娶妻娶賢,打聽得張恩的妹子是個穩妥的女子,便應了。
成親之日挑開蓋頭一瞧,見模樣也算齊整,難得更是性子溫婉,也頗合心意,過門後操持裡外,妥妥帖帖,膝下只得一女,過了年才五歲。
這吳氏也果是個大度賢良之人,慣不會做那等拈酸吃醋之事,便是陳子豐在外如何胡為,她也不曾說過一字半句,倒更加得了陳子豐幾分敬重,把個妾所出庶子養在吳氏身邊,有個什麼心腹事也跟她商議。
宛娘這個事,陳子豐回來就跟吳氏說了,吳氏不禁道:“一個外頭的婦人罷了,怎麼梅公子如此看重,巴巴的做了你這個人情?”
陳子豐道:“妳莫要輕看了她,別瞧著是個寡婦,可盡有的手段。如今梅公子連明月樓都不去了,竟是一門心思都跟她過起了日子。這回是趕上過年,不得不回京,怕這婦人獨個在府裡鬱卒,才想起我這裡,念著妳大度隨和,故此讓妳多陪著她往來走動,卻要好生待承。告訴底下的人,別話不妨頭的胡亂嚼說,這位如今可真真是梅公子的心頭好呢。”
吳氏不禁暗暗納罕道:“若真如此,怎不納進府去,豈不兩便。”陳子豐道:“前一陣倒是聽著有這意思,還說請杜大人做個現成大媒,不想那寡婦卻不應,也不進府,白等在王家巷新置了一座宅子。”
吳氏道:“依著你這麼說,這位莫非很是刁鑽厲害的主兒了。”陳子豐道:“倒也照過一面,瞧著倒是體面模樣,底細的性子,我一個外人怎得知曉,妳只記得莫怠慢了她,也就是了。”
這吳氏得了老爺的話兒哪還不能上心,在裡面聽著信兒,忙著就迎了出來,立在二門首,一眼就瞧見了吳婆子。吳婆子她自是認識的,知道她是來祿兒的娘,在梅府裡很有些體面,如今竟然侍候了這位,可見是得了梅公子的意。
見吳婆子攙著人出了暖轎,忙打迭起精神迎了上去,打頭照了個面,微微打量一遭。只見,外頭羽緞狐狸毛裡兒的斗篷裡是件大紅通袖妝花錦緞的袍兒,下頭玄丁香色織金裙兒,裙擺微動,露出腳下遍地金扣白綾軟靴,好一雙小巧的紅鴛小腳,頭上梳了挑心髻,當中戴了支赤金拔絲觀音,右戴一支紅寶石絳桃,兩點兒赤金鑲火玉的墜子,垂在耳側,映著一張白淨小臉,說不出的端莊標緻。只這一身穿戴,就可瞧出梅公子有多著緊了。
吳氏忙笑道:“一早聽說妹妹要來,我就盼著,不想這會兒才到了。這酒席可都擺下半天了,來來,妳我姐妹裡面吃酒敘話。”
吳氏攜著宛娘的手進了後宅,說說笑笑很是親熱,彷彿兩人並非頭一回見,而是親近的手帕交一般。
雖是內眷也正經八百擺了席,擺在裡面花廳,相陪的除去吳氏尚有兩個挽著婦人髻的女子,比吳氏年紀略小些,瞧著也有二十一二了,姿色都算不差,吳氏一一指給她。
穿著豆綠金沿邊兒比甲,肌膚微豐,白淨圓臉的是方氏。另一個穿著銀紅比甲,瓜子臉,丹鳳眼的是蔣氏。吳氏穿著一件紫丁香灰鼠皮的對襟襖,紫綃翠紋裙,比之兩個妾侍,更顯貴重大方。
宛娘暗度吳氏,跟這兩個丈夫的妾侍倒真跟姐妹一般,三人想來事先得了囑咐,並未把宛娘低瞧,親親熱熱的一味勸酒吃。宛娘推脫不過,吃了兩小盅下去,吳氏待要勸第三盅。
吳婆子忙上前攔道:“不是辜負了夫人的情兒,我們家奶奶著實吃不得多少酒,若是這盅子吃了,說不得就真醉了。爺剛才還特特的叮囑了老奴,不讓奶奶多吃酒的。”
吳氏沒說話,那蔣氏笑道:“早聽說宛娘妹妹是梅公子的心尖子肉,常日還不理會,如今可不得不信了。聽我們家爺說梅公子是個千杯不醉的海量,宛娘妹妹怎能就這點酒量,今兒天寒,這盅子又小,酒也是果酒,溫過早散了酒氣,再吃些也不妨事的。”
吳氏也笑道:“蔣妹妹說得是,再吃了這一盅,咱們便聽曲兒耍吧!我們這府裡雖比不得梅府,個個丫頭都能彈會唱的,卻也有兩個通些音律,平日侍候我們爺的,今兒前頭尋了外頭院裡的,就用不著她兩個,倒便宜了咱們,也消遣消遣。”
宛娘只好吃了,這酒的確是果酒,有種香香甜甜的味道,也不很難吃,吃下去覺得身上暖暖的舒服,
宛娘既不吃酒,吳氏便讓撤了下去,另讓人擺上四碟細點、果脯等物,讓丫頭捧了熱茶來,親手遞與宛娘。
| FindBook |
有 2 項符合
錦屏春暖(下)的圖書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錦屏春暖(下)
老娘穿越來沒有美男相伴就算了,身邊還一堆渣男,這跟電視上演的不一樣啦!
封建社會這個大染缸中,宛娘憧憬的一生一世一雙人,瘋狂的她自己都不相信,豪門世家的梅鶴鳴會為他自請出族,只為成全她的夢!
正值這份熾情燙烙得她百抓撓心之際,前緣王青的報復,身份忽轉千金貴女的惶恐,太后指腹為婚安鳳宣的故意攪亂,繁華喧囂落幕,宛娘能否守護著她的幸福?
作者簡介:
欣欣向榮
徹底的熟女,除了旅行不輕易出門的奼女,已有向腐女發展的趨勢,生活極度無聊。
閱讀、碼字、聊天看視頻外就是無止境的幻想。
幻想自己能穿越,能重生,能成為萬眾矚目的明星……
雖然這只是空想,但正在我的書中一一實現著。夢想其實不遠,只要努力,總會實現!
★ 晉江知名作家,前作備受好評,新作火力全開!
★ 暢銷作品:茶家閨秀、桃花宛后……等
TOP
章節試閱
第一章 計量
梅鶴鳴現如今是更加搞不清宛娘的性子了,打從這回撞了頭,竟跟變個人似的。說她冷,夜裡帳中之事也算順遂,令他這幾日心情甚好。要說她熱,平常一兩句冷言冷語,從那小嘴裡鑽出來,尖得跟刀子一樣,令他愛不得恨不得。這會兒聽聲氣倒又像吃味了似的,真真令人拿不准,卻知道哄她總沒錯。
想著,他便挨到宛娘身邊兒上道:“怎又惱了,這又是從何處而起,京裡哪有什麼爺的妻妾相好,便是有,爺如今心裡除了親親宛娘哪還容得下旁人,這味兒吃得毫無道理。”
宛娘卻不聽他的辯解,往裡挪了挪身子,刻意離他遠些道:“你也莫當...
梅鶴鳴現如今是更加搞不清宛娘的性子了,打從這回撞了頭,竟跟變個人似的。說她冷,夜裡帳中之事也算順遂,令他這幾日心情甚好。要說她熱,平常一兩句冷言冷語,從那小嘴裡鑽出來,尖得跟刀子一樣,令他愛不得恨不得。這會兒聽聲氣倒又像吃味了似的,真真令人拿不准,卻知道哄她總沒錯。
想著,他便挨到宛娘身邊兒上道:“怎又惱了,這又是從何處而起,京裡哪有什麼爺的妻妾相好,便是有,爺如今心裡除了親親宛娘哪還容得下旁人,這味兒吃得毫無道理。”
宛娘卻不聽他的辯解,往裡挪了挪身子,刻意離他遠些道:“你也莫當...
»看全部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欣欣向榮 繪者: 書亦飛
- 出版社: 欣然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4-08-13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320頁
- 類別: 中文書> 漫畫/輕小說> 羅曼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