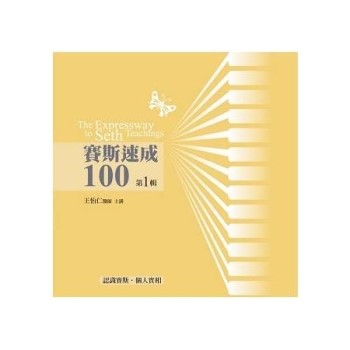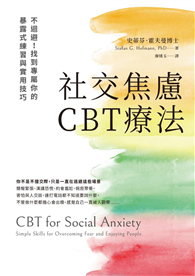書摘/試閱第一章 今生的表兄
嚴清怡掏出荷包數出二十文正要交給他,忽聽面前有人道:姑娘有所不知,這筆最好買新的,回去用墨養著,寫起字來才順手。別人用過的筆,不管是筆鋒還是筆勢都不合自己習慣,不好不好!
抬頭一瞧,卻是個約莫十七八歲的青年男子。
男子身量中等,穿一身象牙白繡了亭臺樓閣的直綴,腰間系著寶藍色腰帶,上面掛了香囊荷包等物,還有塊古拙的黃玉。
黃玉雕成樹葉狀,發出晶瑩潤澤的光芒,一看就知道是塊好玉。
男子側頭又斥夥計:你這人不講道理,是不是欺這姑娘不懂筆墨,哪裡有將舊筆賣人的?我去找你們掌櫃的理論。
夥計立時鬧了個大紅臉,對嚴清怡道:姑娘,實在對不住,敝店以往並沒有賣舊筆的例,這筆確實不能賣與妳。
不關你的事,是我教小哥為難。嚴清怡抱歉的笑笑,將筆還給他,抬頭對那男子道:公子比起晉惠帝,實在是有過之而無不及。拉了薛青昊道:咱們去別家看看。
那男子搖頭晃腦做嘆息狀,道:這濟南府果然粗陋之地,大庭廣眾之下拉拉扯扯,有悖聖人教導,可悲可嘆,痛哉痛哉!
嚴清怡本不欲多事,聽得這話,停下步子嘲道:古人所言不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公子是何等人,一聽便知。
男人正欲辯解,旁邊與他結伴之人忙攔住他道:二弟別說了。又含笑對嚴清怡揖一下:姑娘恕罪,我兄弟心直口快,並非有意唐突,恕罪恕罪。
心直口快?
豈不就是說她之所為就是粗陋無狀了?
那人顯然也意識到了,連忙又作揖道:對不住,對不住,我兄弟讀書讀得迂腐,我卻是胸無點墨不會說話。
嚴清怡見他神情誠懇,沒再吭聲。
走出一段距離,薛青昊問道:姐剛才說的晉惠帝是誰?
嚴清怡笑著解釋道:他是晉朝時的一個皇帝,當時百姓因為饑荒吃不上糧食,官員報到朝廷,晉惠帝說既然沒有糧食,為什麼不吃肉粥……咱們要是銀錢富餘,又怎麼會圖便宜買舊筆?
薛青昊沉默片刻,道:要不算了吧,讀書太費銀錢,家裡樣樣都得靠姐,姐太辛苦了。
嚴清怡親昵的拍拍他的肩,道:你不學著讀書認字,以後怎麼看兵書?如果去遼東或者漠北,怎麼往家裡寫信?要是當了大官還得往朝廷寫奏摺,反正不進學堂不用交束脩,就點筆墨錢,一年下來花費有限。
薛青昊想想有道理,鏗鏘有力的道:姐放心,我一定會上進,以後好好孝敬娘,孝敬妳。
嚴清怡笑一笑,尋到另外一家文具舖子買了紙筆等物,回家前,又買了十斤祿米兩斤粳米和二兩五花肉。
薛青昊不用嚴清怡動手,自己揹著米袋子,拎著麻繩,吭哧吭哧回了家。
薛氏把五花肉分成兩份,一份切成肉粒炸了豆醬,另一半切成片炒了個水芹菜。
中午就著稀飯吃了芹菜炒肉,晚上吃炸醬麵。
薛青昊吃了個肚子溜圓,滿足的舔舔嘴邊的醬渣子對薛氏道:真好吃,什麼時候喊林大哥來吃飯,娘也做炸醬麵吧。
薛氏嗔道:炸醬麵上不了席面,哪裡好待客?我看上次阿清做的那個乾絲湯挺好,要是林教頭喜歡吃,請他得便過來就是。
那我明天就告訴他。薛青昊歡喜得答應了。
第二天一早,薛青昊又去了府衙。
薛氏與嚴清怡坐在院子裡挑揀祿米中的沙子。
萬晉朝官員的俸祿有銀子也有米絹,通常用作祿米的都是陳米,或者裡面摻雜了沙粒,雖然吃著不好吃,但價錢上要便宜許多。
薛氏蒸米飯或者煮大米稀飯的時候,往往再抓一把粳米進去,這樣味道能好一些。頭低久了,嚴清怡的脖子又酸又痛,正打算起身緩一緩,忽聽門外有人叩響了門環,問道:請問,薛氏素真住在這裡嗎?
嚴清怡一愣,下意識的看向薛氏。
薛氏閨名素真,不過已經十幾年沒人這麼叫她了。
嚴清怡疑惑的走出去,就見門口林林總總站了七八個人,叩門的是個十五六歲丫鬟模樣的人。
見有人出來,丫鬟謙卑的笑笑,指著旁邊一位三十七八歲的中年婦人道:這是我家太太,前來尋找薛氏素真,不知她可是住在這裡?
不等嚴清怡回答,身後已經傳來薛氏的聲音:大姐,是大姐?
那中年婦人連忙上前,一把抱住薛氏道:三妹,果然是三妹,我這苦命的三妹,讓姐找得好苦啊!
兩人抱頭痛哭。
嚴清怡恍然,原來這婦人便是薛氏惦念已久的大姨母。
想必已經打聽到薛氏和離了,所以見面就說苦命的三妹,還能找到這裡來。
可門口並非說話之地。
嚴清怡扯一下薛氏的衣襟,笑道:娘,快請姨母他們進屋坐。
薛氏這才反應過來,連忙拭了淚,拉住大姨母的手往裡走,邊走邊道:這是我的大女兒,叫嚴清怡,前幾天過了十二歲生日。
大姨母細細打量嚴清怡兩眼,點點頭道:相貌隨妳,我看著比妳年輕時還俏麗。薛氏將大姨母讓到廳堂正首位的椅子就坐。
嚴清怡上前恭恭敬敬的行個禮,道:見過姨母。
大姨母將她拉在身邊,再看幾眼,贊道:好孩子。
旁邊丫鬟極有眼色的遞上一個海棠木的盒子。
大姨母將盒子塞給嚴清怡,道:一些小玩意兒,留著玩吧。又擼下腕間一個綠汪汪的翡翠鐲子,硬給嚴清怡套在手腕上,道:我家裡一窩小子,就眼饞個閨女。
嚴清怡笑著道了謝。
大姨母揚手將站在廊簷下的幾人叫進來,道:這是我家那幾個不成器的,快,都進來見見三姨母和你表妹。
門外順次走進三人。
嚴清怡一看,巧了,前面兩人正是昨天在水井胡同見過的。後面那個年紀跟薛青昊差不多,倒是頭一次見。
大姨母指著他們順次介紹道:老大陸安平……
陸安平?
不過是簡簡單單三個字,卻好似晴天霹靂般在嚴清怡的耳邊炸響。
嚴清怡腦子頓時嗡的一聲,前世各種事情如潮水般奔湧而至。
怎麼可能?
在這個地方遇見他,而且還是今生的表兄?
嚴清怡茫然的望過去。
陸安平約莫二十出頭,穿件雨過天青色的直綴,中等身量,方正臉兒,眉宇疏朗唇角開闊,既有文人的溫文爾雅,又隱隱透出一股豪邁氣概。
記得二哥羅雁回曾說他直爽豪氣,數次督促他上進;父親也曾誇他若春風沂水。
大姨父祖籍江西,前世羅雁回說陸安平是宜春人。
兩相對照,不是他又是誰?
他與羅雁回稱兄道弟,在羅家白吃白住兩個月,然後一本狀紙洋洋灑灑寫了四頁,將羅家害得家破人亡。
嚴清怡心潮翻湧,心怦怦跳得厲害。
在牢獄裡她曾無數次想過當面質問他究竟有沒有良心道義,想將他剖心剝皮,看看到底是黑的還是紅的。
此時人就在眼前。
嚴清怡再忍不住,脫口罵道:你這個兩面三刀口蜜腹劍的無恥之徒,良心都讓狗給吃了?
一言既出,滿屋人都驚嘆了。
陸安平更是懵懂,愕然的問道:表妹為什麼這樣說?昨天固然是我跟二弟言語不當冒犯了表妹,可總不至於兩面三刀吧?
薛氏也板了臉嗔道:阿清,到底怎麼回事,哪有這樣跟表哥說話的,還不快賠個不是。
嚴清怡矇在當地,腦海裡紛亂如麻,一時竟分辨不出身在何處。
彷彿仍是在羅府,她冷著臉訓斥失手打碎瓶罐的小丫鬟;又彷彿是在牢獄,一眾人圍住蘇氏哀哀地哭;一晃眼又是在陰森森的柴房,滿臉橫肉的婆子擼起袖子一掌摑在她臉上,道:再讓妳手賤,還敢不敢吃裡扒外了?
種種情緒紛遝而至,嚴清怡茫然的看著周圍,不知該如何辯解。
薛氏扯著她的袖子催促道:快,給表哥賠個禮。
這怎麼可能?
陸安平害她家破人亡,她怎肯跟他賠不是?
嚴清怡甩開薛氏,提著裙子沖出門外。
六月的天,驕陽似火,路旁樹木被太陽曬得低垂了枝葉,夏蟬無精打采的叫著知了,知了。
嚴清怡卻好似置身冰窟,從心裡往外絲絲透著寒意,沒有一點溫度,也找不到可以暫歇的去處。
走在街頭,看著行人來來往往,嚴清怡心底一片茫然。
不管前生如何,這一世什麼都未曾發生過,她實不該這樣橫加指責,可要怎樣跟薛氏與大姨母解釋?又要如何阻止陸安平與羅雁回見面?
嚴清怡毫無頭緒。
正煩惱著,忽覺肩頭被人拍了一下,接著傳來一個戲謔的聲音:老遠就看出是妳,果然沒有認錯。
嚴清怡回頭,看到身穿緋衣,搖著象牙摺扇的李實,頓時心生警惕。
李實瞧出她的戒備之意,切一聲,道:怕什麼,就妳這身量,二爺我真想動手,妳還能跑得了?只不過二爺應了人,以後絕不碰妳一個手指頭,呶,看清楚了,我剛才用扇子敲的,沒動手。
有了前車之鑑,嚴清怡根本不敢相信他,眼角掃過樹蔭下挑著籮筐賣西瓜的幾個農夫,慢慢往那邊挪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