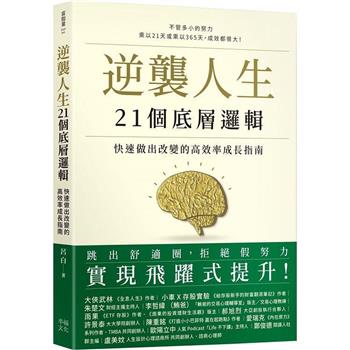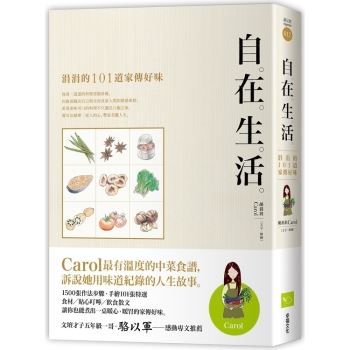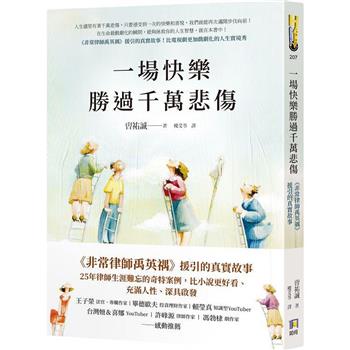第一章 血義
越往西走日頭越烈,草地也越乾涸。原本李宸昊還能嚼嚼草根緩解一下饑渴,現在卻連枯草也找不到幾棵,就是偶爾找到了也沒有一點水份。
吃地更是寥寥無幾,李宸昊每日裡只能以強忍著饑餓感,實在忍不了了才去咬一小口乾糧。
省下的乾糧他用水泡軟了泡稀了餵給木謠,好在乾糧還夠她吃個十餘天的。可水囊裡的水也越來越少了,最多只夠喝一天的了。
咻……馬兒發出最後一聲悲鳴,倒在了地上,馬車也跟著晃了幾晃。
李宸昊一個飛身閃下去,用肩膀扛住車轅穩住了馬車。
抽了幾鞭子後,馬兒只是抽搐了幾下就一動不動了。如此也沒了別的法子,他只能一刀斃命了牠。
涓涓的血流了出來,這種紅色的液體帶著濃重的腥味,讓他噁心。可是早已乾裂的喉頭讓他沒有半點猶豫,趴上去吸吮血液。
幾口下喉後,濃重腥鏽味讓他腹內翻滾,他再也忍不住了,扭頭趴在一邊嘔起來。肚子裡哪還有一丁點食物,只嘔出了幾口混著血的粘液。五臟六腹翻江倒海地疼,他趴在地上痛苦地急喘著。待痛苦稍稍緩解了一點,他又不得不強撐著站了起來,一點點走到馬車旁,掀開簾門。
望著仍在昏迷中的木謠,李宸昊更是心焦如焚,他胡亂地抹了一把臉,發誓一定要把木謠帶出這片戈壁。
然而一眼望去,到處都是單調的土黃色,連一棵草都沒有。此時已近中午,太陽升得老高,曬得地皮直冒煙,連空中的氣流都是滾燙的。李宸昊只覺自己是被烘乾了的朽木,風一吹就可能散落一地。
一點點伸手拿起水囊,將最後一點水一滴不剩地餵給木謠。再拿出匕首又刺了馬兒的一條動脈,把水囊放在下面希望能接一點兒馬血。
血流著流著就凝涸住了,好歹還是接了半囊的。他又撕下車廂的兜布,用兩根樹枝固定起來,做成了簡易可以遮擋太陽的布傘。
將木謠背在身後,再拿起布傘,他輕輕地笑了笑,乾涸發白的嘴唇裂得生疼。
謠兒,妳別怕,我一定帶妳離開這裡,回家去!他低聲緩緩地說道。邁起兩條軟如麺條一般的腿,一步一步地向西南方艱難地走著。
帶木謠回家的念頭強撐著他,不能倒下,絕不能倒下去!
也不知走了多久,太陽漸漸下山了,天也緩緩暗了下來。終於不再這麼熱了,可隨之而來的便是風一起,戈壁又迅速降下溫來。
一陣涼風刮來打在汗濕的脊背上,讓李宸昊打了一個冷顫。冷意越來越甚,沒了車廂的遮風保暖,今夜他和木謠又該如何度過呢?
好在不久後,他找到了一塊大的岩石,將木謠放在岩石後,把布傘蓋在她身上,再用馬血拌了些乾糧餵給她。
濃重的氣味卻讓木謠嘔了幾下,身子也跟著抖了抖。
李宸昊嚇壞了,立即丟下乾糧。他突然想起師父以前說過,他從小在滋補的藥罐裡泡澡,身體裡的血便有滋補之用。
想到這他沒有一點猶豫,霍地劃開自己的手指,血流了出來。他嗅了嗅,覺得比馬的血要好一些,沒那麼濃烈的腥鏽味,甚至還有點中藥的清香味兒。
伸手將手指餵進了木謠嘴裡。木謠微皺了皺眉,倒沒有太大的反抗。
李宸昊松了一口氣,待傷口的血凝固後,他又割另一根手指。一直就這樣割了十根,木謠的臉色漸漸好了一些,他才放下心來。
渾身猛然一松,提著的一口氣鬆懈下來,他頓時覺得頭暈眼花。
李宸昊疲累地晃了晃頭。
這麼幾天水米未盡,又失這麼多血如何會不眼花呢?
望著木謠安穩下來的神態,他展眉一笑,仰面靠在岩石上虛弱地閉上眼睛。
少頃,一陣風刮來,李宸昊冷得一激靈。他低咒了一聲,無奈地爬起來,拖著灌了鉛的腿,向一撮撮灌木叢走去。也幸虧他帶了火摺子,找了一些枯草將根部切掉,點燃枯草,等火大了些再投進灌木枝。
團團轉忙了半天,終於讓他弄出了一個小篝火。他再也沒力氣了,一下子癱在岩石上。風一刮來一身虛汗的他,只覺刺骨的冷。身子不由自主地靠向木謠,想吸取一點溫暖。可是轉念一想,自個一身虛汗再把她弄濕了,於是他立即彈回來,圈著腿抱緊自己縮成小小一團瑟瑟發抖。
就這樣凍了一夜,直到日頭漸漸升上來,酷熱又重新降回大地。他才猛然驚醒,頓覺自己頭疼欲裂,五臟不知是饑還是渴的,竟如烈火在燒一般,這種感覺就如同從地獄裡走過一遭。
這種折磨太痛苦了,若能選擇,他情願永遠不要醒過來。
抬起虛弱無力的眼皮,他望瞭望西南方向。已經走了三日了,為何還沒見到一個村鎮呢?
也許再走一天便能見到吧。
他不停地給自己打氣,倒不是為了自己,只因他無論如何也要把木謠帶出去的。如此心裡橫著一股氣兒,他咬牙緩緩挪向木謠。又用刀割了五根手指頭,餵給木謠。做完這些他竟覺得眼前一片灰白,再看不見任何東西。他慌了,不斷告訴自己,不能出事!不能出事!於是霍地咬開水囊,猛灌了幾口馬血。
咳咳咳……
強烈的腥臭味,再次引起他咳嗽。可是他這次卻不敢再吐了,猛然捂緊自己的嘴,強迫自己不要吐出來。
腹部翻江搗海,仿佛有一把刀在那裡絞割著,疼得他慘白著臉,五指緊緊摳著岩石,在那裡留下一道道血痕。
就這樣不知在煉獄熬了多久,那種翻滾想吐的感覺淡了一些子,他才敢粗喘著放下手。猝然的新鮮空氣炸滿胸腔,他才晃然驚覺他方才可能都快把自己給捂死了。
李宸昊慘然一笑,撐看兩條浮軟的腿,拉開布傘揹上木謠,繼續向西南走去。
快到了!快到了!
他一步一搖拖著兩條隨時會塌倒的腿,不停地反復地告訴自己。
太陽越升越高,天氣也越來越熱。
李宸昊的喉嚨乃至全身都在冒煙,他覺得自己乾熱得快蒸發了。眼前不再是一片灰白,而是天地都在虛晃。
啊……
突然他一隻腳踏空了,從一個小坡上滾了下來。
天旋地轉滾了幾圈,他全身都被摔散了架。
謠兒,謠兒!李宸昊虛弱地喚道,強撐著抬起頭,定睛一瞧木謠已被甩了老遠。
謠兒他啞叫一聲,顫抖的手一點點伸過去。強撐著胳膊試著爬去,眼前猛地一黑,人事不知地昏過去。
戈壁長空烈日高照,這一對有情人就這樣躺在那裡。李宸昊的手指與木謠之間不過幾步之遙,然這咫尺對他們來說便是天涯,或許永遠無法逾越。
風起了,黃沙飛揚,他們就這樣孤伶伶地躺著。枯黃的小草也為他們傷心,開始吟唱起悲傷的歌謠。
木謠只覺頭疼得厲害,仿佛被十匹馬車碾軋過。身子更是一會如墜冰窟,一會又如同被烈火燒烤一樣。
她的腦子卻出現了很多景像,有美謠的,有銀謠的,有北蒙皇帝和皇后的,更多的則是李宸昊。
她迷迷濛濛地在想是不是自己真要死了,否則如何會感覺到了離他這樣的近。
昊郎,昊郎!
是你嗎?
不,怎會是你!
你又怎麼會知道我身在北蒙。也許你以為我早死了,也許你早已與吳家大小姐結親。如此想著木謠只覺心痛如剜,頭也跟著更痛了。她不安地不斷扭動著,一個抽搐她突然彈開了眼睛。
腦中一片空白的她驚喘著,片刻後才迷迷濛濛地打量著眼前的一切。
這裡是哪裡?
屋子四周是胚黃色的土牆,格窗上貼著漢人才愛剪的窗花。
這根本不是獵場營地,這是哪兒?木謠混沌地想著。
一刹那,她被北蒙皇帝強暴,額頭撞上桌角的那幕浮上腦海。她一把掀開被下床,可頭隨之一頓痛,腳下一軟她跪倒炕邊。
姑娘,妳如何起來了?使不得,妳快躺下。持操著西北口音的漢話從身後響起。
木謠被那人重新扶上了炕。
但見是一個三十多歲的農家婦人,皮膚微黑身材魁梧,目光很是溫柔。
她幫木謠掖好被角道:老郎中可說了,姑娘撞了頭這一時半會的不能下炕。
這是哪兒?木謠吃力地問道。
這裡是劉家莊,前幾日我男人想抓幾條毒蛇回來,便往那草攤子上走。可巧碰上了你們倆,看你們昏在那兒,便把你們給揹了回來。婦人劈里啪啦地道。
倆?她和誰呢?是誰把她救出獵場的?
……木謠想再張嘴問問,奈何喉嚨乾得出奇,竟是說不出一個字來,頭也昏沉得很,她眼皮子一沉又昏睡了過去。
不知過了多久,迷迷糊糊地聽到有人在說話。
他爹,你說他們又不是咱村的人,是怎麼跑到草攤子上的?難道是從北蒙過來的?誰知道呢,不過怎麼講咱也不能見死不救。今年收成好,也不在乎這幾口糧食,待會我再去抓幾條蛇來,把他們的醫藥費給補上。
二人叨叨的聲音傳入木謠耳中,卻像是蒙了紗布一般越來越小,昏昏沉沉地她又人事不知了。
又過了三日,清晨打鳴的公雞嗷嗷嗷叫時。木謠才再次悠悠轉醒,這次她覺得身子好了一些,頭也不那麼疼了。
有了上次的教訓她不再貿然起身,只是躺在炕上思考著一些事。
| FindBook |
有 3 項符合
王的寵妃(下)的圖書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王的寵妃(下)
重整破碎山河再塑海晏河清是他必生的志願。
燈火闌珊下,只有那明媚的笑靨掬在他心頭的熱血裡……
家仇得報,國恨卻上升到了新的階段,北蒙入侵,身為定北侯世子責任重大,丁木謠兒女情長中選擇成全,卻不料一次又一次陷入了絕境中,貴人相扶,大難不死,用自己的真心和本事贏得了尊重和信服。生死面前,兩人緊拉對方的手,你生我生,你死我必不獨活……
外憂解決,內患開始,來自朝庭親人的背叛和傷害,又該怎樣一一化解?守得雲開,新皇上任,忠義親王世襲罔替,風光無倆,婚後生活那簡直是快活似神仙,感情如膠似漆,更勝神仙眷侶。
作者簡介:
木芷
喜歡看閒書,睡懶覺,日夜時常顛倒。不奢求字字珠璣,只希望用簡單深刻的文字描寫細膩的情感。滿紙荒唐也好,字字心酸也罷,只要言之有情就能讓妳感動。
知名作者,全新筆名,最新力作!
暢銷作品:王的寵妃
章節試閱
第一章 血義
越往西走日頭越烈,草地也越乾涸。原本李宸昊還能嚼嚼草根緩解一下饑渴,現在卻連枯草也找不到幾棵,就是偶爾找到了也沒有一點水份。
吃地更是寥寥無幾,李宸昊每日裡只能以強忍著饑餓感,實在忍不了了才去咬一小口乾糧。
省下的乾糧他用水泡軟了泡稀了餵給木謠,好在乾糧還夠她吃個十餘天的。可水囊裡的水也越來越少了,最多只夠喝一天的了。
咻……馬兒發出最後一聲悲鳴,倒在了地上,馬車也跟著晃了幾晃。
李宸昊一個飛身閃下去,用肩膀扛住車轅穩住了馬車。
抽了幾鞭子後,馬兒只是抽搐了幾下就一動不動了。如此也...
越往西走日頭越烈,草地也越乾涸。原本李宸昊還能嚼嚼草根緩解一下饑渴,現在卻連枯草也找不到幾棵,就是偶爾找到了也沒有一點水份。
吃地更是寥寥無幾,李宸昊每日裡只能以強忍著饑餓感,實在忍不了了才去咬一小口乾糧。
省下的乾糧他用水泡軟了泡稀了餵給木謠,好在乾糧還夠她吃個十餘天的。可水囊裡的水也越來越少了,最多只夠喝一天的了。
咻……馬兒發出最後一聲悲鳴,倒在了地上,馬車也跟著晃了幾晃。
李宸昊一個飛身閃下去,用肩膀扛住車轅穩住了馬車。
抽了幾鞭子後,馬兒只是抽搐了幾下就一動不動了。如此也...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