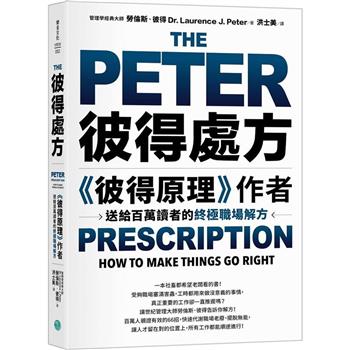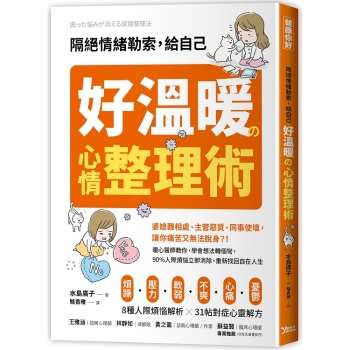第一章 初見
大周永昌二十六年,青州沈府。
十五歲的沈嫣被奶娘護在懷中,絕美的小臉被遮得嚴嚴實實,生怕教她見著任何可怕的畫面。
然而,這不是噩夢。就算她不去看,危機也依然步步緊逼。
原本一個好端端的中秋團圓夜,卻讓幾個不請自來的錦衣衛給攪成了人間煉獄。
這些人一來就是抄家,將沈府上下三十幾人全都趕到這崇光堂中,稍有反抗的就一刀了結性命。
而她的父親,青州知州沈天元,脖子上架著一把明晃晃的繡春刀,被迫跪在主座之人的腳邊。
上座的是錦衣衛北鎮撫司百戶統領。他們以沈府人性命相挾,迫她父親交出錦衣衛指揮使十二年前遺落的腰牌。
猩紅的紅氈地毯上橫七豎八地倒著幾具屍體,俱是沈府的家丁。
她不懂為何一面遺落多年的腰牌竟會與父親扯上關係,更為何還要搭上這樣多無辜的性命。
一聲淒叫傳來,錦衣衛又提起了一個女孩,一柄明晃晃的繡春刀不由分說紮進了心口。
沈嫣一抬頭,滾熱的血水濺了過來,她閃避不及,忍不住尖叫起來。
她只叫了一聲,那為首的百戶提刀逼近,將她從奶娘手中拖出,卻在見著她那張粉雕玉琢的小臉時,亮了眼也停了手,當即笑道:這樣的天姿國色,若是送到教坊司去,可不知要惹得多少王孫權貴爭搶破頭!
奶娘要衝上來拉她,卻被人一腳狠踹飛了出去,當場氣絕。
畜生!你們這群畜生!
沈天元憤而暴起,不顧身上架的刀刃,就要衝上前與那些人拼命。
男人的糙手與氣息令人作嘔,沈嫣死命閃躲尖叫,卻無處可躲,絕望之際只聽見那惡徒在逼問父親:再問一次,腰牌在哪裡!
連問無果,那人眉頭一挑,手下立馬會意,刀光閃冽,隨手在跪地的沈家人裡抓出了一個少年。
沈嫣失聲叫道:三弟!
一個美豔婦人沖出人堆,這是馮姨娘,三弟的生母。
妾身知道官爺要的東西!求求官爺饒了我兒一命!
沈天元怒目圓睜,暴喝阻止,卻被人踢翻在地,吐了一大口血。
老爺書房的架子後有個暗格……馮姨娘不過一個滿心護犢的短淺婦人,將自己所知的信口胡謅一通,只望能讓這些錦衣衛滿意以換她母子平安。
這時兩名錦衣衛從書房捧出了一個青銅匣子。裡面果真放著一塊銀質方牌,其上刻著:錦衣衛北鎮撫使羅良。
沈嫣回頭去看一動不動的奶娘,痛哭流涕,胸口劇烈地起伏,氣息急促得不能自已。本該人月兩團圓的中秋夜,在這樣肝腸寸斷的哭聲下顯得無比淒涼。
縱使這樣,那些殺人兇手卻還不滿足。
那百戶又提起另一樁公案:當年太傅府大火,不但燒死了廢太子,也燒掉了老太傅府上一百三十三口人命,聖上命錦衣衛徹查此事,可本官翻了宗卷,卻發現在那些焦屍裡,並沒有老太傅三歲大的小孫女。聽聞那一年沈大人恰好也在福建,您可知這太傅府的小千金去向何方?
沈天元面如死灰,喃喃地道:事到如今,又何必明知故問?人是錦衣衛殺的,火也是錦衣衛放的。這羅良當年遺落在太傅府的腰牌就是最好的罪證!你們要不是做賊心虛,今日又怎會來趕盡殺絕!
那百戶轉身扼住了沈嫣的脖頸,提到跟前:小美人兒,今年十五了吧?
沈嫣生得貌美,十二歲時已名動青州,就連定國公世子都曾差人送來過問名帖。現下落在這糙漢手中,無異於羊入虎口,眼看衣襟就要被人撕開。
沈嫣喘得撕心裂肺,卻不知從哪裡生出的力氣,忽而猛地抽出這百戶腰間綁著的繡春刀狠狠刺了下去。可她終究是個弱女子,手中的刀還沒挨上那人的皮肉,就被反手摔了出去。那白如月光的刀刃,不偏不倚地沒入了她那細細的脖子,血湧如柱,穿喉見骨的猙獰血口讓這些殺人不眨眼的狂徒都望而卻步。
她一步一步地爬回奶娘懷中,在地上拖出一道長長的猩紅血跡,耳邊爆起了父親的怒吼,長姐的痛哭,還有那些惡魔毫無人性的談笑風生。
嘖嘖,這麼標緻的小妞就這麼死了真是浪費。
死就死了,東西已拿到手,這些人一個不留。
那太傅遺孤還找不找了?
上面交待要斬草除根。這裡有三個丫頭,看著年歲都像,既然死了兩個,剩下的這個也一併除了。
一場殺戮無可避免,父親死了,長姐死了,就連賣主求生的馮姨娘也抱著兒子喪生刀下。
不到一盞茶的工夫,三十餘條鮮活的性命,消亡殆盡!
最後,這些錦衣衛還不忘故技重施,離去時丟下一把火,企圖將一切的罪證都化作飛灰。
濃煙滾滾,沈嫣的身子越來越涼,模糊的視線裡,忽然躥進了一條頎長的影子。
那影子越來越近,依稀看得出這是一個男子,腰間也別著一把兵刃,低著頭在遍地的橫屍中搜尋著,直至在她表妹跟前停住,表妹似乎還一息尚存,那男子還俯身問了些話。
然而沈嫣此刻已經神志模糊,根本聽不清他們在說什麼,可那男子突然站了起來,朝她走來。
周身火光耀目,烈焰烹熬,卻有滾滾的寒潮隨著那人行進的步子朝她湧了過來,似乎都能將她身上的血跡都瞬間凝凍。
這是相當冷的一個人。
男子走近,蹲下,淡淡的目色覆在她的臉上。
這是妳的?連問出的話,都蒙著一層寒霜。
一串玲瓏精緻的金鈴手釧在男子的指縫間漏下,隨著紅絲線的擺蕩,叮叮噹噹地在爆裂不斷的火場裡,彷若山間清泉,分外動聽。
沈嫣睜大了眼,渾濁的視野逐漸清晰,映現出男子清冷得不見一絲人氣的面孔,還有他身上玄色公服上繡得栩栩如生的四爪飛魚紋。
飛魚服,繡春刀。
這個男子竟也是錦衣衛,害死沈府一門的殺人兇手!
身體中殘存的一點血氣翻湧,她倏地握緊了右手中的斷刃。想要將利刃插進這個錦衣衛的心口,就像那些壞蛋的刀尖捅進她家人的心口一樣!
無論能不能傷得了他的性命,她也要用他的血來祭奠沈家這些慘死的亡魂。
然而,她的生命,早就沒了多餘的力氣。
叮的一聲,顫顫巍巍的小手,最終還是握不住那斷刃,落在血紅濕亮的青磚地上。再多的忿恨與不甘,也隨著這隻小手的隕落,淹沒在深夜的寒潮裡。
她躺在那兒,已然沒了心跳。雪頸上大開的血洞,像乾涸的泉眼,流盡了身體裡的最後一滴血。一雙純淨而美麗的眼睛,就這麼空空洞的睜著,將這一世最後的一道眸光,不偏不倚地落在男子清冷如水的俊顏上。
他眉間微動,擰出些許失望,到底還是來遲了一步。沉默了半晌,方抬手掩去了那雙至死都不肯闔上的眸子。
這金鈴,是妳的吧?
※※※
水靈靈的眸子倏地睜開,眸中映出了軟紗帳質地輕柔細膩,正是少女都喜愛的嬌俏桃粉。
絕美的面龐上滿是淚水,連腦後的枕巾都是一片濕涼。
沈嫣緩緩地坐起,轉眸四顧,神情有些凝滯,眼中也漸漸地浮現驚疑。
她很確定自己是死了,咽喉被割開的劇痛也足以令她幾世難忘,然而當一雙纖手顫顫地撫上頸間,指下觸及的肌膚光潔柔膩,嬌嫩無比,還散發著淡淡的香氣,顯然是沐浴後又抹過了玫瑰香脂。
帳子被人掀開,一個有些發福的婦人探進身來,見著她滿面的淚痕,頓時心疼不已。乖命兒,好好地怎麼哭了?
聽到這再熟悉不過的聲音,沈嫣一下紅了眼眶,鼻端一熱,淚珠兒吧嗒吧嗒地掉了下來。
奶娘!她哇地一聲撲進了婦人的懷中。
這婦人是她的奶娘劉嬤嬤,昨夜為了她不受欺侮而被人活活踢死。
劉嬤嬤抱著比自己親生的娃還要親的小姐,已有了些皺紋的臉上盡顯慈愛:不怕不怕,奶娘在這,阿命兒不怕,當心哭得厲害又鬧毛病了。
沈嫣有哮症,這是從娘胎裡帶出的毛病,發作起來雖不致命卻是十分難受。長大成人後,許是家中照顧得好,倒是有兩年不見發作。然縱使這般,劉嬤嬤也是格外小心精細,生怕有個閃失。
聽了這話,她又想起昨夜裡奶娘的死,哭得更厲害了。
奶娘!我好怕沒追上妳們我就成了孤魂野鬼!
等咱們到了奈何橋,可不要喝那孟婆茶,一定要先去閻君那告上一狀,絕不能讓那些惡人逍遙法外!
沈嫣閉著眼睛,語無倫次,大聲地哭著,喊著,盡情宣洩著心底的委屈和恐懼。
大吉大利!劉嬤嬤聽出了點意思,變了臉色,慌忙打斷她的哭喊道:大過年的,姑娘說什麼傻話!
沈嫣愣住了:過年?
見她不哭了,劉嬤嬤掏出帕子為她擦了淚痕,又拿了外裳來給她穿上:可不是要過年了,今兒是除夕夜,也只有您這做姑娘才能有清閒睡午覺。我老太婆可是忙了一整圈,這才得空來看看您起了沒。年夜飯開得早,馮姨娘都打發人來催了兩回了,姑娘還是快些起來收拾一下,免得去晚了讓人落了話頭。
沈嫣越聽越糊塗。
奶娘,您說什麼呢,咱們不是都死了嗎?難道地府裡也過年嗎?
| FindBook |
有 2 項符合
錦衣還朝(1)的圖書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錦衣還朝(1)
除了這個叫洛天佑的錦衣衛,重生指南完全不起作用。
哪想人家搖身一變,成了強勢回歸的東宮太子。
愛妃,這樣可還順眼?
中秋團圓節,青州沈府因一塊神秘腰牌遭錦衣衛滅門。
傾城絕色的沈二姑娘一朝夢醒回到半年前的除夕夜,重活一世的她只求家人能擺脫中秋厄運。她洞悉天機,事事搶先,讓一切都朝著預期的方向行進。
一串自小佩戴的金鈴,讓她與錦衣衛洛天祐不打不相識,起初她還忌憚他那嚇人的身份,一再抗拒他的靠近,可洛天祐這座冰山卻不上道,非但不請自來,更動不動一言不合扛人就走。
情敵相見,哪怕對方是高高在上的世子爺,他也分毫不讓……
作者簡介:
傾吾三下
網絡寫手,紅薯中文網簽約作者,文筆優美,筆觸細膩,小說故事娓娓道來,邏輯嚴謹,情節環環相扣,跌拓起伏,深受讀者喜愛。
我會一直安靜的寫,惟願我在,你們也在,我們一起分享來自另一個虛幻世界裡的歡笑和淚水。
★ 暢銷作品:錦衣還朝
章節試閱
第一章 初見
大周永昌二十六年,青州沈府。
十五歲的沈嫣被奶娘護在懷中,絕美的小臉被遮得嚴嚴實實,生怕教她見著任何可怕的畫面。
然而,這不是噩夢。就算她不去看,危機也依然步步緊逼。
原本一個好端端的中秋團圓夜,卻讓幾個不請自來的錦衣衛給攪成了人間煉獄。
這些人一來就是抄家,將沈府上下三十幾人全都趕到這崇光堂中,稍有反抗的就一刀了結性命。
而她的父親,青州知州沈天元,脖子上架著一把明晃晃的繡春刀,被迫跪在主座之人的腳邊。
上座的是錦衣衛北鎮撫司百戶統領。他們以沈府人性命相挾,迫她父親交出錦衣衛指揮...
大周永昌二十六年,青州沈府。
十五歲的沈嫣被奶娘護在懷中,絕美的小臉被遮得嚴嚴實實,生怕教她見著任何可怕的畫面。
然而,這不是噩夢。就算她不去看,危機也依然步步緊逼。
原本一個好端端的中秋團圓夜,卻讓幾個不請自來的錦衣衛給攪成了人間煉獄。
這些人一來就是抄家,將沈府上下三十幾人全都趕到這崇光堂中,稍有反抗的就一刀了結性命。
而她的父親,青州知州沈天元,脖子上架著一把明晃晃的繡春刀,被迫跪在主座之人的腳邊。
上座的是錦衣衛北鎮撫司百戶統領。他們以沈府人性命相挾,迫她父親交出錦衣衛指揮...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