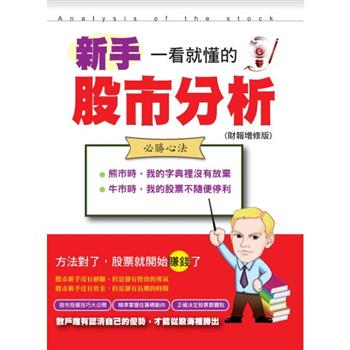第一章 重回鐘府
春末夏初,下了幾陣雨後天兒終於回了晴,豔陽高照,讓人覺著熱了起來。街上行人減了襖子,穿得薄透圖涼爽,只在路過樹蔭遮下的灰瓦宅子時覺到一股涼意,聞著裡面透出來的淡淡藥味,忍不住的加快了步子走開。襯著外面一路而來的寥落庭院,這往日車水馬龍衣香鬢影的鐘府更加顯得冷清,一股難以言喻的寂寥輕輕滲入肌骨。正茗居鐘鴻飛的住所,還未靠近一股濃濃的藥味就撲面而來,門窗捂得緊緊的,一個神情懶散的媳婦子守在門口不住的打哈欠,見有人過來,忙板正了身子,沖著行禮。
“四太太您……您今兒怎麼過來了?”阮娘有些緊張的回望了裡面一眼,提了嗓音磕絆絆說道。
被喚做四太太的女子披一件湖水藍薄綾紗襖子,旭日初春頗是清麗嫵媚,身後跟著一端著個雕繪著荷葉蓮藕紅漆盤兒的丫鬟。海氏站定在門口往關著的房裡面望了一眼:“怎麼,我這做夫人的探望老爺還要妳一個婆子同意不成,還不讓開。”
“這……”阮娘念著方才進去之人的交代,杵著身子進退不得,正不知如何是好就聽著身後的門吱呀一聲的開了,暗地裡松了一口氣,退在了一邊。趁著沒人發覺的空檔,又別了海氏身後跟著的丫鬟一眼,這嘴碎的,老爺醒來的消息這麼快就傳給了最能折騰事兒的四太太,二人對上,免不了一陣吵鬧的,到時又把老爺給吵暈過去。
“喲,我還以為裡面的是大夫,原來是姐姐您吶。老爺醒了這麼大的事兒都傳的不及時,姐姐得治治手下人,不知道的還以為咱們之間有隔閡,妳想一個人專美於前呢。”海氏笑得明媚,卻也壓不住話語中的刻薄勁。
“妹妹誤會了,老爺剛剛醒來,我正打算著人去通知妳們,老爺又昏了過去,這不正準備出來找大夫瞧瞧看。”許氏也同樣笑著,眼底盡是冷意。
海氏聞言一頓,巴巴的望了一眼房門,生了退意,嘴上卻是不饒道:“怎麼這般巧的,我要見就昏過去,總不會是老爺還是姐姐不待見,不想我見吧。”
許氏心裡冷笑,分明是她自己怕老爺的病症有染,不願踏足,這會兒一聽醒了倒是想來表現,哪有這麼好的事兒。面上卻是不顯,一派和善:“妹妹說哪兒去了,老爺就在裡面,妹妹要看隨時進去看,陪在跟前,保證老爺一睜眼就能見著妳,念著妹妹的好。”
海氏一噎,她自然不會進去陪著,上個大夫怎麼死的她可親眼見了,滿身發瘡得極為可怖。那人之前一直在屋子裡為老爺診治,定是因此受了染,打那以後她只進過老爺房裡兩回,回去都用艾葉煮水好好洗了才安心。不過許氏就不同了,每回老爺醒轉她都在,也不見任何措施,還真為了老爺肯捨身?海氏抽了抽嘴角,看向許氏的眼神也有了一絲不同,訕訕地道:“我又不是大夫幫不了什麼忙的,姐姐還是快些請大夫過來瞧,免得延誤了時機。”隨即話一轉的,帶著幾分懊惱道:“這月總共醒了兩回,兩回都只見了姐姐,我怎麼就趕不上呢!”
說者無心,聽者有意。許氏嘴角笑意一僵,神色透出一絲不自然,只是轉身帶著丫鬟離開的海氏沒來得及發現。房門前,許氏佇立著目送海氏主僕走遠,回頭掃向了阮娘,涼聲吩咐道:“妳且在這兒守著,除了丁大夫誰也不許進,省得感染了病症,害了一家子。”
“是。”阮娘緊張著應下,下意識的往邊上又挪了挪,也是生怕被感染。這一幕落在許氏眼裡,勾了勾嘴角,拂袖離去。
被捂得嚴實房子裡,紫檀雕繪草鳥蟲花樣的床鋪裡躺著一名消瘦面苦的男子。這會兒眼睜得大大的,手費力地往前伸著,張著口卻發不出半點聲兒來,半晌之後,才頹然放了力道,癱在床上流下兩行濁淚。
海氏回了玉瓊苑,急忙洗了個澡換身衣裳,也不知是不是心理作用,鼻端總能嗅到一縷若有似無的藥味,正晦氣著忽而想到隔壁苑兒裡的人,正要出門尋過去,就聽著翠屏說有客人上門。待見著來人,海氏是真真的喜著了,她是最後一個入門的小妾,原是京城紅樓的歌妓,知府在四喜樓做壽,因著鐘鴻飛極會來事兒,就把她當作回禮送了,從良之後就徹底與京城那頭斷了。再見到昔日一同患難的好姐妹,禁不住紅了眼眶,抱在了一塊兒。女子生的一張芙蓉瓜子臉,身著一件玫瑰紫的遍地纏枝芙蓉花的錦緞褙子,斜墮馬髻上插著一支金托底紅包是牡丹花樣的珠釵,一副嬌俏可親的模樣。
“秦桑,我們有個五六年沒見著了罷,可還好?”海氏打量著她,視線落在了她挽起的髮髻上,已是出嫁的婦人,不由好奇道:“桑桑當年放話可是與綠綺廝守餘生,哪家的公子這麼有本事讓妳食了言?”
秦桑聽著她打趣的話兒,不好意思的嗔了她一眼,笑容裡染上幾分甜蜜:“磨不過只好依了,就在幾月前,這不跟著來了宛城,想著妳在這兒來瞧一瞧。妳呢,那位鐘老爺待妳可好?”
提到這,海氏的眸子黯了黯,因著沒人訴說憋了一肚子的話一股腦兒的都倒了出來。鐘鴻飛病倒後許氏霸權,各院裡都苛刻不少,又因著出身的緣故,交際應酬沒她什麼事的,比在紅樓裡還沒了自由。兩人拉家常,大多是海氏在說,秦桑聽著,不時搭上幾句,讓她一吐為快了先。
秦桑拿了茶壺給兩個潤瓷浮紋茶碗裡都添上了水,細心的蓋上茶碗蓋,歎了口氣道:“照妳這活潑性子在這府裡確實悶著。”話一頓的,轉而揚起一絲笑意道:“相公要在此地久留,我閑著就來找妳,陪妳解悶兒。”
海氏聞言掃了方才的愁緒,也是頗為高興,余光瞥見秦桑穿戴不菲,心生羡慕,多問了幾句才知她嫁的是京城白家三少。公公是當今的戶部尚書,膝下三子,各有所成,大少和二少徵兵沙場,威名遠播,白家三少生得風流倜儻,一手金算盤打得倍兒溜,是做生意的好手。說起來白三少還是鐘鴻飛的小舅子,鐘甯生母的胞弟。難怪……海氏垂眸,心底生出了幾絲妒意,待她問及時也就有了保留,將鐘府的情況輕描淡寫而過,心下也是有些不解。白家小姐與鐘老爺的事她有所聽聞,白家因此惱上鐘家,多年不曾有生意往來,這會兒怎麼……
秦桑見她一問三不知的,也就放棄了,見時候不早,同她辭別,約了改日一道喝茶。待秦桑離開後,海氏總覺得有哪兒不對勁,自己又想不明白,往回走著臨到自家院子拐了彎的去了褚玉閣。院子裡種著兩棵極高大的梔子花樹,此時正是開花的好時節,葉瓣翠綠,花形潤白,隨著微風將陣陣清香柔柔相送,很是好聞。海氏帶著丫鬟進了褚玉閣,在用飯的廳裡找到了夏氏。圓圓的紅木八角雕牡丹浮紋大桌上擺放著好些吃食,一籠熱氣騰騰的小籠包,周邊團團擺著紅豆米麵發糕,鵝脂酥炸豆沙麻團,四色蔥香畫卷,還有棗泥山藥糕,甜鹹兩色粥點,金米南瓜粥和香菇雞粥占了一角,放在夏氏面前,還未開動。
海氏掃了一眼,蹙了眉頭:“怎麼每回見姐姐都吃這些,不多吃點好的,身子怎麼好得起來。”
夏氏生得柔弱,有著江南女子特有的婉約,說話聲兒也是柔柔的,叫人添了碗筷,招呼她一塊兒坐下用點。海氏在她面前也有些斂了性子,總覺得自個兒說話一大聲了就能把對面之人驚著,因著心裡面存著疑惑,先行問了出口。白家、許氏、鐘府三者之間的關係,晚來的海氏或許不太清楚,同一圈子裡嫡小姐出身的夏氏可是清楚得很,只是那時不曾想到這當笑話聽的事兒,過了還不到一年就家道中落,自己也進了這座宅子……
夏氏聽完海氏所說,就大約明瞭了,當初白家因鐘鴻飛在白氏難產去了之後連納兩名妾室惱上,許氏與白氏情同姐妹,又因著嗷嗷待哺的鐘甯白家忍了,而她……白家只覺先前受了鐘鴻飛矇騙,斷了往來。如今白家三奶奶說的生意,定是白氏的閨中之友許氏在穿針引線,因著鐘鴻飛病入膏肓緩和了兩家關係,只是……依著許氏心性,真是找個靠山如此簡單?
夏氏捧著南瓜粥,小口吃著,正暗自思量著,就聽著海氏一臉興致道:“要真是個生錢的,我倒想投進去些,鐘芙母女把著鐘家裡外的,都沒什麼閒錢置買東西的。”
“妹妹若是信得過我,這生意千萬別摻和進去。”夏氏放下白瓷碗,慢條斯理的拿帕子摁了摁嘴角:“如今她二人掌權,是沒咱們什麼事兒,還能有一席之地,是看在老爺的面兒上。要是老爺一走,鐘府成了許府,妳說還有沒有我們的容身之所。”
海氏心裡一咯蹬,叫她的話給驚著了,咬著唇,半晌不知所措道:“我去瞧過老爺,說是又惡化了,這離去不去的,我看著也沒差多少了,咱們可怎麼辦?”
夏氏抿了口茶水,亦是歎了口氣:“當初鐘甯在時,好歹有個牽制,不至於翻了天去,如今真是要變了天了,妳我膝下又沒孩子,如何去爭。”
“孩子……”說到這個,海氏心裡更惡,她進府裡好幾年一直無所出,起先還懷疑是自己身子緣故,後來叫外面的大夫看了才知道是一直服用了藥物,絕了子孫緣,能做出這等事的除了許氏不作第二人想。這會兒提起被戳了痛處,想著想著忽然想起一人來,陡然興奮道:“姐姐,有孩子的。”
“嗯?”
“那個……那個叫綠枝的,當初在姐姐妳身邊當差,勾引老爺,那時候診出來肚子裡已經有了老爺的種,讓許氏瞞下給趕出了府。後來老爺知道不是還罰了許氏那賤人,是不是有這事?”海氏入門雖晚,可最喜歡聽宅子裡的辛秘事兒,陳年舊事也不放過。夏氏摩挲著茶杯的邊緣,鳳眸閃過絲幽深的光後,略作沉吟道:“是有這事,可老爺派人去找的時候,綠枝早就沒了蹤影,是死是活還不清楚呢!這會兒提起妳想作何打算?”
| FindBook |
有 3 項符合
王府小廚娘(下)的圖書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王府小廚娘(下)
重活一世,鐘寧立誓重振祖蒙、把前世的債千百倍討回來!
懷揣食譜,發家致富奔小康,虐渣賤,奪家業!
大張旗鼓,重回鐘府,平靜表像下,暗濤洶湧。
府中之人各懷心思,互相牽制,鐘父同宗兄弟以管家身份打理事務,照顧頗多。
繼母步步緊逼,屢下黑手逼她離開,鐘寧步步為營,鬥智鬥勇,引導二人一步一步走向為她們設定好的結局。
只是每次夜裏見到小王爺的俊美身影,鐘寧總覺得自己走錯房,可這明明是她的閨房,這人也太熟門熟路了吧……
作者簡介:
粟米殼
晉江文學城簽約作者,唯美食與旅行不可辜負,熱衷於將故事變成文字記錄。
★暢銷作品:王府小廚娘
TOP
章節試閱
第一章 重回鐘府
春末夏初,下了幾陣雨後天兒終於回了晴,豔陽高照,讓人覺著熱了起來。街上行人減了襖子,穿得薄透圖涼爽,只在路過樹蔭遮下的灰瓦宅子時覺到一股涼意,聞著裡面透出來的淡淡藥味,忍不住的加快了步子走開。襯著外面一路而來的寥落庭院,這往日車水馬龍衣香鬢影的鐘府更加顯得冷清,一股難以言喻的寂寥輕輕滲入肌骨。正茗居鐘鴻飛的住所,還未靠近一股濃濃的藥味就撲面而來,門窗捂得緊緊的,一個神情懶散的媳婦子守在門口不住的打哈欠,見有人過來,忙板正了身子,沖著行禮。
“四太太您……您今兒怎麼過來了?”阮娘...
春末夏初,下了幾陣雨後天兒終於回了晴,豔陽高照,讓人覺著熱了起來。街上行人減了襖子,穿得薄透圖涼爽,只在路過樹蔭遮下的灰瓦宅子時覺到一股涼意,聞著裡面透出來的淡淡藥味,忍不住的加快了步子走開。襯著外面一路而來的寥落庭院,這往日車水馬龍衣香鬢影的鐘府更加顯得冷清,一股難以言喻的寂寥輕輕滲入肌骨。正茗居鐘鴻飛的住所,還未靠近一股濃濃的藥味就撲面而來,門窗捂得緊緊的,一個神情懶散的媳婦子守在門口不住的打哈欠,見有人過來,忙板正了身子,沖著行禮。
“四太太您……您今兒怎麼過來了?”阮娘...
»看全部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粟米殼 繪者: 絕色插畫
- 出版社: 錦聿豐文化 出版日期:2016-01-27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320頁 開數:21x14.8 cm
- 類別: 中文書> 漫畫/輕小說> 羅曼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