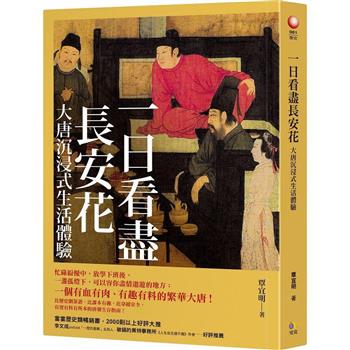遭雙方算計,她被一劍釘在牆上,身死名裂。
攜怨重生,再次踏上前世之路。
這一回,有恩報恩,有怨報怨。
攜怨重生,再次踏上前世之路。
這一回,有恩報恩,有怨報怨。
渣爹叫她嫁給皇親國戚,哪怕是跪著嫁進去,也要給家族掙得榮耀。
繼母假惺惺地說,絮兒什麼都能做好的。
繼妹居高臨下地說,你就是給我擋災的一條狗。
曾經,她滿足了他們。她把世上最最難搞的男人,冷酷無情的魏王殿下搞到了手。
成為魏王妃後,她致力於給家族帶來榮耀與權勢。
然而最後得到的,卻是渣爹與繼母聯手,讒言蠱惑了魏王,將她一劍穿胸,釘死在牆上。
上天垂憐,給她重生的機會。這一次,她要攪得天翻地覆,雞犬不寧。
一次轉機,她得貴人相助,救得母親性命,填平心中最大的遺憾。
將母親藏好,她毅然決然踏上復仇之路。
收服心腹丫鬟,結識仗義閨蜜,挑撥渣爹和繼母,教訓跋扈繼妹,將心懷叵測的魑魅魍魎打得無所遁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