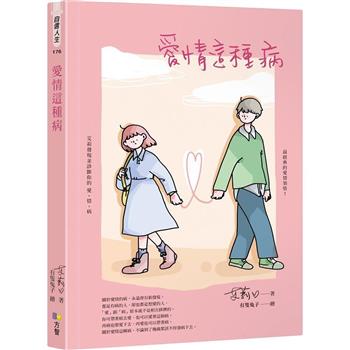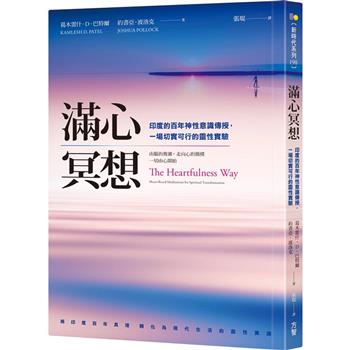現代的小白領一朝穿越竟然成了一清二白的小丫頭,家徒四壁不說還險些餓死,
不過陶陶不氣餒,咱有頭腦有本事,銀子沒了咱自己賺,
有美男王爺助力,能力夫子加持,咱賣陶器,倒洋貨,
南來北往商路變通途,終成就了一代財神小王妃……
不過陶陶不氣餒,咱有頭腦有本事,銀子沒了咱自己賺,
有美男王爺助力,能力夫子加持,咱賣陶器,倒洋貨,
南來北往商路變通途,終成就了一代財神小王妃……
什麼,穿越了?陶陶睜眼看了看四周,這還真是家徒四壁,窮掉底兒了!
她不要這麼倒楣啦,別人穿越不都是美男成群,帥哥成堆的嗎?
怎麼到了自己這兒連個美男的渣渣兒都沒瞧見,這也太倒楣了。
她不穿越了,她要回去!
咦,還真有個美男,什麼還是王爺!
雖說這美男看著自己的目光很是嫌棄,但不管啦,既然有美男王爺,老娘在這兒落戶安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