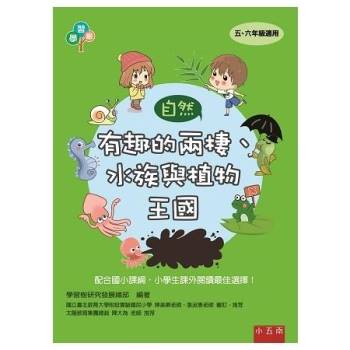第一章 海狸先生◎VS◎阿童木小姐
1
今天考兩門,上午毛概,下午法律。
我先前辛辛苦苦地將複習資料上的題目全部請教好答案,謄了一遍,又拿去縮印,回來用剪刀剪成豆腐乾模樣,再送去印。來來去去,活活折騰了一天,比那些臨時抱佛腳而半夜背書的人還用功。
發考卷的時候看到那些試題,我驟然有點喜極而泣了。功夫不負有心人啊,居然在昨天抄答案的時候,將那些知識點記了個大概。
本人心情頓時大好,剛想將紙條收好卻感到一個帶著諂媚的炙熱眼神落到自己身上。
「薛桐,借我用用吧。」坐在我旁邊,中間隔了條走道的鍾強討好地說,「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呢。」
我看了看他,再看了看手裡的東西,用力咬牙遞給他:「記得還我。」
開考二十分鐘以後,監考員羅老師拿起一張空白的毛概試卷開始沉思,沉思之後目光縹緲起來,很明顯羅老師開始神游了。於是考場進入了一個黃金作弊時段,同學們的膽子漸漸發酵,各顯神通。
我後面的白霖今天一早就來教室用鉛筆將答案抄在桌子上,現下正在埋頭奮筆疾書。
而鍾強則看了看講臺上的羅老師,再從口袋摸啊摸的,口袋裡簌簌地響了半天,終於摸出那兩張救命的小紙條。
我不再看他那個笨模樣,嘴裡含著筆,兩條眉毛皺一起,開始嚴肅地思考毛主席思想的精髓所在。
過了一會兒,我聽到鍾強在咳嗽,而且咳個不停,一抬臉我便看見他朝我猛地使了眼色。我隨著他的視線低頭看去──那張借他救命的紙條居然被風吹到了我這邊的桌子腳下,赫然躺在寬敞的走廊上。
一張紙上密密麻麻地印著比螞蟻還小的字,為了方便,我在上面印了今天兩門學科的答案,正面毛概、背面法律,大概有二分之一張光碟那麼大。
如今,我瞧了瞧那紙,有些心疼。我抬頭剜了鍾強一眼,這人抄個答案都不會,還能弄到掉地上。
我生氣地彎腰去撈,撈了一下沒撈著,第二次加大弧度再去撿的時候,一隻腳踩在了上面。
我疼惜地扯住紙條的一角,壓低嗓門小聲地說:「同學,你踩著我的東西了。」這人真不識趣,交卷就去交卷,要走就快走,差點壞了我的好事。
可是,那隻腳一直沒挪開。
我又說:「同學。」說完,我本想仰頭瞪瞪對方,無奈角度太大,脖子只夠抬到一半,看到膝蓋上方便無法再向上。
要不是講臺上還坐著個老師,換在平時,我不保證不啃他一口。
旁邊的鍾強又咳了咳,再咳了咳。
「喂。」我急了。
這人不能因為腿長,就這麼踩著我的東西不放吧?
白霖也跟著咳起來。
這下我納悶了,學校沒暴發流感啊,怎麼這一個兩個的都一起患上咳嗽了,存心讓我被那羅老頭發現嗎?
就在此刻,對方終於抬了腳,我這才將東西抽出來,正要長長舒口氣,卻不想那雙腿的主人竟然彎腰蹲下來。
隨即,一張年輕男人的臉緩緩落入我的視線。
我看著那副突然在眼前放大的五官,腦子還沒轉過彎來。
男人粲然一笑,指著我手裡的東西,親切地問:「同學,妳手裡拿的什麼呢?」
話音剛落,他胸前掛著的工作證也一搖一擺地垂下來,上面赫然印著三個頓時讓我形神俱滅的粗體字──「巡考員」。
鍾強一見這苗頭,迅速地起身交卷,然後飛快地從考場裡消失了。
我看了看他,又看了看鍾強消失的背影,再看了看手裡捏得緊緊的東西,嘴巴張了張卻是徒勞,活活被對方逮了個現行,百口莫辯。
我先是驚慌,然後羞愧,接著開始直視蒼涼的人生,最後居然變成一副大義凜然、捨生取義的樣子。
本來東西掉地上,周圍人都不承認就得了,只能草草了事。但是他不早不晚偏偏選了個人贓俱獲的最佳時機來抓我,我可真比那竇娥還冤啊!
「還不服氣?」辦公室裡,巡考員老師笑盈盈地問。
「有點。」我冷嗤。
「這東西不是妳的?」
「……是。」我寫的,我印的,我剪的。
「不是妳帶進考場的?」
「……是。」
「那妳就不要告訴我,妳本來想作弊,但是在考前卻突然良心發現決定改過自新,然後好心地借給了同學,結果這位同學不小心將東西掉在妳的腳下,這個時候我來了……」男人揚了揚眉梢,「同學啊,很多年前這臺詞在我們學校就已經不流行了。」
我的臉從紫紅變成了青黑,這人一口氣把我能說的想說的都說了。
我深吸了口氣,世界上怎麼有這種老師?
待我看到對方還擺著一副悠閒自得、得意揚揚的模樣,更加怒火中燒,有種馬上撲上去掐死他的衝動。
臨走的時候,我惡狠狠地回頭,視死如歸:「老師!」
「嗯嗯,還有話說?」
「麻煩你把我的東西還給我。」
「幹嗎?」男人漫不經心地問。
「我下午考法律基礎還要用。」我答。
我聽見門口吧嗒一聲,大概是守在走廊上的白霖跌了一跤。
沒想到男人一點也沒生氣,反倒微微一笑,用下巴示意了一下桌子上的罪證說:「拿去吧。不過,這位同學,妳下午如果要作弊得挑個好點的手段,夾帶紙條屬於最笨的一種。」
我跟白霖啞口無言。
過了一天又一天,直到所有的科目都考完,我還是沒有被輔導員召見,也未曾收到系裡任何處理我的消息。
我這人天生比別人少根筋,漸漸也不將這事情放心上,回到家,一心好吃好喝,養點膘,熱情迎接大三的新生活。
2
在教育部招生計畫的指導下,A大逐年擴招,以前老校區早就已經擠不下了。所以學校將一二三年級的學生都安排在新修的西區,到了大四或者研究生才回到校本部。
西區在離A城市區有幾十公里的小鎮上,周圍大部分還是農田。所以,別說逛街,就是找點娛樂項目都很難。
我們宿舍裡一共就四個人,我、白霖、宋琪琪還有趙曉棠,而且都念一個班。
每週週末吃了晚餐無聊的時候,我就和宋琪琪去學校外面看電影。那個所謂的電影院,其實僅有一個放映廳,只放盜版,不播正版。所以要是想看新上映的電影得比城裡面晚許多天。一張票卻只要八塊錢,若是預存一百塊就可以辦張會員卡,票錢還能折成五元,這個價格可是非常吸引人。
但是我和宋琪琪都沒有卡,可是又心疼那多出來的三塊錢,於是──
「我買兩張七點的票。」宋琪琪遞了二十塊錢過去。
「有卡嗎?」大嬸問。
「有、有!」宋琪琪回頭朝我使了個眼神,「小桐,妳那卡呢?」
「喔。」我打開手袋,裝模作樣地翻錢包。
「快點,帶了嗎?」宋琪琪問。
「哎呀!好像忘記帶了。」我驚呼。
「啊,那可怎麼辦啊?」宋琪琪哀嘆,然後將二十塊錢收回來。
「只好不看了。」我說。
「唉……」宋琪琪長嘆一聲。
「阿姨,」我走上前甜甜地叫了一聲,「阿姨啊,我們辦了卡的,但是今天忘記帶了,妳就賣兩張會員票給我們吧。」
大嬸將信將疑:「真的?」
「真的有,今天忘記帶了。」我急忙點頭,可憐巴巴地望著對方,「要回去拿就來不及趕開場了。我們一個星期就這會兒有時間,其他晚上都上自習,好好學習呢。我一天才十塊錢生活費,這一張票要是能省出三塊錢,也能讓我多買份肉了。」
我說得幾乎聲淚俱下。
大嬸瞧了瞧我:「妳這孩子真是忒瘦了。好吧,下次記得帶啊。」
我拿著票回頭偷偷朝宋琪琪做了個勝利的手勢。
這個方法我們用了N次,屢試不爽。後來,只要是那位好心的大嬸看到我,連卡都不查了,直接對旁邊的人說:「嗨,這孩子我認識,老會員了。」
在知了還在樹上苟延殘喘的季節,我進入了大三。這學期有一門我們期待已久的必修的選修課──二外。
A大外語學院分了英語、日語、德語、俄語、法語五個專業,所以我們的二外也是在日、德、俄、法中間選。這些年,日語和法語很緊俏,導致英語系裡選修日語和法語的也特別多,有時候一個班都裝不下,還要增班。
我們宿舍右邊住的日語系的同學,其中一個和宋琪琪是老鄉,每天來串門都要說他們某個師兄學了日語如何如何有出息,去了日資企業的生活又如何如何逍遙。
「唉,其實吧,我覺得你們當初不應該學英文的。」小日語又開始哀嘆。
「為什麼?」宋琪琪反問。
「只要念過書的人都會這個,學出來有什麼用?」小日語一臉高冷地嘲諷著,完全不管別人的感受。
宋琪琪脾氣好,笑笑了事。
「我們去年畢業的一個師姐,畢業後幫人家翻譯日本動漫,可賺錢了。後來人家覺得她聲線好,如今送她去了日本培訓,還想讓她配中文來著。」
我忍無可忍地從上鋪翻下來,冷嗤一下:「是啊,多好,看愛情動作片都不需要翻譯。」
小日語沒說話。
我對著鏡子梳了梳頭髮,又說:「你們那個師姐配什麼音呢,是不是一直說『亞美爹』、『克莫奇』啊?」
小日語的臉抽搐了一下。
她以前在宋琪琪面前炫耀,因為宋琪琪性格溫和從來沒反駁她什麼,她就變本加厲。如今見到我諷刺她,估計才覺得難堪。
「我去吃飯了,真是『哈次卡西』呀!」然後,我拿著飯盒,害羞地掩面出門。
原本,我一直抱著推廣以上影片的夢想而立志二外學日語的,但是小日語的反覆出現讓我打消了這個想法。
正當我迷茫的時候,白霖帶來了一個消息。
「我要選俄語!」白霖在宿舍裡高呼。
「俄語?」我吞了一口米飯,「妳想去當愛斯基摩人?」
「小桐。」白霖看了我一眼,「妳的路痴程度加劇了,能將俄羅斯人和愛斯基摩人扯一塊去。」
「不都是什麼斯人嗎?不都是在北極嗎?」我據理力爭。
宋琪琪插嘴問:「怎麼突然想學俄語呢?妳前段時間不是說選法語嗎?」
白霖笑咪咪地說:「今年系裡分來教我們俄語的老師啊,超級帥。就是那個團委的老師,今天他在食堂一出現,我們全部都被征服了。」
就是拜白霖的這句煽動語所賜,我也被拉去選了俄語。
3
俄語課一周兩節,設在星期一的晚上。
沒想到這一屆選俄語的人呼啦一下冒出許多,完全超出系裡面的預料,不得不換了一間大教室,完全有趕法語、超日德的趨勢。
第一節開課前,俄語系的老主任專門來了一趟,無非是鼓勵大家好好學習之類的,其間看著下面濟濟一堂的求知學子們,幾欲老淚縱橫地又說:「同學們,想當年,我們外語學院還稱外語系的時候,只有俄語一個專業。那個時候,全國上下都掀起了學俄語的浪潮,不懂俄語出去就等於文盲一樣。後來隨著蘇聯解體,俄羅斯實力的衰退,有的人甚至預言我們俄語走到了盡頭。今天,看到你們,我才知道俄語的第二春又來臨了!」
「傅老夠激動的。」我說,「都快感動得哭了。」
「是啊。他老人家要是知道真相,會哭得更厲害。」白霖說。
老師叫陳廷,回國之前在莫斯科留學,去年才開始教課。外語學院男生少,男老師更少,年輕男老師少之又少,所以只要稍微年輕一點又未婚的男老師簡直就是稀有動物,倘若模樣再好看點那就是巨星級的大眾偶像了。
陳廷便是其中之一。他個子高高,斯斯文文的,戴了一副眼鏡,據說有種儒雅的感覺。
但是,就是這麼一個人,當我第一節俄語課看到他的時候,失落之情卻溢於言表。
「這也叫帥啊?」
被人騙了,後悔死沒先親自鑑定下。
白霖兩眼放光地說:「這還不叫帥?那妳指個帥的給我看看。」
我將錢包摸出來,抽出裡面的照片說:「這男的才是天下第一帥哥。」
白霖興致勃勃地接過,照片是張雙人合影,我旁邊站著個中年人,白白胖胖挺著個啤酒肚,一臉彌勒佛的喜慶模樣。
「妳就少拿妳爸的英姿來寒磣我們了。」白霖沒好氣地說,「也不知道是老爸的形象太偉大,還是妳整個人生觀、價值觀、審美觀這三觀都有問題。」
「妳才三觀有問題。」我就一直覺得男人長得像我爸那種才算英俊。
此刻,只聽陳廷在講臺上說:「我是個不點名的人,我一直以為要用點名冊來維持上課人數,其實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
底下有男生偷偷鼓掌。
「有時候你覺得我上課無趣,或者臨時有事情不來也可以,也不用向我請假,但是──」陳廷微笑,「來了就要百分之百認真。」
原本這種二外課就和那些必修的公共課是一樣的,有點雞肋的感覺。可是,陳廷是個極有耐性的人,工作也很負責。
一干人從俄語的三十三個字母起頭,開始了英俄混雜的生活。
下了自習,我和白霖提著溫水瓶去開水房打水,路上突然遇見隔壁班那個讓我背黑鍋的鍾強。
我用冰封一樣的眼神剜了他一眼。
「小桐啊,那事後來不都了了嗎?妳就饒了我吧。」鍾強說。
「呸!小桐小桐也是你叫的?」白霖唾棄他,「這種男人沒擔當,別理他。」說完,拉起我就走。
中途,白霖對我說:「上次抓妳的那個老師還挺好的,後來再也沒怎麼樣了,但是我們怎麼從來沒在學校見過他呢?」
「是不是老師都還不一定呢。看他長得那樣,就跟個小混混似的,說不定就是偷了個工作證的冒牌貨。」
雖然事隔兩個多月,我依然提起他就來氣。
陳廷的課挺有意思的,人也有趣。但是老師的魅力比起外面的花花世界和網遊裡的跌宕人生終究氣場弱了些。經過了一個月,當全班同學發現他真的不點名以後,開始翹課。
哪知有一天,七點零一分,陳廷還沒到。
七點零五分,陳廷仍然沒到。教室裡的人開始竊竊私語了。
「不會忘了吧?」有人問。
「怎麼會呢,而且陳老師每次挺準時的。」有人說。
就在嗡嗡嗡的嘈雜聲逐漸放大的時候,一個男人進來了。
男人夾著一本書,閒庭信步地走到講臺上,隨即對著下面淡淡一笑:「陳老師有事不能來,我替他上課,沒想到教室這麼難找。」
全班女生被他那相貌驚得吸了口涼氣,除了我!
我握緊拳頭,頓時想起一句俗語:「仇人見面分外眼紅。」這男人不是別人,正是上次抓了我作弊後,又像一股青煙似的無影無蹤地消失在我校的那個冒牌老師。
如今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陳老師去外地培訓了,我替他給大家上俄語課。」男人說。
有女生舉手:「老師,你是教俄語的嗎?我們怎麼沒見過你?」
我知道,這女的意思是:『老師呀,如果你是外語學院的老師,是怎麼躲過我們的八卦探頭的?』
男人說:「不是,我不是俄語老師。」
大家異口同聲地「喔」了一聲。
「不是學俄語的還敢說自己來代課。」我恨恨地說。
「但是──」男人一頓,「我在俄羅斯待了好些年,水平大概和你們陳老師差不了多少。」
所有人又一起「喔」了一下,意思和剛才又不一樣。
我撇了撇嘴,真是自負。
會說兩句俄語了不起了嗎?我說英文你聽得懂嗎?
只要是討厭的人,真是從頭到腳、從內心到皮囊都惹人厭。
這時另一個女生說:「老師,能告訴我們您叫什麼嗎?」
「我姓慕。」男人說完便拿起桌面的粉筆在黑板上唰唰唰地留下瀟灑俊逸的三個字,「慕承和」。
他轉過身來,眉心舒展:「同學們可以叫我慕老師、小慕、老慕。當然。」他將二指間的粉筆頭輕輕扔回盒子裡,眼梢上揚,盈盈一笑,「想私下叫我承和,也可以。」
白霖突然抓住我的手,激動地說:「小桐,這老師笑起來真是……」她皺了皺眉,「怎麼形容呢,就是四個字的成語,覺得對方很好看那種,怎麼說來著?」
我咬牙切齒地答:「禍國殃民!」
白霖:「……」
| FindBook |
有 3 項符合
獨家記憶 (上下同梱版)的圖書 |
| |
獨家記憶(共二冊) 出版日期:2022-03-11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獨家記憶 (上下同梱版)
如果妳愛上了一個人,妳需要多大的勇氣來表白?
如果他是妳的老師,妳又必須擁有多少毅力與堅持?
他們之間的初遇,十分的戲劇性。
她是考生,他是巡考員,一場烏龍的作弊案,她被抓了正著。
再一次遇見,是在俄語課,
俄語老師有事請假,他是代課老師,而她是倒楣的俄語課代表,
且因為發不出一個音,她被留下來單獨輔導。
從此,她那悠閒舒適的大學生活以「慕承和」為轉折點,悲慘了起來。
「薛桐,梧桐?鳳凰非梧桐不棲?」
「不是,我爸爸姓薛,我媽姓童,就給我取名字叫薛童。後來人家算八字說我五行缺木,我爸就給我改成梧桐的桐了。」
作者簡介:
木浮生
生於蜀地,自小喜歡看書,偏愛書中那些有關兒女情長的橋段。一直記得亦舒的那句話:「做人凡事要靜。靜靜地來,靜靜地去;靜靜努力,靜靜收穫,切忌喧譁。」所以,唯願自己擁有一顆安靜的心。
已出版作品:
《原來我很愛你》
《良言寫意》
《世界微塵裡》
《獨家記憶》
《時光行者的你》等。
章節試閱
第一章 海狸先生◎VS◎阿童木小姐
1
今天考兩門,上午毛概,下午法律。
我先前辛辛苦苦地將複習資料上的題目全部請教好答案,謄了一遍,又拿去縮印,回來用剪刀剪成豆腐乾模樣,再送去印。來來去去,活活折騰了一天,比那些臨時抱佛腳而半夜背書的人還用功。
發考卷的時候看到那些試題,我驟然有點喜極而泣了。功夫不負有心人啊,居然在昨天抄答案的時候,將那些知識點記了個大概。
本人心情頓時大好,剛想將紙條收好卻感到一個帶著諂媚的炙熱眼神落到自己身上。
「薛桐,借我用用吧。」坐在我旁邊,中間隔了條走道的鍾強討好...
1
今天考兩門,上午毛概,下午法律。
我先前辛辛苦苦地將複習資料上的題目全部請教好答案,謄了一遍,又拿去縮印,回來用剪刀剪成豆腐乾模樣,再送去印。來來去去,活活折騰了一天,比那些臨時抱佛腳而半夜背書的人還用功。
發考卷的時候看到那些試題,我驟然有點喜極而泣了。功夫不負有心人啊,居然在昨天抄答案的時候,將那些知識點記了個大概。
本人心情頓時大好,剛想將紙條收好卻感到一個帶著諂媚的炙熱眼神落到自己身上。
「薛桐,借我用用吧。」坐在我旁邊,中間隔了條走道的鍾強討好...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上冊】
第一章 海狸先生 VS 阿童木小姐
第二章 慕容承和公子 VS 玫瑰花小姐
第三章 明月 VS 溝渠
第四章 左撇子 VS 右撇子
第五章 你是否知道
第六章 左邊
第七章 心的牆
【下冊】
第八章 太陽噴嚏人
第九章 聽見
第十章 保加利亞玫瑰
第十一章 親愛的橡樹
第十二章 青桐有心葉相承
第十三章 Mоя Девушка(我的女孩)
番外一 臨時演員
番外二 借書記
第一章 海狸先生 VS 阿童木小姐
第二章 慕容承和公子 VS 玫瑰花小姐
第三章 明月 VS 溝渠
第四章 左撇子 VS 右撇子
第五章 你是否知道
第六章 左邊
第七章 心的牆
【下冊】
第八章 太陽噴嚏人
第九章 聽見
第十章 保加利亞玫瑰
第十一章 親愛的橡樹
第十二章 青桐有心葉相承
第十三章 Mоя Девушка(我的女孩)
番外一 臨時演員
番外二 借書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