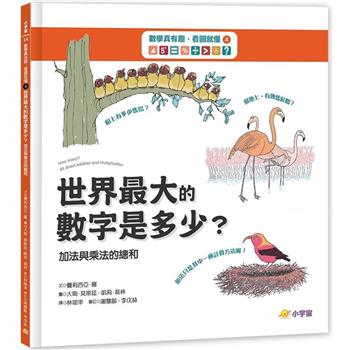《寫字年代》
周夢蝶甫承受親人死別的嚴酷打擊,卻同時得到象徵國內藝文界最高榮譽的第一屆國家文藝獎,煎熬之下接受獎項的原因,竟只是「不忍澆人冷水」;
聶華苓的愛荷華國際寫作計畫超過四十年,讓他家的客廳成為無國界的作家聚集場所,全球三百多位知名作家更聯名推薦他為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
擅寫小說的洪醒夫,應邀投稿小品文,報紙刊登後不到一個月不幸因車禍離世,小品文遂成為小說家的最後遺作……
那是個執筆的人的風華年代,所有通訊聯繫還是以書寫為主要方式的懷念歲月。
因為創作以及工作職務的關係,向陽與學界、文壇等諸多學者、作者魚雁往返,從前行代的楊逵、龍瑛宗等幾近喑啞,卻又謙遜雍容地試圖跨越語言的艱困;到同輩份的陳芳明、阿盛等在政治或者鄉土中,努力尋求屬於一代人的聲音。斑駁的手稿,串連起戰前至解嚴後的臺灣文壇。二十四位名家,二十四個故事,多重身分的向陽以謹慎的學術之筆,浪漫的詩人情懷,客觀的編輯態度,將被時代迅速湮沒的墨痕溫度,一一重新在紙上點燃。儘管歲月催人,筆跡的力道猶存,於普遍習慣透過電腦打字的今天,再現那蘊含於一筆一畫裡的動人情感。
《寫意年代》
一九七○、八○年代的臺灣,是變動與美好兼存的年代,在黨政高壓監控下,文壇歷經白色恐怖、鄉土文學論戰、美麗島事件的震動,卻也孕育出新生的力量。政治解嚴後本土意識抬頭,文壇繁花競放。當時任職《自立晚報.副刊》的向陽,風雲際會,與作家們以文會友,以筆傳情,寫出了相惜相攜的溫暖情緣,共創寫意年代,也見證了波瀾歷史。
二十四則手稿故事,在歲月的印痕中,照見了二十四位作家對理想的堅持,為臺灣在地文學積極發聲的身影。這些身影中,對臺灣詩壇具啟發性的郭水潭、唐文標,推動臺語文運動的黃勁連、楊青矗,勇於批判威權體制的巫永福、渡也、王拓、李敏勇、施明正,深耕在地文化的王灝;展現個人新詩美學的楊熾昌、辛鬱、趙天儀、白萩、羅門、蓉子、林燿德;走過日治時代,以外省作家身分寫本土礦工題材的王默人,對晚輩提攜不倦的元老級小說家鄭清文,還有經營出版社,對本土作家看重的林海音、林佛兒、隱地。
他們多數經歷臺灣文學史上的鄉土文學論戰,曾遭受政治迫害,或為當時百家爭鳴的詩社花圃中留下經典,或以勇猛的身姿,為戰後新生代的後輩作家奠定基石。光陰匆匆,青絲轉鶴髮,向陽從風化泛黃的信稿,抽一縷精魄,帶領讀者重返寫字年代,為輝煌的歲月留住感動與溫情。
★ 以圖輔文,從相片與信札重回八○年代臺灣文壇歷史現場,感受文友間彼此真摯的友誼。
作者簡介:
向陽
本名林淇瀁,臺灣南投人。美國愛荷華大學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國際寫作計劃)邀訪作家,政治大學新聞系博士。
曾任《自立晚報》副刊主編、《自立》報系總編輯、《自立晚報》副社長兼總主筆。現任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教授。獲有吳濁流新詩獎、國家文藝獎、玉山文學獎文學貢獻獎、榮後臺灣詩人獎、臺灣文學獎新詩金典獎、教育部「推展本土語言傑出貢獻獎」等獎項。
著有學術論著、詩集、散文集、評論集、時評集等四十多種;編譯作品三十餘種。
章節試閱
《寫字年代》
「孤獨國」詩人──周夢蝶的雪與火(摘錄)
●
清明返鄉,從溪頭向陽書房中找出三箱書信帶回暖暖。某晚得空整理了其中一箱,發現一張獨特的明信片,背面空白,正面是詩人周夢蝶先生寄給我的明信片。上書:
南投縣鹿谷鄉
溪頭
林淇瀁 先生
諸書已絕版。廣告誤登。乞諒之。
臺北市武昌街一段五號
周夢蝶謹答
明信片上的郵戳「臺灣 64.2.1 15臺北」,顯示了寄發的年度和地點,算來距今三十七年了。
一九七五年一月,放寒假了,我返回溪頭家中,買書只能根據詩刊、書目郵購,印象中是在某本詩刊上看到夢蝶先生的詩集有售,於是寫信求購於他。這張明信片就是他的回函了。
對於一個二十歲的愛詩青年來說,夢蝶先生當時已是詩壇名家,對於一個我尚未毫無詩名的後生小子,大可不理不睬,想不到他會如此慎重其事,端正濡墨,以他清瞿、有名的瘦金體字回覆我的請求。
這張明信片,因此這樣被我保存了下來,在溪頭的書房之中,一待就是三十七年。這張明信片並不完整,右側的缺角,彷彿歲月,在飛逝之餘,留下了無法避免的殘缺。
三十七年過去,如今的我五十七歲,與夢蝶先生當年年紀不相上下。回想從年輕時至今,與夢蝶先生的往來卻也其淡如水。對他,我至今依然懷有著最早收到這張明信片時的恭敬與感念。那恭整、清瘦的字跡,一如他的人與詩,帶有某種孤獨、枯乾,而又傲然、冷峻的格調。那是「赤裸裸地趺坐在負雪的山峰上」(〈孤獨國〉詩句)的主人。
●
要等到一九七七年四月,我自費出版了我的第一本詩集《銀杏的仰望》之後,我才與夢蝶先生有了稍微多一點點的對話。在他的詩攤前,從陽明山搭公車下山的我,帶著一疊詩集,其中一本贈書,其餘(約十本吧)則託售於他。夢蝶先生說:「好,你放著,賣完了再來結。」,我說:「好,謝謝周先生。」就是這樣。
然後,我當兵去了,也沒問詩集賣得如何。一九七八年五月,我在高雄小港當兵,在書店中買到了周夢蝶詩集《還魂草》(臺北:領導出版社),這是一九六五年文星版的重刊本,也收了《孤獨國》的部分詩作。封面是夢蝶先生的畫像,照換了我對他的想念。當時我因為好友陳銘磻之邀,在他主編的《愛書人》雜誌開了「向陽專欄」,於是就以〈還魂讀夢蝶〉為題,發表了我的讀後感。其中有幾句是這樣說的:
「於雪中取火,且鑄火為雪」,讀《還魂草》,我們看到了一棵心靈常處在對立的兩極:雪與火,紅與黑,生與死……的不斷替代、糾葛、衝突中……。那是生命在不斷投入、脫出中歷練的大悲,是情智在輾轉分化、交融裡煎熬的至苦,只有行到水窮處,才能坐看雲起時的。
文章發表後,我找了一個休假日到臺北,將之面教夢蝶先生,彷彿是對當年收到明信片之情的一種答報,表示一個年輕詩人對他的敬意。夢蝶先生只說:「謝謝你。」接著忽然想到甚麼似的:「你的詩集賣完了,要不要結?」我聽到詩集賣完,這就夠了,答以:「可不可以換詩集?」夢蝶先生點頭,我挑了幾本詩集,便算結了帳。這是我與夢蝶先生奇特的往返經驗,我們以詩集易詩集,做了一次「生意」。
●
一九九七年,夢蝶先生以其詩藝成就獲第一屆國家文藝獎,評審委員會擬定的「得獎理由」由詩人瘂弦主草,末段指夢蝶先生:
人格風格高度統一,文學哲學渾然一體,建構出一個完整的心靈世界。在當今文壇,以苦行堅持個人情志、完成文學事業、淡泊自持、無怨無悔如周先生者,洵屬少見。
說的也正是他鎔鑄文學之火、哲學之雪而建構出的澄明境界。我當時忝任評審委員之一,由於委員會擔心夢蝶先生婉拒領獎( 而依他的狷介個性,這是極有可能之事 ),乃指派我與他聯繫,請他接受此一榮譽。我受此高難度任務,便與夢蝶先生聯繫,約了一個週日上午到他在新店的住處看他。還記得當天風和日麗,我準時到達,見了夢蝶先生,向他說明來意,也希望他了解國家文藝是經由嚴謹的評審過程所產生,是全體委員不帶感情地對他作品成就的肯定,請他萬勿謙辭。
十多年過去,我如今已經忘了我當時如何組織那些我所講的話,只記得夢蝶先生只是傾聽,有時回應一聲,如我年輕時在武昌街見他一樣。也許是我說的,讓他難以拒絕吧,最後他接受了。頒獎典禮之後,我讀到記者史玉琪訪問夢蝶先生的稿子,這才知道當時他才剛自中國大陸探親回來,承受了「得知母親、二子故去,妻子改嫁也故去,長子得見最後一面,只剩一個女兒在」的生命中最嚴酷的打擊。原來我去拜訪夢蝶先生,遊說他請勿婉拒國家文藝獎時,他是在這樣的苦境之中,在這樣的煎熬之下;原來他之接受國家文藝獎,是因為「不忍澆人冷水」,是因為「接受比拒絕容易」。而當時的他,有的是「人在病中,慘澹經營」的感覺。
十多年過去,我開始漸漸明白夢蝶先生當日自苦而不苦人的謙遜。他的內在世界深藏於詩作最底層,不輕易示;但同時他又是一個多情之人,用葉嘉瑩教授的話說,他有著屬於「火」的沉摯的凄哀,也有著屬於「雪」的澄淨的凄寒。他的孤獨,源自於此;他的受人敬重,也源自於此──這在他寫給二十歲的我的明信片上,如此;在他寫給年輕躁進的「陽光小集諸仁者」的題墨中,也是如此。
《寫意年代》
沉默的巒峰
──巫永福以詩長青
一、
秋夜讀詩,讀到詩人巫永福寫於一九五○年代的一首詩〈沉默〉,不禁油然想起這位與我同屬南投縣出身的前輩的身影。巫永福先生,一九一三年生於山明水秀的南投埔里,從日治時期出發,跨越兩個時代,先後使用日文和中文寫作,逝世於二○○八年九月十日,享壽九十六歲,出道既早,寫作生命也存續甚久,可說是臺灣「跨越語言的一代」作家中的長青樹。
〈沉默〉這首詩詠讚中央山脈的巒峰,通過埔里的開發過程,寫出在臺灣被殖民的歷史之下人與土地的關係:
中央山脈的巒峰告訴我們
告訴我們故鄉城鎮的歷史
有如守護者 悠悠然地
把城鎮造成之前 之後
長久歲月的愛憎悲歡
城鎮角落的生死離別
激烈無比的爭鬥變遷
詳細地告訴我們 那巒峰
時而欣喜似地燃紅
時而瞭解似地點頭
時而哀傷似地消沉
也會打顫身心而憤怒
然而巒峰知曉得太多
致過分勞累了
終於很美麗地沉默下來
以安逸的姿態橫臥下來
這詩中「終於很美麗地沉默下來/以安逸的姿態橫臥下來」的巒峰,也是我童年時代每天面對的峰巒。巫永福先生筆下的中央山脈有如觀音橫臥,美麗而沉默,既是一首動人的地誌詩,同時也透過「長久歲月的愛憎悲歡/城鎮角落的生死離別/激烈無比的爭鬥變遷」表達出強烈的歷史感,指點出漢人來臺拓植、日本殖民和戰後初期歷經二二八事件之後的土地創傷。秋夜讀這首詩,追想前賢行誼,以及他堅毅而有威嚴感的臉容,這詩彷彿也是他生命的自述。
二、
我與巫永福先生初識於一九八○年代。我於一九七六年開始在《笠》詩刊發表臺語詩,與詩人趙天儀熟識,接著是陳千武,一九八一年我進入《自立晚報》編輯副刊,與日治年代出發的臺籍作家有了密切的來往,印象中與巫永福先生認識是在小說家王昶雄先生主催的「益壯會」聚會中;同年我應陳千武先生之邀,與笠詩社同仁到東京參加日本地球詩社三十周年祭,與當時年近七十的他在旅行中有了更多的交談;一九八二年一月,由陳千武先生主催的「中日韓現代詩人會議」在臺北召開,巫永福先生被舉為中華民國代表團團長,由於他和千武先生與我有同鄉(出身南投縣)之緣,因而更覺親切,而有了更進一步的往來。
這個階段我認識的巫永福先生是詩人。他的詩部分由千武先生自他日治時期的日文詩作譯為中文,部分則是他以自習的中文寫出。日文譯作有一首〈祖國〉,於一九七二年出版的《笠》第五十二期發表,這首詩控訴日本人的殖民統治,呼喊「祖國喲 站起來」,在鄉土文學論戰前後成為名作;中文作品有〈泥土〉一詩,起於「泥土有埋葬父親的香味/泥土有埋葬母親的香味」,結於「嫩葉有父親血汗的香味/嫩葉有母親血汗的香味」,表現鄉土的美感,也成為名作。我讀他的詩,可以深刻體會到他對土地的熱愛,也可以感覺到他在跨越日文和中文鴻溝之間的難以暢言。但這無損於作為詩人的他,在詩作當中潛藏的奮進、堅定和開朗的精神。
然而,巫永福先生對於成為一個小說家似乎更耿耿於懷。有一次聊天時,他對我說:「我其實更想成為一個小說家,日本時代我寫過一些小說,用日文書寫,順暢多了,用中文來寫,總是有未順的感覺。」沒錯,他二十歲時就考進東京明治大學文藝科(一九三二),受教於菊池寬、橫光利一等大師,受到日本新感覺派作家的深厚影響;同時也和張文環、王白淵、曾石火、吳坤煌等人共組「臺灣藝術研究會」,創刊了《フォルモサ》(福爾摩莎)雜誌(共三期),陸續發表了小說〈首與體〉、〈黑龍〉等小說,受到矚目。如果不是因為戰後的語言轉換,他一定可以成為一位大小說家,而不只是詩人。但這樣的悲哀,不止於他,龍瑛宗、張文環也都有著同樣的苦痛。巫永福先生最後以詩人定位,雖非所願,但能持續書寫,他從日文新詩到短歌、俳句,從中文現代詩寫到臺語詩,作品豐富繁多,也是一種幸福了。
巫永福生前有《巫永福全集》二十四卷傳世,其中詩集就有七卷、評論集三卷、文集兩卷、小說兩卷,此外另收日文創作小說一卷、日文詩一卷、俳句兩卷、短歌兩卷、短句俳句一卷、臺語俳句兩卷,也以詩作為多。詩人李魁賢曾加以統計,說巫永福的創作量「詩大約九百首、小說十五篇、散文大約一百五十篇」,就可看出他的主要創作領域還是在詩。詩,讓巫永福先生長青。
三、
巫永福先生之所以在臺灣文壇長青,另一個因素,則在他對推動臺灣文學運動與發展的關注。除了年輕時組織「臺灣藝術研究會」,創刊《フォルモサ》雜誌之外,他在日治時期還參與了「臺灣文藝聯盟」(一九三五)的行列,為《臺灣文藝》供稿;參加張文環等創刊的《臺灣文學》雜誌,並與鹽分地帶作家吳新榮、郭水潭等時相往來。戰後他有一段相當長的時間遠離文學,加入實業界,到一九六五年出任東京短歌雜誌《からたす》臺北市部長,也加入臺北歌會、臺北俳句會;一九六七年加入《笠》詩社;一九六八年創立《臺北歌壇》;一九七七年接任《臺灣文藝》發行人;一九七九年創立巫永福評論獎;一九八四年,加入臺灣筆會;一九九三月成立「財團法人巫永福文化基金會」,將巫永福評論獎分為「巫永福文學評論獎」、「巫永福文化評論獎」及「巫永福文學獎」……。這些具體時績,都說明了他對臺灣文學的關注和參與之深,他的書寫和他的參與,讓他受到文壇與社會的肯定。
我手邊有一篇他寫於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三十日的手稿〈臺灣的長青樹──讀謝里法著「臺灣出土人物誌」有感〉,以六百字稿紙寫了十四張半,字數長達八千七百字。在這篇屬於讀後感的文論中,他追憶謝里法書中所寫黃土水、劉錦堂、張秋海、王白淵、陳澄波、郭雪湖、范文龍、江文也等八位藝術家與他的人生因緣,文字相當動人。他除了追記這八位臺灣傑出藝術家的生平之外,同時也以自身的創作經歷回顧從日治時期到戰後的臺灣文藝界發展,顯現了他對於臺灣文學與藝術界的瞭若指掌,在這篇長文中,除了這八位之外,他隨手提到的藝術家就有田王孫(王王孫?)、溥儒、張李德和、黃清呈、陳夏雨、蒲添生、顏水龍、廖繼春、李石樵、李梅樹、楊三郎、洪瑞麟、張萬傳、林玉山、林之助、陳進、張大千、黃君璧、郭芝苑……等,足見他不僅關心文學,對於藝術界的大家也相當重視並且互有往來。細讀他的這篇舊作手稿,讓我深刻感覺到巫永福先生的博學多識,以及他內心深處對於同屬日治時期出發的臺籍菁英惺惺相惜之情。
這篇長文末段說:「臺灣人自己的獎勵才是真正的獎勵」,更是動人,這或許也是他生前創設「巫永福評論獎」的初心和決志之所起吧。他以「臺灣的長青樹」為題來形容黃土水、劉錦堂、張秋海、王白淵、陳澄波、郭雪湖、范文龍、江文也等八位藝術家,指的應是他們的藝術成就,而非人生遭遇。這八位都是在大動亂年代中被埋沒的藝術家,人生際遇實際上並不「長青」,真正長青者,如今看來,似乎也非巫永福先生莫屬了。
四、
我在主編《自立晚報.副刊》階段,與巫永福先生往來頻仍,他喜歡自立晚報這份臺灣人的報紙,也常投稿給副刊,多半是像〈臺灣長青樹〉這樣的長稿,而副刊有字數的限制,有時很難來稿就登,巫永福先生頗能體諒我這個小輩的難處,並不苛責。
有一次他寄來一篇〈小談臺灣現代詩〉,字數甚多,我斟酌甚久,最後還是附信退了稿,懇請他另賜短作,幾天之後接到到他的回覆:
回稿與信均悉。「小談臺灣現代詩」要在報上刊登略長,其中所寫人名太多,但這我是有用意的。
遵示以報導色寫了「紀弦的天真」,雖比你指定的一千五百長略長,二千多字即請原諒。
「再談彩繪」內有中國歷代畫院制度等,可作臺灣彩繪界的參考,屆時請寄副刊三分給我便轉送國外……
這封信讓我愧疚許久,信末「86.10.20」是我標記的來稿日,此時的巫永福先生年七十四,對我的退稿並無怨言,相對凸顯了我的無知。他以七十四高齡仍潛心寫作,所寫之文也非沒有參考價值,只因文字稍長,就被我退了,成為我編輯生涯倍感遺憾之事;巫永福先生不以為忤的態度,則讓我從中學習到了長輩寬闊的胸懷,我保留此信,加註日期,當時大概也有自惕自勉的想法吧。
一九八七年前後,正處戒嚴/解嚴交替時期,臺灣筆會自一九八四年成立之後也常參與社會運動行列,走上街頭,抗議執政的國民黨,反對政治迫害,當時的老作家中,巫永福先生也常與我們年輕作家一起走上街頭。他滿頭白髮,與我們同行,不僅有鼓舞年輕人的力量,同時也彰顯了不同世代臺灣作家對於自由民主與人權的共同主張。我至今仍保存當時在街頭為他拍攝的照片,他在抗議隊伍中領頭,手舉草帽,上纏「反對政治迫害」布條,白髮蒼蒼,面帶微笑,為他走過的人生、時代做了最鮮明的見證,也為臺灣的政治民主做了最堅定的宣示,這樣的精神,讓我想起他寫的一首詩〈含羞草〉中的兩句「氣憤地站在山坡上/為討回公道向風呼喚」。他以耄耋之年走上街頭,應該也有著這樣坦蕩、磊落的心境吧。
我從副刊主編轉任總編輯之後,由於工作關係,處理的都屬新聞和政治事務,與文壇的接觸日稀,但每次碰到巫永福先生,他總還是精神抖擻,不忘鼓勵我這同鄉晚輩。印象最深刻的是,每次參與文學界聚會,他總是坐在最前排聆聽,有時會站起來說話,他的中氣十足,一點也不顯老態;話語有時慷慨,但總不忘期許後輩為臺灣文學打拚。他的確是臺灣文壇的長青樹,從日治年代走來,走過白色恐怖年代到臺灣,走到可以隨心所欲的自由年代,一貫充滿鬥志,也充滿生氣!
我在秋夜懷念他,懷念「終於很美麗地沉默下來/以安逸的姿態橫臥下來」的他,這才知道他不只是文壇長青樹,還是護持臺灣的巒峰。
二○一五年八月
《寫字年代》
「孤獨國」詩人──周夢蝶的雪與火(摘錄)
●
清明返鄉,從溪頭向陽書房中找出三箱書信帶回暖暖。某晚得空整理了其中一箱,發現一張獨特的明信片,背面空白,正面是詩人周夢蝶先生寄給我的明信片。上書:
南投縣鹿谷鄉
溪頭
林淇瀁 先生
諸書已絕版。廣告誤登。乞諒之。
臺北市武昌街一段五號
周夢蝶謹答
明信片上的郵戳「臺灣 64.2.1 15臺北」,顯示了寄發的年度和地點,算來距今三十七年了。
一九七五年一月,放寒假了,我返回溪頭家中,買書只能根據詩刊、書目郵購,印象中是在某本詩刊上看到夢蝶先生的詩集...
目錄
《寫字年代》
墨痕深處,溫潤長在──《寫字年代:臺灣作家手稿故事》序
園丁的叮嚀──齊邦媛與國家文學館
慈悲喜捨的樹──聶華苓與IWP
田園躬耕的隱者──陳冠學與《自立》副刊
建構臺灣主體論述的史家──葉石濤與《臺灣文學史綱》
臺灣文壇的老園丁──中秋夜懷楊逵
哀傷之禽鳥──商禽詩〈木棉花〉的原始版本
在文學、歷史與政治的交叉口──陳芳明的「陳嘉農」年代
咏唱臺灣庶民心聲的歌者──王禎和及其〈人生歌王〉
臺灣文學史的墾拓者──黃得時及其臺灣文學論述
定型新詩的倡議者──周策縱及其「棄園」詩情
「醬缸」文化的批判者──柏楊與〈醜陋的中國人〉
「孤獨國」詩人──周夢蝶的雪與火
臺灣的心窗──王昶雄及其〈阮若打開心內的門窗〉
臺灣文學明燈──鍾肇政與《臺灣文藝》
為母土而書寫──阿盛與「散文阿盛」
喑啞的能言鳥──龍瑛宗的書寫語境
鄉里人物的刻繪者──追憶洪醒夫
亞細亞文學交流的鼓手──陳千武與《亞洲現代詩集》
文學傳播的掌舵者──蔡文甫與九歌出版社
臺灣農民的守護者──吳晟及其詩文
臺灣客語文學的女人樹──杜潘芳格及其客語詩
臺灣現代詩壇的「行動派」──張默與年度詩選
把草原上的月光寫入詩中──側寫席慕蓉
美麗島的玉蘭花──陳秀喜的人生與詩作
《寫意年代》
地層下的採礦人──王默人的礦工書寫
喑啞的詩人──被時代遺忘的郭水潭
亦狂亦狷一大俠──唐文標的文學夢
薔薇與砲火──楊熾昌的超現實與現實
曠野盡頭一匹豹──辛鬱的冷與澀
沉默的巒峰──巫永福以詩長青
爾雅出版家──隱地與《人生船》
為臺灣塑像──趙天儀的童心與詩心
孤岩的存在──白萩其人其詩
一尾活龍──臺語歌詩健將黃勁連
龍哭千里──溫瑞安與神州詩社傳奇
孤獨憂鬱的「魔鬼」──施明正的愛與死
總是和「鄉土文學」連結在一起──我所認識的王拓
從玫瑰到野草──渡也的詩路歷程
衝決暗房──李敏勇的現實主義詩學
現實、社會與民族的拉扯──陳映真的複雜圖像
飛成一隻鳥──以詩為宗教的羅門
心心念念為臺灣──林佛兒的文學與出版志業
為臺灣工人代言──即知即行的楊青矗
大埔城文化推手──詩書畫三絕的王灝
「新世代」旗手──英年早逝的林燿德
臺灣作家保母──林海音的包容與慈悲
永遠的青鳥──蓉子的溫婉與強韌
淡彩寫人間──鄭清文小說中的悲憫情懷
《寫字年代》
墨痕深處,溫潤長在──《寫字年代:臺灣作家手稿故事》序
園丁的叮嚀──齊邦媛與國家文學館
慈悲喜捨的樹──聶華苓與IWP
田園躬耕的隱者──陳冠學與《自立》副刊
建構臺灣主體論述的史家──葉石濤與《臺灣文學史綱》
臺灣文壇的老園丁──中秋夜懷楊逵
哀傷之禽鳥──商禽詩〈木棉花〉的原始版本
在文學、歷史與政治的交叉口──陳芳明的「陳嘉農」年代
咏唱臺灣庶民心聲的歌者──王禎和及其〈人生歌王〉
臺灣文學史的墾拓者──黃得時及其臺灣文學論述
定型新詩的倡議者──周策縱及其「棄園」詩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