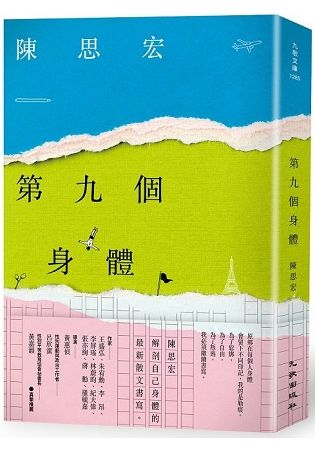原鄉在每個人身體會留下不同印記,我的是勒痕。我嚮往城市,歐洲電影,文學旅行,自由恣意,紐約巴黎。……身體有勒痕,為了鬆綁,為了自由,為了再度叛逃,故鄉在後追趕,我必須繼續書寫。
一九七六年,陳思宏在彰化縣永靖鄉出生,陳家第九個孩子。在絕對重男輕女的環境下長大,從小被寵,習慣父權思考。這套堅固的守舊在他身上卻註定失效,因為,他無法組異性戀家庭,延續香火。父權的制約與身體持續對撞,開始累積許多隱形傷口。
逼視傷口,陳思宏透過書寫,誠實面對家族記憶、成長路上的跌跌撞撞、遭遇的歧視和異樣的眼光。他審視經歷過的閉鎖與敞開、成年後的身體試煉、以及旅居德國之後的身體思考,從個人細微身體史啟程,呼應島嶼的身體焦慮。
走過暗夜,他勇敢揭露生命之痛,哀感頑豔。移開視線,凝視他人身體,肥肚有故事,皺紋藏記憶,文字聚焦跨界、少數,抵抗主流審美觀點,別闢邊緣身體光譜。行走他鄉,任身體自在揮灑,太陽底下鮮事多,筆走旅行各種怪現狀,畫龍點睛,令人會心爆笑。
如今居住在柏林的這第九個孩子,身體每天都經歷文化交匯與衝突,將坦白交出個人身體履歷。寫傷口,寫長大,寫失落,寫旅行,同時也在找自由……
本書特色
★首刷限量簽名版
★書寫個人的身體成長,寫家族往事、婚禮喪禮、性向啟蒙、鄉野封閉。攤開身體的履歷,揭露傷口。
★寫性別跨越、身體政治、厭女仇恨、恐同狹隘,尊重個人的身體差異,讓少數能生存,有盛開的角落。
★抓取個人異地生活經驗,寫旅行途中的身體變異,寫身體與他者文化的短暫交會。
名人推薦
作家王盛弘、朱宥勳、李昂、李屏瑤、林蔚昀、紀大偉、張亦絢、蔣勳、羅毓嘉
導演黃惠偵
性別運動與政治工作者呂欣潔、性別平等教育協會祕書長黃嘉韻 真摯推薦
| FindBook |
有 1 項符合
第九個身體(首刷簽名版)的圖書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第九個身體(首刷簽名版)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陳思宏
一九七六年在彰化縣永靖鄉八德巷出生,農家的第九個孩子。得過一些文學獎,例如林榮三文學獎短篇小說首獎、九歌年度小說獎。出版作品《指甲長花的世代》、《營火鬼道》、《態度》、《叛逆柏林》、《柏林繼續叛逆》、《去過敏的三種方法》。寫作、翻譯、演戲、主持、叛逆,忙著在德國柏林當個永靖鄉下人。網站:www.kevinchen.de
陳思宏
一九七六年在彰化縣永靖鄉八德巷出生,農家的第九個孩子。得過一些文學獎,例如林榮三文學獎短篇小說首獎、九歌年度小說獎。出版作品《指甲長花的世代》、《營火鬼道》、《態度》、《叛逆柏林》、《柏林繼續叛逆》、《去過敏的三種方法》。寫作、翻譯、演戲、主持、叛逆,忙著在德國柏林當個永靖鄉下人。網站:www.kevinchen.de
目錄
卷一、永靖身體
1.壞掉的老久,肥美的荔枝
2.趕路
3.渾身是勁的凱文
4.泳褲
5.我要變成外國人
6.書本、電影鑄成的盾牌
7.公車
8.火車站
9.體育課
10.#我也是
11.酒肆軍旅行
12.鏽粥
13.變形
14.盜身
15.影展一場夢
16.上電視
17.落髮
18.帥哥
19.囤積花襯衫
20.怕人情
21.痔
卷二、少數身體
1.越界
2.綠週
3.彩虹海芋
4.看鸛
5.男護士
6.小人
7.人言
8.酸甜
9.召喚人文藝術,肢解後真相
10.柏林劇場裡的裸體風景
11.德國沒有博愛座
12.易碎的歐洲時刻
13.希望
14.選後
15.叛逆漢堡
16.慢開的花
17.胖瘦
18.標準
19.丟掉聖誕節
卷三、旅行身體
1.帶二姐去旅行
2.彈孔、恐怖、雕像:布達佩斯的苦與甜
3.文青的都柏林
4.康尼麻拉馬
5.罵葉慈
6.孩子
7.暈眩西西里
8.排隊
9.油雞
10.敘爾特島
11.呂根島
12.重逢啤酒節
13.家醜
14.穿裙
15.世故倫敦
16.空白
17.法國幻想
18.混凝土聖誕
19.臭日子
20.美國心靈小語
21.霧海上的旅人
1.壞掉的老久,肥美的荔枝
2.趕路
3.渾身是勁的凱文
4.泳褲
5.我要變成外國人
6.書本、電影鑄成的盾牌
7.公車
8.火車站
9.體育課
10.#我也是
11.酒肆軍旅行
12.鏽粥
13.變形
14.盜身
15.影展一場夢
16.上電視
17.落髮
18.帥哥
19.囤積花襯衫
20.怕人情
21.痔
卷二、少數身體
1.越界
2.綠週
3.彩虹海芋
4.看鸛
5.男護士
6.小人
7.人言
8.酸甜
9.召喚人文藝術,肢解後真相
10.柏林劇場裡的裸體風景
11.德國沒有博愛座
12.易碎的歐洲時刻
13.希望
14.選後
15.叛逆漢堡
16.慢開的花
17.胖瘦
18.標準
19.丟掉聖誕節
卷三、旅行身體
1.帶二姐去旅行
2.彈孔、恐怖、雕像:布達佩斯的苦與甜
3.文青的都柏林
4.康尼麻拉馬
5.罵葉慈
6.孩子
7.暈眩西西里
8.排隊
9.油雞
10.敘爾特島
11.呂根島
12.重逢啤酒節
13.家醜
14.穿裙
15.世故倫敦
16.空白
17.法國幻想
18.混凝土聖誕
19.臭日子
20.美國心靈小語
21.霧海上的旅人
序
自序
敞開身體書寫
我敞開,坦承,說出口,書寫。
我是彰化永靖鄉下的第九個孩子,在絕對重男輕女的環境下長大,從小被寵,習慣父權思考。但,堅固的守舊在我身上註定失效,因為,我是同志。我無法組異性戀家庭,成家立業,延續香火。我在學院裡閱讀當代性別理論與文本,接觸性別社運,父權制約與我的身體正面對撞,陳家的第九個孩子,身體開始累積許多隱形傷口。
《第九個身體》是解剖自己身體的書寫計畫,誠實面對家族記憶、成長悲喜,寫農家的身體制約、中學的暴力體罰、身為同志的跌撞、遭遇的歧視、成年後的身體試煉、與旅居德國之後的身體思考。我透過書寫審視陳家的這第九個身體,從永靖到台北到柏林,經歷的閉鎖與敞開,從個人身體史啟程。
《第九個身體》不只剖開自己的身體,也書寫他人身體的反叛,以文字重建少數、邊緣身體姿態,聚焦飽受責難的越界身體,抵抗守舊圍勦。
也寫我的個人異地體驗,寫旅行途中的身體變異,寫身體與他者文化的短暫碰撞。旅行找自由,身體奮力游向彼岸,逃亡,找生機。彼岸不見得是應許地,但掙扎是本能,尋光源,找出口。我這第九個身體還在掙扎,還在寫作,還在旅行,還在找自由。
我相信敞開的力道。攤開的書頁掉出詩句,張開的嘴唱出詠嘆,開放的邊界讓人自由遷徙。
這農家的第九個身體剛滿四十二歲,無法抵抗衰老,但不信青春鮮美是唯一美麗的人生季節。敞開,是我的書寫策略。我寫疾病,寫傷口,寫長大,寫失落,其實都是為了爭自由,一步一步,奪回身體的自主權。
這本書,寫給所有承擔污名的少數身體。
敞開身體書寫
我敞開,坦承,說出口,書寫。
我是彰化永靖鄉下的第九個孩子,在絕對重男輕女的環境下長大,從小被寵,習慣父權思考。但,堅固的守舊在我身上註定失效,因為,我是同志。我無法組異性戀家庭,成家立業,延續香火。我在學院裡閱讀當代性別理論與文本,接觸性別社運,父權制約與我的身體正面對撞,陳家的第九個孩子,身體開始累積許多隱形傷口。
《第九個身體》是解剖自己身體的書寫計畫,誠實面對家族記憶、成長悲喜,寫農家的身體制約、中學的暴力體罰、身為同志的跌撞、遭遇的歧視、成年後的身體試煉、與旅居德國之後的身體思考。我透過書寫審視陳家的這第九個身體,從永靖到台北到柏林,經歷的閉鎖與敞開,從個人身體史啟程。
《第九個身體》不只剖開自己的身體,也書寫他人身體的反叛,以文字重建少數、邊緣身體姿態,聚焦飽受責難的越界身體,抵抗守舊圍勦。
也寫我的個人異地體驗,寫旅行途中的身體變異,寫身體與他者文化的短暫碰撞。旅行找自由,身體奮力游向彼岸,逃亡,找生機。彼岸不見得是應許地,但掙扎是本能,尋光源,找出口。我這第九個身體還在掙扎,還在寫作,還在旅行,還在找自由。
我相信敞開的力道。攤開的書頁掉出詩句,張開的嘴唱出詠嘆,開放的邊界讓人自由遷徙。
這農家的第九個身體剛滿四十二歲,無法抵抗衰老,但不信青春鮮美是唯一美麗的人生季節。敞開,是我的書寫策略。我寫疾病,寫傷口,寫長大,寫失落,其實都是為了爭自由,一步一步,奪回身體的自主權。
這本書,寫給所有承擔污名的少數身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