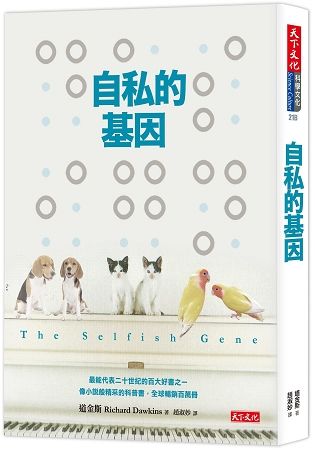這本書充滿想像力,就像科幻小說……
任何生物,包括我們,都只是求生機器,
暗地裡已被輸入某些程式,
用來保養那些叫做基因的自私分子。
這麼說來,我們不都成了基因的俘虜?
但這本書卻是實實在在的科學……
動物也會實施家庭計畫?
父母對子女的照顧,會有大小眼嗎?
雌性擇偶為何比雄性更小心?
工蟻憑什麼要為女蟻王賣命?
好人真的會出頭嗎?
從「自私的基因」觀點出發,這些問題全都可以找到答案。
|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自私的基因的圖書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自私的基因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道金斯Richard Dawkins
英國人,著名演化理論學者,英國皇家學會會士。1941年出生於肯亞,1949年全家返回英國。就讀牛津大學,受業於動物行為學名家丁伯勤(Nikolaas Tinbergen, 1907-1988;一九七三年諾貝爾生理醫學得主),獲動物學博士學位。
1976年,道金斯出版了《自私的基因》這本書,闡釋以「基因」為分析單位的演化觀,因而聲名大噪。
1995年起,擔任牛津大學新設立的科學教育講座教授(Chair of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2001年當選英國皇家學會會士。
道金斯是英國最重要的科學作家,不但每一本書都是暢銷書,並經常在各大媒體討論、評論科學的各個面向。道金斯的暢銷著作中,《自私的基因》為最重要的代表作,《延伸的表現型》(The Extended Phenotype, 1982)次之。此外,《盲眼鐘錶匠》(The Blind Watchmaker, 1986)與續篇《攀登不可能的山》(Climbing Mount Improbable, 1996)都是演化生物學的入門書。
譯者簡介
趙淑妙
東海大學生物系畢業,台灣大學植物學碩士,美國杜蘭(Tulane)大學生物學博士,專長植物分類學及演化。
曾任美國休士頓市德州大學人類遺傳中心客座助教授,中央研究院植物所副研究員、研究員。現任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研究員。
志趣在從事研究工作,並關心社會教育、人權與環境。
道金斯Richard Dawkins
英國人,著名演化理論學者,英國皇家學會會士。1941年出生於肯亞,1949年全家返回英國。就讀牛津大學,受業於動物行為學名家丁伯勤(Nikolaas Tinbergen, 1907-1988;一九七三年諾貝爾生理醫學得主),獲動物學博士學位。
1976年,道金斯出版了《自私的基因》這本書,闡釋以「基因」為分析單位的演化觀,因而聲名大噪。
1995年起,擔任牛津大學新設立的科學教育講座教授(Chair of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2001年當選英國皇家學會會士。
道金斯是英國最重要的科學作家,不但每一本書都是暢銷書,並經常在各大媒體討論、評論科學的各個面向。道金斯的暢銷著作中,《自私的基因》為最重要的代表作,《延伸的表現型》(The Extended Phenotype, 1982)次之。此外,《盲眼鐘錶匠》(The Blind Watchmaker, 1986)與續篇《攀登不可能的山》(Climbing Mount Improbable, 1996)都是演化生物學的入門書。
譯者簡介
趙淑妙
東海大學生物系畢業,台灣大學植物學碩士,美國杜蘭(Tulane)大學生物學博士,專長植物分類學及演化。
曾任美國休士頓市德州大學人類遺傳中心客座助教授,中央研究院植物所副研究員、研究員。現任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研究員。
志趣在從事研究工作,並關心社會教育、人權與環境。
目錄
作者序 我們都是機器人的化身! 道金斯
再版序 新思想在燃燒 道金斯
第一章 為什麼我們是人?
第二章 複製者傳奇
第三章 不朽的雙螺旋
第四章 打造求生機器
第五章 生存策略
第六章 基因的自私算盤
第七章 動物早懂得家庭計畫
第八章 母親你真偉大
第九章 愛情遊戲
第十章 你幫我搔癢,我幫你抓背
第十一章 自私的「瀰」
第十二章 好人還是會出頭!
第十三章 基因無遠弗屆
附錄
名詞注釋
延伸閱讀
再版序 新思想在燃燒 道金斯
第一章 為什麼我們是人?
第二章 複製者傳奇
第三章 不朽的雙螺旋
第四章 打造求生機器
第五章 生存策略
第六章 基因的自私算盤
第七章 動物早懂得家庭計畫
第八章 母親你真偉大
第九章 愛情遊戲
第十章 你幫我搔癢,我幫你抓背
第十一章 自私的「瀰」
第十二章 好人還是會出頭!
第十三章 基因無遠弗屆
附錄
名詞注釋
延伸閱讀
序
序
我們都是機器人的化身!
讀這本書要像讀科幻小說,因為我寫的時候就是希望它充滿想像力。但是本書可不是科幻小說,而是實實在在的科學。雖然「真實的生活比小說的劇情更神奇」這句話聽起來有些陳腔爛調,但正好表達我對事實的感覺。
我們都是求生存的機器──機器人的化身,暗地裡已被輸入某些程式,用來保養這些叫做「基因」的自私分子!這是個如今仍然令我心驚膽寒的事實。雖然我己經知道這個事實多年,卻仍然未法完全接受它。我有個想法:拿這個真理來嚇嚇別人,或許可以得逞。
■像神祕故事一樣引人入勝
我在寫這書時,希望有三種讀者來探班,現在我將本書獻給他們。
首先是一般的讀者,也就是外行人。為了易讀,我幾乎完全避免了深奧難懂的術語,而多用自己定義的特殊字眼來表達我的觀念。在此順便提一下,為什麼我們不把所有期刊中大部分的專業術語都簡化呢?雖然我假設外行人沒有專業知識,但我可沒假設他們都是傻瓜。如果有心的話,任何人都可以把科學普及化。我已盡力嘗試在不失精髓的情況下,用非數學的言語闡釋一些細膩又複雜的觀念。我不知道在這方面是否成功,也不知道能否達成另一野心:嘗試讓讀者覺得看這本書看到欲罷不能,而且是個很好的消遣。
我一直感覺,生物學應該可以像神祕的故事一樣引人入勝。因為神祕的故事正如生物學一樣包羅廣泛。我很惶恐地希望,我能充分表達本書主題的剌激性。
我第二個假想的讀者是專家。他對我某些解說的比喻和數字,竟然批評得喘不過氣來。他最喜歡的措辭是「除了……」、「但從另一方面來說」和「哼!(不屑的嘆氣)」。我會專心聽他說話,甚至為了他而重寫一章。可是到頭來,我還是要用自己的方法來說故事。這位專家當然不是百分之百滿意我的處事方法。但我還是希望他可以從書裡發現一些新鮮事,或是給已經熟悉的觀念發現嶄新的詮釋;可能的話,也剌激他產生新的看法。
如果這樣的期許還是太高,那我希望至少他們無聊時可以翻翻。
我心中的第三種讀者是學生,那些正從外行人邁向專家的人。如果他還沒決定將成為哪一行的專家,我想鼓勵他們考慮進到我的本行——動物學。念動物學除了「有用」和動物很可愛以外,還有一個比較好的理由。這個理由是:到目前為止,動物是最複雜且設計得最完美的機器。如果你同意我的理由,那就很難理解,為什麼大家都跑去念其他的科系?對那些已經投入動物學的學生,我希望這書對他有一些學習價值。但是他一定得再去研讀我所參考的原始文獻和工具書。
如果覺得原始資料難以消化,或許我那些非數學的解釋有點幫助;也就是說,你大可以把本書看作前言或注腳。
我寫這本書的時候,只考慮到這三種讀者,當然是不夠的。我只能說,雖然我一直擔心這件事,但這些擔心比起我為本書所花的心血,顯然是不成比例的。
■誌謝
我是個動物行為學家,而本書是關於動物行為的。我虧欠在動物行為學所受的傳統訓練是很明顯的。特別是虧欠丁伯根(Niko Tinbergen, 1907-1988,一九七三年諾貝爾生理醫學獎得主),我在他的牛津研究室工作了十二年,受他影響很深,可惜他一直不知道這件事。雖然「求生的機器」一詞不全是他創的,但也差不多是了。
人類學近來深受其他非傳統人類學的新觀念所衝擊。本書大部分的立論也都是基於這些新觀念。在適當的各章內,對這些新觀念的創作人,我都予以致謝,他們主要是威廉斯(G. C. Williams, 1926- ,美國演化學家)、梅納史密斯(J. Maynard Smith, 1920-2004,英國演化學家)、漢彌敦(W. D. Hamilton, 1936-2000,英國理論生物學家)和崔弗斯(R. L. Trivers,美國社學生物學家)。
我非常感謝不少同僚為本書命名。我將這些名字當做英文版中各章的標題:克利伯斯(John Krebs)的「Immortal Coils」;莫里斯(Desmond Morris)的「The Gene Machine」;柯拉頓布羅克(Tim Clutton-Brock)和津恩‧道金斯(Jean Dawkins)的「Genesmanship」。很抱歉,帕特(Steve Potter)的沒上榜。
雖然我希望讀者都能對本書讚不絕口,而且愛不釋手,但我寧愛那些給本書實在批評的讀者。到完稿前,我不斷地修改底稿,而瑪麗安‧道金斯(Marian Dawkins)也跟著不停地一再謄稿。她不只是在生物學文獻和理論問題上有深厚的涵養,也一直給我無限的鼓勵和心靈上的支持。這都是我在撰稿過程中最重要的依靠。
克利伯斯也讀了本書的原稿,他比我更知道我要寫的主題,也一直傾囊相授他的知識。湯姆生(Glenys Thomson)和包德摩(Walter Bodmer)在遺傳學的題材上,給了我不少中肯的意見。恐怕他們尚不滿意我所修正的,但希望他們認為我已經有相當的改進。我非常感謝他們所花的時間和耐心。此外,約翰‧道金斯(John Dawkins)正確地指出可能造成誤導的措辭,而且還建議我如何改寫。我稱史丹伯(Maxwell Stamp)「聰明的外行人」,是再恰當不過的。他指出我初稿中很重大的瑕疵,使得完稿得以改善。
其他在各章節給我建設性的批評或專業建議的人有:梅納史密斯、莫里斯、麥舍(Tom Masher)、瓊斯(Nick Blurton Jones)、凱陶威爾(Sarah Kettlewell)、韓佛瑞(Nick Humphrey)、柯拉頓布羅克、強生(Louise Johnson)、格拉漢(Christopher Graham)、帕克(Geoff Parker)和崔弗斯。至於希羅(Pat Searle)和維霍宜文(Stephanie Verhoeven)打字熟練而且敬業樂群,也予我相當的鼓舞。
最後我想感謝牛津出版社的羅傑斯(Micheal Rodgers),他不只給原稿善意的批評,而且在出版本書的過程完全投入,使得本書可以順利出版。
再版序
新思想在燃燒
《自私的基因》一書出版十二年來,主旨已成為教科書的正統思想。
過程是十分弔詭的,不太簡單;書剛出版時並不被評為革命性的書,後來卻贏得完全相反的看法,再到現在成為正統的思想。讓我們不禁要問,這究竟怎麼一回事?
相當出乎意料之外的是,一開始書評都對本書很滿意,而且也不將它當作具爭議性的書。經過幾年卻漸漸生出爭議,竟被廣泛認為是部偏激的異端主義作品。但是,當本書被稱為異端主義的「美譽」逐漸升高後,幾年下來,「內容」似乎又不再令人覺得那麼極端,而愈來愈為人所接受。
■看待達爾文理論的新方法
「自私的基因」理論是達爾文的理論,雖然他不曾從這觀點來表達,但我想他應該會贊同我的觀點。實際上,這是正統的新達爾文主義(neo-Darwinism)的邏輯延伸,而以某種新形象來表達。它從基因的眼光來看本性,而不著眼於個體。它是從不同的角度來看,而不是另一個不同的理論。在《延伸的表現型》(The Extended Phenotype)一書的前幾頁開場白,我曾用奈克方塊(Necker cube)的隱喻來解釋。奈克方塊是在書面上是個平面的圖形,但讓人感覺像是個透明的立體方塊。
當你注視它幾秒鐘,它會換成另一個不同的方向面對著你(你會看到方塊的頂面)。再繼續注視得久些,它又會轉回原來的方塊(你看到方塊的底面)。兩種方塊與我們視網膜上的線條訊息都是相吻合的,所以我們的大腦也很樂意輪替這兩種方塊的影像,兩者並沒有不同。
我的重點是,看天擇有兩種方式,從基因的角度或是從個體的角度。如果了解得很恰當,那它們是相等的——也就是對相同真理的兩種觀點。你可以從一種角度跳到另一種,但仍然是相同的新達爾文主義。
現在我認為這樣的比喻太謹慎了。科學家最大的貢獻,與其說是提出新理論或揭開新事實,不如說是發現以新的方法看舊理論或事實。奈克方塊的模型是誤導的,因為它暗示兩種觀察的方式一樣好。更確切地說,那種比喻只對了一半,因為「角度」不像理論,無法以實驗來判斷;而無法以實驗來判斷,就表示無法利用我們熟悉的對錯標準去判斷。不過在最好的情況下,改變眼光可能可以達到比理論更高的境界。它可以推向全然的思考狀態中,許多令人興奮而且可試驗的理論因而產生了,且無法想像的事實也會揭露出來。但是奈克方塊的比喻完全缺乏這些;它只抓住視覺跳躍的概念,卻無法判斷價值何在。
我們所討論的並不是如何跳到相等的觀點,而是更極端的情況:讓整個形象都改變!
我不敢說,自己在這方面有何淺見。然而因為這樣,我更不想將科學和「科學普及」作明確的劃分。想要解釋那些僅出現在技術性文獻上的概念,是一門很難的藝術,它需要深入的語文技巧和啟發性的比喻。但如果你使力創新語言和比喻,最後肯定會有一番新看法。就如我剛才談過的,新穎的看法本身就是科學界原創性的貢獻。
愛因斯坦絕非通俗科學作家。但我常常猜想,他生動的比喻對他自己的思考,要比對我們這些人的幫助還要多——愛因斯坦為了能生動比喻而進行的思考,不也助燃了他創造的天分嗎?
■從基因的角度看演化
一九三○年代早期,費雪(R. A. Fisher, 1890-1962,英國族群遺傳學家、統計學家)和其他新達爾文主義的偉大前衛人士,就說明了達爾文主義基因角度的觀點;到了一九六○年代,漢彌敦和威廉斯又有更詳細的解說。他們的洞察力獨具眼光。但我覺得他們的解釋太簡明,勁力不足。
我相信,更深入而成熟的解釋,可以將生命的細節放在心中或腦中的正確方位。我一直想寫這樣一本從基因的眼光來看演化的書。書中會把例子集中在社會的行為,以糾正已經在不知不覺中,滲入達爾文主義的群體選擇主義(group-selectionism)。
機會來了,一九七二年因為英國工業抗爭導致停電,中斷了我的實驗研究,我便開始寫這本書。寫了僅僅兩章之後,不巧燈火管制結束,我的寫書計畫就擱在一邊;直到一九七五年,我有一年休假,才又拿起筆來。那時書中的理論也擴展了,特別是因為梅納史密斯和崔弗斯的貢獻。我現在才了解到,那時正是許多新觀念正在醞釀的神祕時期。我當時寫《自私的基因》就有些像得了一場興奮的高燒。
■創意獨具的新主題
牛津大學出版社找我出第二版時,他們堅持不需要革新,不需要擴大內容,不需要逐頁訂正。有些書在他們的觀念裡是需要相當修訂的,但《自私的基因》不是。不過我還是作了增補。
本書第一版在撰寫時,模仿了當代充滿朝氣的特質。那時國外正瀰漫著一陣改革的氣息,閃爍著詩人華茲華斯(William Wordsworth, 1770-1850)那充滿著愉悅的黎明。到了這第二版時,受時代的影響更深了。新發現的事實豐富了它的內容,複雜和謹慎則成了它身上的標記,而且仍實話實說。還有全新的章節,探討切中時機並具創意的主題,以帶動革命開端的新氣氛——這就是第十二和十三章。
我的靈感是在新舊兩版之間的幾年,受這領域的兩本書所啟發的:愛梭羅德(Robert Axelrod, 美國政治科學學家)所寫的《合作之演化》(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提供了我們對未來的某些期望;及拙作《延伸的表現型》,因為它填滿了我那幾年歲月,並且因為它可能是我寫過最好的一本書──而值得推薦給你。
「好人會出頭」(Nice guys finish first)這個標題是從「地平線」(Horizon)電視節目借用的。這節目是我在一九八五年英國廣播電台(BBC)推出的,是一部五十分鐘的紀錄影片,內容從賽局理論的方法探討合作演化。這部影片與另一部「盲眼鐘錶匠」(The Blind Watchmaker)都是同一位製片——泰勒(Jeremy Taylor),對他的專業,我致以崇高的敬意。從這個主題的處理已顯明,「地平線」的製作群已脫胎換骨成了高級學術專家,他們製作的一些節目在美國也可以看到,但常常多加了一個「新」(Nova)字。
第十二章所要感謝的,不僅是章名借自那部紀錄片,也要感謝泰勒和「地平線」的同仁們,讓我有與他們一起密切工作的經驗。
■誌謝
最近我聽到一件無法苟同的事情:一些有影響力的科學家喜歡將他們的名字,掛到自己壓根沒參與的作品中。很明顯的,有些資深的科學家要求在論文上掛名,而他們的貢獻只限於提供實驗室空間、研究經費,以及編校稿件。據我所知,這些人所有的科學聲望,可能都是學生和同仁的工作成果堆積出來的。
我不知道該怎麼阻止這樣不誠實的行為。或許學術期刊的編者應該拿到每一位作者的具名切結書,清楚說明他們的貢獻。這只是順便提到的。我在這裡提起這種事,是因為要做一個對比。柯若寧(Helena Cronin,英國哲學家,著有《螞蟻與孔雀》)替我很仔細地修正了每一行每一字,但她堅決拒絕在本書的新版本中掛名。我很感謝她,而且很抱歉的是,我的致謝謹此而已。
我也要感謝黎得利(Mark Ridley)、瑪麗安‧道金斯和格拉分(Alan Grafen)的忠告及對某些段落建設性的批評。並感謝牛津大學出版社的韋伯斯特(Thomas Webster)、麥格林(Hilary McGlynn)和其他同仁,對我的唐突及拖延的包涵。
我們都是機器人的化身!
讀這本書要像讀科幻小說,因為我寫的時候就是希望它充滿想像力。但是本書可不是科幻小說,而是實實在在的科學。雖然「真實的生活比小說的劇情更神奇」這句話聽起來有些陳腔爛調,但正好表達我對事實的感覺。
我們都是求生存的機器──機器人的化身,暗地裡已被輸入某些程式,用來保養這些叫做「基因」的自私分子!這是個如今仍然令我心驚膽寒的事實。雖然我己經知道這個事實多年,卻仍然未法完全接受它。我有個想法:拿這個真理來嚇嚇別人,或許可以得逞。
■像神祕故事一樣引人入勝
我在寫這書時,希望有三種讀者來探班,現在我將本書獻給他們。
首先是一般的讀者,也就是外行人。為了易讀,我幾乎完全避免了深奧難懂的術語,而多用自己定義的特殊字眼來表達我的觀念。在此順便提一下,為什麼我們不把所有期刊中大部分的專業術語都簡化呢?雖然我假設外行人沒有專業知識,但我可沒假設他們都是傻瓜。如果有心的話,任何人都可以把科學普及化。我已盡力嘗試在不失精髓的情況下,用非數學的言語闡釋一些細膩又複雜的觀念。我不知道在這方面是否成功,也不知道能否達成另一野心:嘗試讓讀者覺得看這本書看到欲罷不能,而且是個很好的消遣。
我一直感覺,生物學應該可以像神祕的故事一樣引人入勝。因為神祕的故事正如生物學一樣包羅廣泛。我很惶恐地希望,我能充分表達本書主題的剌激性。
我第二個假想的讀者是專家。他對我某些解說的比喻和數字,竟然批評得喘不過氣來。他最喜歡的措辭是「除了……」、「但從另一方面來說」和「哼!(不屑的嘆氣)」。我會專心聽他說話,甚至為了他而重寫一章。可是到頭來,我還是要用自己的方法來說故事。這位專家當然不是百分之百滿意我的處事方法。但我還是希望他可以從書裡發現一些新鮮事,或是給已經熟悉的觀念發現嶄新的詮釋;可能的話,也剌激他產生新的看法。
如果這樣的期許還是太高,那我希望至少他們無聊時可以翻翻。
我心中的第三種讀者是學生,那些正從外行人邁向專家的人。如果他還沒決定將成為哪一行的專家,我想鼓勵他們考慮進到我的本行——動物學。念動物學除了「有用」和動物很可愛以外,還有一個比較好的理由。這個理由是:到目前為止,動物是最複雜且設計得最完美的機器。如果你同意我的理由,那就很難理解,為什麼大家都跑去念其他的科系?對那些已經投入動物學的學生,我希望這書對他有一些學習價值。但是他一定得再去研讀我所參考的原始文獻和工具書。
如果覺得原始資料難以消化,或許我那些非數學的解釋有點幫助;也就是說,你大可以把本書看作前言或注腳。
我寫這本書的時候,只考慮到這三種讀者,當然是不夠的。我只能說,雖然我一直擔心這件事,但這些擔心比起我為本書所花的心血,顯然是不成比例的。
■誌謝
我是個動物行為學家,而本書是關於動物行為的。我虧欠在動物行為學所受的傳統訓練是很明顯的。特別是虧欠丁伯根(Niko Tinbergen, 1907-1988,一九七三年諾貝爾生理醫學獎得主),我在他的牛津研究室工作了十二年,受他影響很深,可惜他一直不知道這件事。雖然「求生的機器」一詞不全是他創的,但也差不多是了。
人類學近來深受其他非傳統人類學的新觀念所衝擊。本書大部分的立論也都是基於這些新觀念。在適當的各章內,對這些新觀念的創作人,我都予以致謝,他們主要是威廉斯(G. C. Williams, 1926- ,美國演化學家)、梅納史密斯(J. Maynard Smith, 1920-2004,英國演化學家)、漢彌敦(W. D. Hamilton, 1936-2000,英國理論生物學家)和崔弗斯(R. L. Trivers,美國社學生物學家)。
我非常感謝不少同僚為本書命名。我將這些名字當做英文版中各章的標題:克利伯斯(John Krebs)的「Immortal Coils」;莫里斯(Desmond Morris)的「The Gene Machine」;柯拉頓布羅克(Tim Clutton-Brock)和津恩‧道金斯(Jean Dawkins)的「Genesmanship」。很抱歉,帕特(Steve Potter)的沒上榜。
雖然我希望讀者都能對本書讚不絕口,而且愛不釋手,但我寧愛那些給本書實在批評的讀者。到完稿前,我不斷地修改底稿,而瑪麗安‧道金斯(Marian Dawkins)也跟著不停地一再謄稿。她不只是在生物學文獻和理論問題上有深厚的涵養,也一直給我無限的鼓勵和心靈上的支持。這都是我在撰稿過程中最重要的依靠。
克利伯斯也讀了本書的原稿,他比我更知道我要寫的主題,也一直傾囊相授他的知識。湯姆生(Glenys Thomson)和包德摩(Walter Bodmer)在遺傳學的題材上,給了我不少中肯的意見。恐怕他們尚不滿意我所修正的,但希望他們認為我已經有相當的改進。我非常感謝他們所花的時間和耐心。此外,約翰‧道金斯(John Dawkins)正確地指出可能造成誤導的措辭,而且還建議我如何改寫。我稱史丹伯(Maxwell Stamp)「聰明的外行人」,是再恰當不過的。他指出我初稿中很重大的瑕疵,使得完稿得以改善。
其他在各章節給我建設性的批評或專業建議的人有:梅納史密斯、莫里斯、麥舍(Tom Masher)、瓊斯(Nick Blurton Jones)、凱陶威爾(Sarah Kettlewell)、韓佛瑞(Nick Humphrey)、柯拉頓布羅克、強生(Louise Johnson)、格拉漢(Christopher Graham)、帕克(Geoff Parker)和崔弗斯。至於希羅(Pat Searle)和維霍宜文(Stephanie Verhoeven)打字熟練而且敬業樂群,也予我相當的鼓舞。
最後我想感謝牛津出版社的羅傑斯(Micheal Rodgers),他不只給原稿善意的批評,而且在出版本書的過程完全投入,使得本書可以順利出版。
道金斯
一九七六年
一九七六年
再版序
新思想在燃燒
《自私的基因》一書出版十二年來,主旨已成為教科書的正統思想。
過程是十分弔詭的,不太簡單;書剛出版時並不被評為革命性的書,後來卻贏得完全相反的看法,再到現在成為正統的思想。讓我們不禁要問,這究竟怎麼一回事?
相當出乎意料之外的是,一開始書評都對本書很滿意,而且也不將它當作具爭議性的書。經過幾年卻漸漸生出爭議,竟被廣泛認為是部偏激的異端主義作品。但是,當本書被稱為異端主義的「美譽」逐漸升高後,幾年下來,「內容」似乎又不再令人覺得那麼極端,而愈來愈為人所接受。
■看待達爾文理論的新方法
「自私的基因」理論是達爾文的理論,雖然他不曾從這觀點來表達,但我想他應該會贊同我的觀點。實際上,這是正統的新達爾文主義(neo-Darwinism)的邏輯延伸,而以某種新形象來表達。它從基因的眼光來看本性,而不著眼於個體。它是從不同的角度來看,而不是另一個不同的理論。在《延伸的表現型》(The Extended Phenotype)一書的前幾頁開場白,我曾用奈克方塊(Necker cube)的隱喻來解釋。奈克方塊是在書面上是個平面的圖形,但讓人感覺像是個透明的立體方塊。
當你注視它幾秒鐘,它會換成另一個不同的方向面對著你(你會看到方塊的頂面)。再繼續注視得久些,它又會轉回原來的方塊(你看到方塊的底面)。兩種方塊與我們視網膜上的線條訊息都是相吻合的,所以我們的大腦也很樂意輪替這兩種方塊的影像,兩者並沒有不同。
我的重點是,看天擇有兩種方式,從基因的角度或是從個體的角度。如果了解得很恰當,那它們是相等的——也就是對相同真理的兩種觀點。你可以從一種角度跳到另一種,但仍然是相同的新達爾文主義。
現在我認為這樣的比喻太謹慎了。科學家最大的貢獻,與其說是提出新理論或揭開新事實,不如說是發現以新的方法看舊理論或事實。奈克方塊的模型是誤導的,因為它暗示兩種觀察的方式一樣好。更確切地說,那種比喻只對了一半,因為「角度」不像理論,無法以實驗來判斷;而無法以實驗來判斷,就表示無法利用我們熟悉的對錯標準去判斷。不過在最好的情況下,改變眼光可能可以達到比理論更高的境界。它可以推向全然的思考狀態中,許多令人興奮而且可試驗的理論因而產生了,且無法想像的事實也會揭露出來。但是奈克方塊的比喻完全缺乏這些;它只抓住視覺跳躍的概念,卻無法判斷價值何在。
我們所討論的並不是如何跳到相等的觀點,而是更極端的情況:讓整個形象都改變!
我不敢說,自己在這方面有何淺見。然而因為這樣,我更不想將科學和「科學普及」作明確的劃分。想要解釋那些僅出現在技術性文獻上的概念,是一門很難的藝術,它需要深入的語文技巧和啟發性的比喻。但如果你使力創新語言和比喻,最後肯定會有一番新看法。就如我剛才談過的,新穎的看法本身就是科學界原創性的貢獻。
愛因斯坦絕非通俗科學作家。但我常常猜想,他生動的比喻對他自己的思考,要比對我們這些人的幫助還要多——愛因斯坦為了能生動比喻而進行的思考,不也助燃了他創造的天分嗎?
■從基因的角度看演化
一九三○年代早期,費雪(R. A. Fisher, 1890-1962,英國族群遺傳學家、統計學家)和其他新達爾文主義的偉大前衛人士,就說明了達爾文主義基因角度的觀點;到了一九六○年代,漢彌敦和威廉斯又有更詳細的解說。他們的洞察力獨具眼光。但我覺得他們的解釋太簡明,勁力不足。
我相信,更深入而成熟的解釋,可以將生命的細節放在心中或腦中的正確方位。我一直想寫這樣一本從基因的眼光來看演化的書。書中會把例子集中在社會的行為,以糾正已經在不知不覺中,滲入達爾文主義的群體選擇主義(group-selectionism)。
機會來了,一九七二年因為英國工業抗爭導致停電,中斷了我的實驗研究,我便開始寫這本書。寫了僅僅兩章之後,不巧燈火管制結束,我的寫書計畫就擱在一邊;直到一九七五年,我有一年休假,才又拿起筆來。那時書中的理論也擴展了,特別是因為梅納史密斯和崔弗斯的貢獻。我現在才了解到,那時正是許多新觀念正在醞釀的神祕時期。我當時寫《自私的基因》就有些像得了一場興奮的高燒。
■創意獨具的新主題
牛津大學出版社找我出第二版時,他們堅持不需要革新,不需要擴大內容,不需要逐頁訂正。有些書在他們的觀念裡是需要相當修訂的,但《自私的基因》不是。不過我還是作了增補。
本書第一版在撰寫時,模仿了當代充滿朝氣的特質。那時國外正瀰漫著一陣改革的氣息,閃爍著詩人華茲華斯(William Wordsworth, 1770-1850)那充滿著愉悅的黎明。到了這第二版時,受時代的影響更深了。新發現的事實豐富了它的內容,複雜和謹慎則成了它身上的標記,而且仍實話實說。還有全新的章節,探討切中時機並具創意的主題,以帶動革命開端的新氣氛——這就是第十二和十三章。
我的靈感是在新舊兩版之間的幾年,受這領域的兩本書所啟發的:愛梭羅德(Robert Axelrod, 美國政治科學學家)所寫的《合作之演化》(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提供了我們對未來的某些期望;及拙作《延伸的表現型》,因為它填滿了我那幾年歲月,並且因為它可能是我寫過最好的一本書──而值得推薦給你。
「好人會出頭」(Nice guys finish first)這個標題是從「地平線」(Horizon)電視節目借用的。這節目是我在一九八五年英國廣播電台(BBC)推出的,是一部五十分鐘的紀錄影片,內容從賽局理論的方法探討合作演化。這部影片與另一部「盲眼鐘錶匠」(The Blind Watchmaker)都是同一位製片——泰勒(Jeremy Taylor),對他的專業,我致以崇高的敬意。從這個主題的處理已顯明,「地平線」的製作群已脫胎換骨成了高級學術專家,他們製作的一些節目在美國也可以看到,但常常多加了一個「新」(Nova)字。
第十二章所要感謝的,不僅是章名借自那部紀錄片,也要感謝泰勒和「地平線」的同仁們,讓我有與他們一起密切工作的經驗。
■誌謝
最近我聽到一件無法苟同的事情:一些有影響力的科學家喜歡將他們的名字,掛到自己壓根沒參與的作品中。很明顯的,有些資深的科學家要求在論文上掛名,而他們的貢獻只限於提供實驗室空間、研究經費,以及編校稿件。據我所知,這些人所有的科學聲望,可能都是學生和同仁的工作成果堆積出來的。
我不知道該怎麼阻止這樣不誠實的行為。或許學術期刊的編者應該拿到每一位作者的具名切結書,清楚說明他們的貢獻。這只是順便提到的。我在這裡提起這種事,是因為要做一個對比。柯若寧(Helena Cronin,英國哲學家,著有《螞蟻與孔雀》)替我很仔細地修正了每一行每一字,但她堅決拒絕在本書的新版本中掛名。我很感謝她,而且很抱歉的是,我的致謝謹此而已。
我也要感謝黎得利(Mark Ridley)、瑪麗安‧道金斯和格拉分(Alan Grafen)的忠告及對某些段落建設性的批評。並感謝牛津大學出版社的韋伯斯特(Thomas Webster)、麥格林(Hilary McGlynn)和其他同仁,對我的唐突及拖延的包涵。
道金斯
一九八九年
一九八九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