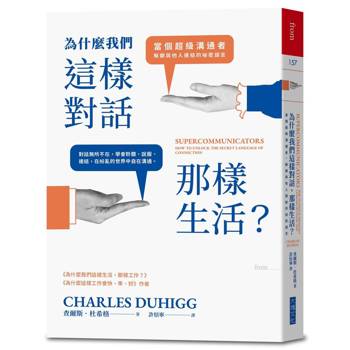虛無主義的危機
哲學,是對人生經驗作全面的反省。人有理性,總希望能夠明白人生究竟是怎麼回事,尤其是在亂世裡。周公制禮作樂之後,時代演變愈來愈快,到了春秋時代末期,可以用四個字來描寫:周文疲敝。「禮壞樂崩」一語就足以說明周朝原來的構想失效了。一方面是天子失德,既無仁愛也無正義,百姓生活陷入困境;另一方面,社會開始急遽演變,有學問有專長的人流落到民間。春秋時代百家爭鳴,其中最重要的是儒家與道家兩派。儒家重視學習與修養,而道家老子所發展出來的思想卻另有特色。
周文疲敝:文化失去活力
老子是哲學家,是道家的創始者。司馬遷《史記‧老子韓非列傳》記載老子是楚國人,在周朝負責管理國家檔案,他退休後騎青牛西出函谷關,遇到關尹(守關的官員),他聽說老子很有學問,想請他留下一些智慧資產,所以老子在短期內寫了五千多字。這是傳說,要在短期內寫出《老子》五千言,可能性不大,應該是由一群隱居的人長期生活留下的心得。據說後來關尹隨老聃一起隱居去了。《莊子‧天下》有一段說:關尹、老聃都嚮往「道」。過去談「道」,通常會配合「天之道」或「人之道」。但是,做為道家的老子,他談的是「道」的本身,並發揮成一套完整的系統。
老子出關之後不知所終,重要的是他留下了《老子》。這本書又稱《道德經》,共八十一章,一到三十七章稱為〈道經〉,因為第一章開頭是「道可道,非常道」;三十八到八十一章稱為〈德經〉,因為第三十八章開頭是「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道與德合在一起,稱為《道德經》,所說的和仁愛、慈悲、忠孝毫無關係。道,用一句話來說,就是「究竟真實」。如果用兩個字來形容,儒家是「真誠」,道家則是「真實」。真誠只對人有效,而真實對萬物都有效,因為宇宙萬物都有其真實的一面。而虛偽的出現,是因為人的認知與行動,常常帶來複雜的情況。「道」要回應的是:宇宙萬物充滿變化,背後有沒有不變的本體呢?「德」是指獲得的「得」,「德」與「得」在古代音意相通,與倫理道德無關;萬物獲得道所賦予的部分稱作德。道與萬物之間就靠「德」在連繫及運作,而「德」又不能離開萬物,所以說「德」是道在萬物裡的代表。譬如,一朵花,因獲得道的支持,才能存在。萬物獲得道的部分,稱作它們的本性與稟賦。唯一有問題的是人,人同樣獲得道的加持,不過人製造很多複雜的情況,是道所無法規定的,這就牽涉到比較深刻的問題。
哲學家面對時代危機,要思考如何讓人繼續活下去。要活下去,有兩個基本要求,仁愛與正義。仁愛就是發展經濟,讓人足食足衣,可以養家活口、傳宗接代,一代代發展下去。但要維持正義比較困難。人有自由,有人行善,有人作惡,所以需要賞善罰惡,如果沒有正義,任人胡作非為、巧取豪奪,社會就會混亂。儒家強調仁愛與正義,要具體落實在人的生活中。而道家則認為仁愛和正義必須推到最根源,從根本上化解這個問題。因此二家各有不同的取捨。
回到周文疲敝。文化為什麼會慢慢疲累毀壞呢?現在很多人談國學,也有人疑惑為什麼要談這些老東西?文化分為三個層次:器物、制度、理念。器物最為具體,展現為經濟繁榮發展,每個人都有方便豐富的器物以節省時間和力氣;制度層次有法律與規範,能讓社會秩序維持穩定;理念層次則無形無象,我們講國學的目的,談的就是理念。如果有人學了老子之後,希望仿效其中的器物與制度層次,就只能說是「小國寡民」。老子在八十章提到「小國寡民」,人們老死不相往來,彼此不會比較,也沒有紛爭,因為比較是痛苦的來源之一。柏拉圖也提出理想國的概念,他的國家只有五千零四十人,他認為只有這種小型國家,才能穩定和諧。
《莊子‧天地》有個故事,子貢看到一個老人家辛苦地抱著甕去裝水,於是好心建議他用桔槔(汲水的器具)。沒想到老人家生氣了,他說:「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意思是,人使用機械之後,就會思考怎麼樣最便利,發展到最後,世界會變得非常複雜,所以老子主張回到原始狀態。但今天可能沒有人想再回到原始的生活。
我們要學習老子的理念:什麼樣的人生是合理的,什麼樣的觀念是正確的。我年輕時讀到「強行者有志」(《老子‧第三十三章》),亦即勉強自己往前走就是有志向;有志向才會要求自己。這使我對人生有了不同的看法。後來念到「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老子‧第四十四章》),意思是過分愛惜必定造成極大的耗費;儲存豐富必定招致慘重的損失。因為誰也無法預料天災人禍。舉例來說,一個人很喜歡蒐集酒杯,家裡有個酒櫃,擺滿了酒杯,後來地震時酒櫃倒下來,酒杯全部碎光了,他也從此不再看酒杯了。
虛無主義:價值上與存在上
老子有很多語句可以當座右銘,但我們希望能理解老子完整的思想。老子和儒家有什麼不同?這得從分辨古代的兩種虛無主義開始。「虛無主義」一詞參考了西方的背景,但可以普遍應用,中國古代出現了價值上和存在上的虛無主義。
儒家關心價值上的虛無主義,這種虛無主義認為沒有真假、善惡、是非、美醜。人發現善惡沒有報應,在失望之餘,自然會懷疑行善避惡的必要性。至於美與醜,看多了後會發現那也是相對的。這時只有求助於宗教,但所有的宗教都建立在善惡有報應的基礎上,這樣宗教才有可能發展。若今生沒有報應,來世也沒有報應,那麼還有誰要信仰宗教呢?如果人生在世只要設法避開災難就好,那只是消極無奈地活著。所以,如果在價值上出現虛無主義的困境,一般百姓將會無所措其手足,因為不知道自己的言行何時會惹禍上身,既沒有善惡之分,也沒有正義可言,這就是典型的亂世。儒家對此深感憂心而苦思對策。孔子與孟子想盡辦法教導世人:只要真誠就會產生由內而發的力量,促使人行善避惡,然後快樂也將由內而發。快樂本身就是最好的報應,是行善的善報。
孔子責怪原壤:「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為賊。」(《論語‧憲問》)他批評這個老朋友年輕時既不謙虛也不友愛,年長後更沒有好的行為可讓人稱讚,這種人如果活得長久而不死,就可以稱之為賊。此處的「賊」不是指小偷,是指傷害做人的原則。一般人都認為好人應該長壽。我們過年時喜歡說五福臨門,《尚書‧洪範》所說的五福是:一,壽;二,富;三,康寧,健康平安;四,攸好德,所愛好的是德行;五,考終命,可以活得很老,安享天年。但是如果長壽卻一直受苦,誰願意呢?這套說法有很廣的適用性,對外國人來說也可以成立。但是對儒家來說,問心無愧,才是最快樂的。這種快樂最可貴,也最可靠。如果肯定賺錢快樂,那麼賠錢呢?從外而來的,將在外面失去,只有由內而發的才是我們可以掌握的,這是儒家最重要的觀點。
道家比儒家看得更深刻。儒家關懷人群,道家則認為不必考慮太多有關人群的問題。道家關心存在上的虛無主義。這種虛無主義和生死有關,譬如《老子‧七十五章》說:「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夫唯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每一個人都希望活下去,為什麼有些人輕易就死掉呢?是因為在上位者稅收太重,只顧自己吃喝玩樂,不顧百姓的生活,所以這涉及生死問題。不過《老子‧七十四章》還有一句:「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意思是千苦艱難唯一死,若連死都不怕,還有誰可以嚇你?這說明了當時的情況,非自然的死亡是普遍的現象,很多人認為活著同死去沒什麼差別,死後一了百了。這就是存在上的虛無主義。
吳稚暉是一位科學家,也是第一屆中研院院士。他是一位無神論者,也承認自己是虛無主義者。所謂無神論者,代表他認定死後沒有靈魂,也沒有鬼神,更不用談上帝。這種想法落實在生活裡,一個人該如何生存呢?怎麼跟別人來往呢?我尊敬吳先生,因為他很誠實,他說:「我是無神論者,所以人生只有四個字,『一片漆黑』。死後埋進墳墓不是一片漆黑嗎?」這種想法很消極。後來有人問他:「你是學者,應該講一些比較積極的話吧。」他說:「人生只有三件事,第一,吃飯;第二,生孩子;第三,交朋友。」吃飯和生孩子,屬於動物性的食色性也,是可以理解的。吳先生認為,人的世界比較複雜,所以要同各種朋友來往,人也可以透過交友得到一些快樂。這樣的想法就是存在上的虛無主義,其實這種想法相當普遍。現在由於訊息流通,在發生天災人禍時,不免想到自己也可能碰上同樣的狀況。這樣的事情想多了以後,會發現生命只是一種偶然性:如果得意,是偶然得意;如果失意,也是偶然失意。人生就是佛教所說的「無常」,沒有任何事情是穩定可靠的,也沒有任何保障。在這種情況之下,危機顯然非常深重。
老子比孔子年長約三十歲。孔子去拜訪老子,老子規勸他不要太想有所作為,總想改善社會,讓人們快樂活下去。在孔子看來,若肯定這個世界的價值,就要設法做官,設法發展經濟,好好照顧百姓。有個守城門的人說孔子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也」,這句話顯示了儒家的精神。儒家有一種悲壯的豪傑情操,看到天下大亂依然想努力改善,即使沒有把握成功。這是為了要回應內心的要求。道家同樣希望人們過得快樂,但他們認為儒家這樣做固然用心良苦,但耗盡一生力氣卻未必能夠成功。因此,孔子回到家鄉之後對學生說,我終於看到龍了。由此可見孔子推崇老子的高明智慧。
性格決定了命運的發展,但老子絕不只是性格特殊而已,他還有很深刻的智慧,看得比儒家更遠。儒家看到人類的問題,而老子看到存在的問題,亦即不只人類,還有整個自然界。能掌握住這兩個層次,老子的思想當然更為周全。西方學者特別喜歡研究老子的思想,他們認為老子有形上學,而儒家只有倫理學。倫理學講的是人活在世界上要行善避惡,所以要先界定什麼是善,什麼是惡,然後去做該做的事。形上學超越善惡,只講宇宙萬物有沒有本體,有沒有最後真實的存在,如果沒有,這形上學就變成虛無了;如果有,則形上學可以建立。老子面對的是存在上的虛無主義,這才是究竟意義的虛無主義。
西方學者特別欣賞道家,主要原因是他們知道人的言語有其限制。老子說「道可道,非常道」(《老子‧第一章》),接著是「名可名,非常名」。意思是:道,如果可以用言語表述,就不是永恆的道;名,如果可以用名稱界定,就不是恆久的名。取名字很重要,因為人靠名字認定自己的存在。有一隻動物跑過去,你卻喊不出名字,這樣等於什麼都沒見到。魏晉時代的阮修與人談論有無鬼神的問題。有人認為人死之後會變成鬼,但阮修主張鬼不存在。他說:「自稱看到鬼的人說,鬼穿著生前所穿的衣服。如果人死變成鬼,那麼衣服也有鬼嗎?」衣服是物質,鬼如果穿著白袍出現,那麼鬼不見時白袍應該留下來,但白袍也不見了,白袍也有鬼嗎?這就說明名稱的重要。有些民俗觀念也相當深刻,譬如人死了要喊他的名,把他的魂喚回來。名字代表個人,人會變,名字不會變,當然現在可以改名,那是別的問題了。名對人的概念思考能力來說,是不可或缺的,一物沒有名字,對人而言等於不存在。
名字是約定俗成的,為什麼可以扮演這麼重要的角色呢?這就是人類思維的特色。老子顧及這些觀念,西方學者當然佩服。他們只要看到:「可以用言語表述的,就不是永恆的道。」這句話就夠了。他們認為存在本身(Being)是無法形容的。他們常提到上帝,但是無法正面形容上帝,而只能用否定的方式來形容絕對完美的神。譬如:上帝不是太陽,上帝不是月亮,上帝不是海洋。這樣講都正確,因為上帝確實不是太陽、月亮、海洋,但卻也等於什麼都沒說。老子說:「道可道,非常道」,西方學者一看就懂,看不懂的人只覺得「玄之又玄,眾妙之門」。老子在西元前六世紀時就有這種思想,西方學者直到一七八八年才將《老子》翻譯成拉丁文,但「道」字很難翻譯,只能音譯,外國人實在看不懂。有人把「道」譯成「路」,那麼這個路就不是普通的路。所以西方學者始終覺得老子的思想神祕莫測。
老子的思想可以區分為兩個部分:第一,專門屬於形上學的部分;第二,落實在生活應用上的部分。司馬遷《史記》裡記載老子事蹟的篇章稱為〈老子韓非列傳〉,這實在是委屈了老子。韓非是法家代表,如何與老子扯在一起?法家利用道家的形上學,而在《韓非子》有〈解老〉、〈喻老〉兩篇,代表韓非認真研究過老子的思想,結果司馬遷就上當了。
西方學者研究古代中國哲學,得到三點結論:第一,老子具有革命性;第二,墨子最保守;第三,孔子的思想承先啟後,所以顯得最溫和。老子的思想是用「道」代替「天」。古代君王稱為天子,只有天子才有天命。孔子最大的創見就是主張每個人都有天命,如他說自己「五十而知天命」,但古代這樣講天命等於要造反了。從孔子以後,天命是每個人都可以理解的,都可以在自己身上加以肯定的。現在,老子用「道」代替「天」,所以西方學者認為老子的思想具有革命性。
一般人只以為道家主張順其自然、清淨、無為、不爭,老子怎麼會與「革命」相關呢?另外,而墨子講天志,明鬼,他主張做壞事鬼就會懲罰你。這是哄小孩的,很多壞人比鬼還兇。墨子還提倡兼相愛,交相利,因為大家都是上天的子女,上天的意志希望人類像兄弟姊妹一樣相親相愛。這是很好的理想,但恐怕難以實現。所以,墨家信徒摩頂放踵,到處幫助別人,甚至犧牲自己成全別人,最終變成游俠、刺客之類的人,這也是《史記‧刺客列傳》的由來。繼續演變下去,則成為武俠小說裡的人物,那些大俠的表現都像墨子和他的信徒,以天下為家,但觀念卻是最保守的,想要賞善罰惡,無法突破與創新。
摘自《傅佩榮‧經典講座──老子:在虛靜中覺悟人生智慧》第一講
| FindBook |
有 8 項符合
傅佩榮.經典講座──老子:在虛靜中覺悟人生智慧的圖書 |
 |
傅佩榮‧經典講座 老子:在虛靜中覺悟人生智慧 作者:傅佩榮 出版社:天下文化 出版日期:2018-10-08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平裝 / 240頁 / 14.8 x 21 cm / 普通級/ 單色印刷 / 初版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245 |
中國/東方哲學 |
$ 277 |
哲學 |
$ 277 |
道家思想 |
$ 277 |
Social Sciences |
$ 298 |
文學小說 |
$ 298 |
文學小說 |
$ 308 |
中國哲學 |
$ 8690 |
社會人文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傅佩榮.經典講座──老子:在虛靜中覺悟人生智慧
老子是道家的創始者,建構了完整的道家體系。
他以「道」代替「天」,超越以「人」為中心的思考模式,具有革命性。
「道」是萬物的來源與歸宿,是「究竟真實」,主張從道來看萬物,
亦即將人生依託在永恆不變的基礎上,再由此觀照人間,安排適當的言行方式。
本書以淺顯易懂的文字,探究老子的政治願望與人生價值。
學習道家,讓我們成為自己生命的統治者,人生就能得到很大的轉機。
作者簡介:
傅佩榮
民國三十九年生,上海市人。美國耶魯大學哲學博士,曾任比利時魯汶大學、荷蘭萊頓大學講座教授,臺灣大學哲學系主任兼研究所所長,現任臺灣大學哲學系、所教授。傅佩榮教授的教學深受學生歡迎,曾獲頒教育部教學特優獎、大學生社團推薦最優通識課程、《民生報》評選校園熱門教授等獎項,另外在學術研究、寫作、演講等方面,都有卓越成就。作品深入淺出,擅長說理,曾獲國家文藝獎與中正文化獎。
著作甚豐,範圍涵蓋哲學研究與入門、人生哲理、心理勵志等。
著有《哲學與人生》、《轉進人生頂峰》、《活出自己的智慧》、《那一年我在萊頓》、《珍惜情緣》、《宇宙的舞者》、《向孔子學做人》等數十本。並重新解讀中國經典,著有《究竟真實─傅佩榮談老子》、《人性向善─傅佩榮談孟子》、《人能弘道─傅佩榮談論語》、《樂天知命─傅佩榮談易經》、《逍遙之樂─傅佩榮談莊子》、《止於至善─傅佩榮談大學.中庸》、《孔子:追求人的完美典範》、《孟子:浩然正氣與成功人生》、《老子:在虛靜中覺悟人生智慧》與《莊子:以自在之心開發無限潛能》、《易經入門與國學天空》、《國學與人生》、《人生,一個哲學習題》等書(以上皆由天下文化出版)。
章節試閱
虛無主義的危機
哲學,是對人生經驗作全面的反省。人有理性,總希望能夠明白人生究竟是怎麼回事,尤其是在亂世裡。周公制禮作樂之後,時代演變愈來愈快,到了春秋時代末期,可以用四個字來描寫:周文疲敝。「禮壞樂崩」一語就足以說明周朝原來的構想失效了。一方面是天子失德,既無仁愛也無正義,百姓生活陷入困境;另一方面,社會開始急遽演變,有學問有專長的人流落到民間。春秋時代百家爭鳴,其中最重要的是儒家與道家兩派。儒家重視學習與修養,而道家老子所發展出來的思想卻另有特色。
周文疲敝:文化失去活力
老子是哲學家,是道家的...
哲學,是對人生經驗作全面的反省。人有理性,總希望能夠明白人生究竟是怎麼回事,尤其是在亂世裡。周公制禮作樂之後,時代演變愈來愈快,到了春秋時代末期,可以用四個字來描寫:周文疲敝。「禮壞樂崩」一語就足以說明周朝原來的構想失效了。一方面是天子失德,既無仁愛也無正義,百姓生活陷入困境;另一方面,社會開始急遽演變,有學問有專長的人流落到民間。春秋時代百家爭鳴,其中最重要的是儒家與道家兩派。儒家重視學習與修養,而道家老子所發展出來的思想卻另有特色。
周文疲敝:文化失去活力
老子是哲學家,是道家的...
顯示全部內容
作者序
【自序】
「掩耳疾走,背他而去。」我好像也曾有過這樣的念頭,但針對的「他」是誰呢?不是別人,就是我在這兒要向大家介紹的「孔子、孟子、老子、莊子」。他們並稱為「中國四哲」,但我年輕時,只覺得他們難以親近,也不易理解。孔子說話精簡扼要,如念格言金句;孟子倡言仁政理想,結果落個好辯之名;老子看似很有見地,內容卻是恍惚難解;莊子寓言常有巧思,讓人感嘆浮生若夢。我曾想過,如果沒有這四哲,我們求學時會不會輕鬆一點?傳統的包袱會不會減少一點?
他們身處危機時代,虛無主義的威脅有如張牙舞爪的惡魔。孔子與孟子代表儒...
「掩耳疾走,背他而去。」我好像也曾有過這樣的念頭,但針對的「他」是誰呢?不是別人,就是我在這兒要向大家介紹的「孔子、孟子、老子、莊子」。他們並稱為「中國四哲」,但我年輕時,只覺得他們難以親近,也不易理解。孔子說話精簡扼要,如念格言金句;孟子倡言仁政理想,結果落個好辯之名;老子看似很有見地,內容卻是恍惚難解;莊子寓言常有巧思,讓人感嘆浮生若夢。我曾想過,如果沒有這四哲,我們求學時會不會輕鬆一點?傳統的包袱會不會減少一點?
他們身處危機時代,虛無主義的威脅有如張牙舞爪的惡魔。孔子與孟子代表儒...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自 序
主題一:面對天下大亂
第一講:虛無主義的危機
周文疲敝:文化失去活力
虛無主義:價值上與存在上
換個角度思考人生意義
第二講:與儒家的三點差異
不以「人」為中心的思考模式
以「道」代替「天」
以德報怨:包容一切
第三講:從認知提升到智慧
以知為區分
以知為避難
以知為啟明
主題二:道的深刻意義
第一講:道是什麼?
萬物的來源與歸宿
整體與永恆的觀點
悟道方法:虛與靜
第二講:道與德的配合
德是萬物「得」之於道者
德:本性與稟賦,人的問題?
自然:自己如此的狀態
第三講:從道來看萬物
一往平等的精神
平衡和諧的狀態...
主題一:面對天下大亂
第一講:虛無主義的危機
周文疲敝:文化失去活力
虛無主義:價值上與存在上
換個角度思考人生意義
第二講:與儒家的三點差異
不以「人」為中心的思考模式
以「道」代替「天」
以德報怨:包容一切
第三講:從認知提升到智慧
以知為區分
以知為避難
以知為啟明
主題二:道的深刻意義
第一講:道是什麼?
萬物的來源與歸宿
整體與永恆的觀點
悟道方法:虛與靜
第二講:道與德的配合
德是萬物「得」之於道者
德:本性與稟賦,人的問題?
自然:自己如此的狀態
第三講:從道來看萬物
一往平等的精神
平衡和諧的狀態...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