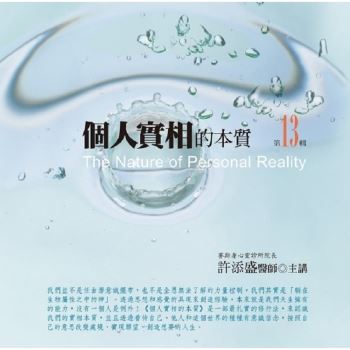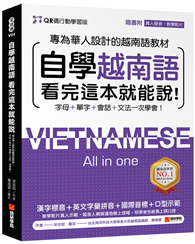第一章
清晨,褚雁翎輕手輕腳地下了床,莫岫媛本來還在睡,但她向來睡得很輕,睡眼迷蒙地看著他,問道:“妳要去上朝了?”
“嗯。”褚雁翎輕輕撫摸著她的臉頰,細心體貼地幫她把被子蓋好:“妳再睡會兒吧。我去看一下麟兒就走。”
“一早別去鬧他了。”莫岫媛拉住他,問道:“今天父皇會向朝臣們宣佈昨天答應妳的那些事情吧?”
“嗯,應該是的。”
“這一招,不知道能不能擋得住太子對妳的猜忌和群臣的悠悠眾口。”莫岫媛憂心地說:“父皇昨天說得對,妳這樣做,是有些像‘此地無銀三百兩’。昨天妳和裘千夜商量過了嗎?他也贊成妳突然從朝政中退出來?”
“以退為進他是贊同的。但是他也說越晨曦那邊肯定還有後招,不見得是我能退得下來的。朝中諸臣和我關係好的人有很多,今天父皇若是開口免我的職權,應該會有人站出來提出質疑。所以……”
莫岫媛明白了,她揉了揉眼:“所以以退為進是妳在父皇面前討好示弱的手段,其實,妳並沒有真的想交出職權。”
“當然。”褚雁翎的雙眸清亮:“我在朝中奮鬥了這麼多年,好不容易才有了些自己的根基,豈能輕易交出?我若交了,太子不是要得意死了?”他冷笑道:“縱然我沒有繼承江山的可能,也不會讓他太過耀武揚威。尤其是在父皇面前……”
莫岫媛伸著手臂,袖子褪落,露出一截藕臂,她摸著他的臉,笑道:“不怕,若是父皇真的就此卸了妳的職,也沒有朝臣幫妳說話,我們兩個人就正好過輕輕鬆松的不操閒心的日子。妳也能天天在家陪麟兒了。”
褚雁翎拉過她的手咬了一口,笑道:“妳倒想得開。一會兒別忘了去看看雁茴,她雖然上次哭跑了太子,但是每天都惦記著周襄,我又不能老去見她,惹人注意,也不能叫周襄再入宮來見她。昨天周襄給我帶了封信過來,我還沒得空交給她,妳給她送過去吧。”
莫岫媛驚喜道:“周襄來信了?妳倒也大膽,還敢為他們傳信。”
“不傳怎麼辦?總是我惹出的事,我要收拾這個爛攤子嘛。”他笑著在她額頭上留下一吻。起身梳洗,更衣,然後出殿去上早朝。
但是到達上朝前眾臣休息的廂房時,卻見這裡不同於以往的熱鬧,只有零零星星的幾個人。
褚雁翎一愣:“怎麼?今天諸位大人都病了嗎?”
刑部尚書郝文成忙起身行禮:“參見殿下,剛剛宮裡來傳話,說陛下今日不上朝,所以諸位大人都回去了。”
“不上朝?”褚雁翎訝異地問道:“說了什麼原因了嗎?”
“沒有……不過聽說太子昨夜在下匙後入宮,然後就一直沒有離開……”郝文成因為身負破昨日刺客案子之責,一直覺得重任在肩,惴惴不安。太子昨夜入宮未去的傳聞更令他擔心不已。
此時剛才負責傳話的太監並未離開,見到褚雁翎到來,那太監便上前道:“三殿下,陛下口諭,請三殿下現在去景仁殿問話。”
褚雁翎暗自一驚道:父皇沒有上早朝已經是非常不尋常的一件事了,如今叫太監來傳的話口氣又十分重:“去景仁殿問話”,顯然是有事要被質詢。昨天和父皇的一番對話不是都已經說清楚了嗎?為什麼父皇現在態度突然有了轉變?再聯想太子昨夜入宮……這原本是他和裘千夜事先預料到的事情,所以他才會提前到父皇面前說明情況,使出以退為進的一招。那時候的父皇是理解並支持他的。
那麼,太子究竟說了什麼,會讓父皇態度大變?
他一路思索,來到景仁殿門口,只見四周如昨夜一般清靜,但是殿門口卻站著兩排大約十幾人的內宮近侍。
內宮護衛向來是由他負責,但這些近侍在此地的出現顯然不是他的指令。是父皇?父皇為什麼要派這些人來?是要看住誰,還是要抓誰?
他猶豫著,那些侍衛並未上前攔他,而太監已經到殿門口通報:“陛下,三殿下來了。”
“叫他進來吧。”鴻蒙國主的聲音聽來很平靜,沒有任何波瀾,不知道後面又蘊含了怎樣的風暴。
他走進殿內,只見父皇坐在正中的龍書案後,太子褚雁德就在父皇的左手邊,而面對父皇七八步外的青石板上則跪著一個人,一身黑衣勁裝,全身被五花大綁著,腳上還被栓了鎖鏈。
褚雁翎的心中飛快地閃過一個念頭:莫非這人……
鴻蒙國主看著他,低聲開口:“雁翎,妳認識此人嗎?”
褚雁翎走到那人正前方看了一眼,答道:“兒臣不認識。”
褚雁德冷笑道:“但他可認得妳呢。”
鴻蒙國主看了一眼褚雁德:“雁德,妳先不要急著說話,我自會給妳問個清楚公道。”
褚雁德只好閉了嘴,但那眼神明顯都是張揚的得意。
鴻蒙國主直視著褚雁翎,說道:“此人是昨晚太子抓到的,從驛站行刺之後逃走的那名刺客。”
褚雁翎雖然已經猜出,但聽到確實的消息後還是很訝異,笑道:“那可真是太好了,兒臣正擔心這案子若是因為抓不到一個活口問供,豈不是要成了懸案?和皇兄及金碧使臣都無法交待了。”
“但是……他昨晚所供述的事情卻讓我很是震驚。”鴻蒙國主慢吞吞地說著,眼睛一瞬不眨地盯著褚雁翎:“他竟然說是妳指使了這次刺殺事件。”
褚雁翎轉過身,不是看向那刺客,而是看向太子褚雁德:“這人是大哥抓到的?”
“哼。”褚雁德斜睨著他:“沒想到我會這麼快就抓到人吧?”
“在哪兒抓到的?”
褚雁德揚起頭:“城東的一處小醫館,他受了傷跑去找大夫治傷,而刑部已經通知了各家醫館和客棧,遇到可疑人士必須上報。刑部尚書在宮裡問話,人就被帶到我這兒來了。”
“他沒反抗,就輕易被抓住了?”
褚雁翎的質疑讓褚雁德怒道:“怎麼?幾十名刑部捕快一起抓他一個刺客還能抓不住嗎?”
褚雁翎踱步到那人跟前,仔仔細細看了一遍,那人的手臂上有一處已經包紮的傷口。
“這胳膊是斷了嗎?需要跑到醫館去包紮?”他彎下腰查看,對那人說道:“若妳真是身負絕密任務,而任務又完成得一塌糊塗,就算是不自殺謝罪,又怎麼有膽子敢在京城內的醫館出沒?難道妳會想不到事敗之後會被全城搜捕嗎?”
褚雁德插話道:“三弟,妳現在這是威脅他,還是嚇唬他?氣他說破了妳的秘密,把妳供出來了?可惜妳現在說什麼都晚了!他已經認罪,現在是妳要給父皇一個交代的時候了!”
褚雁翎回頭笑道:“大哥莫急啊,我就是要給父皇一個交代。這個人是誰派來的我雖然不知道,但是我心裡明白此事與我無關,必然是有人刻意嫁禍栽贓給我。”他看著鴻蒙國主:“父皇要真相,這真相必須是乾乾淨淨的!”
鴻蒙國主凝視著他,慢聲道:“雁翎,妳知道父皇最不希望看到妳們手足相殘,如果妳能證明這一切是妳大哥的誤會的話,若是真有人有心栽贓陷害妳,父皇自然會給妳做主。”
“謝父皇。”褚雁翎跪地叩首,褚雁德急了,躍起身道:“父皇為什麼這麼願意輕信他……如今人證就在眼前……”
“我從不聽一面之詞。”鴻蒙國主揚聲道:“雁德,妳若肯沉住氣聽他說一說他的道理,也算是妳有未來人君之風範。”
父皇的一句呵斥,讓褚雁德不得不暫時咽下那口氣,往後退了一步,咬牙道:“好,就聽他怎麼圓謊!”
褚雁翎來到那刺客身前,說道:“他的衣服倒是與那幾名刺客相同,看布料,款式都出自一處。所以我相信這刺客與今晚那些人是同一撥的,不是被人臨時找來冒名頂替。”
褚雁德撇嘴道:“廢話!”
褚雁翎又說道:“看這人的傷勢,並沒有嚴重到非要立刻就醫的地步,學武之人,刀劍傷是時常會受的,誰手裡都得備點金瘡藥。更何況他現在身在非常時期,竟敢去醫館找大夫看傷,這件事就很不尋常。”
他踢了一腳那看起來已經少了半條命的刺客:“妳說是我指使妳做的這件事,好啊,妳先說妳是哪裡人?怎麼接受我的指令?是我當面跟妳談,還是另外派人去告訴妳的?”
那人喘著粗氣,啞聲道:“是殿下您派人去告知小的,命小的等人在昨夜去驛站行刺……”
“行刺的目標是誰?我皇兄?”
“對。”
褚雁翎笑道:“那就不對了。太子殿下昨天去驛站是臨時決定的行程,連我都不知道的,怎麼可能告訴妳?”
那人立刻說道:“我等潛伏在太子府外多日,一直在找機會下手。昨天見太子只帶了數人出府,於是就跟蹤尾隨,一直跟到驛站之內就動手了。”
“為何不在半路動手?”褚雁翎追問道:“驛站之內的護衛眾多,妳們就不怕和護衛動手之後根本無法取勝嗎?”
那人答道:“路上行人太多,怕驚擾到官府……”
褚雁翎好笑地看著他:“行人再多,終究不是幫手,驛站裡的護衛雖少,但以一敵十,妳們竟是一群笨人嗎?”
褚雁德懶得聽下去,煩躁地開口:“行了老三,妳這轉著彎子的問,不就是為了把妳自己摘乾淨嗎?可我聽了半天還是沒聽出來妳的乾淨在哪裡?”
褚雁翎慢悠悠道:“大哥別著急啊,我就是怕妳聽不懂,這才慢慢地講給妳聽啊。這些人身上攜帶的刀劍,都是從咱們益陽本地的劍鋪買來的,這件事昨日我已命人調查過,從哪家鋪子買到的都可以有證據。因為各家兵器鋪為了區別各自的東西,都會在劍柄和劍刃連接處刻上自家的標記,而這些人的劍全是出自一家叫王二的兵器鋪,老闆證實,這些兵器都是三天前賣出的。要說這些刺客想殺人,為什麼不用自己最趁手的兵器,而要用新兵器呢?”
“混淆視聽,有什麼奇怪的。”褚雁德冷笑道。
“對,就是這混淆視聽。”褚雁翎盯著那刺客的臉:“他們這樣做是為了掩蓋他們自己本來的出處之地,怕別人查出他們的真實身份。可是,無論衣服換成什麼樣,兵器換成什麼樣,有一個標記卻是他們自己根本改不了的。那就是口音!”褚雁翎的聲音變得尖利起來:“雖然妳故意少說話以掩飾自己的口音不純正,但焉能騙得過旁人?妳說話絕不是鴻蒙人的口音!說!妳是哪裡人?”
那刺客哆嗦了一下,說道:“小的自小在江湖漂泊,東南西北去的地方多了,口音較雜,所以不夠純正。”
褚雁翎卻哈哈大笑,回頭對父皇道:“父皇知道兒臣掌管的鐵衣衛是何等重要的地方,凡是能進鐵衣衛的人,都必然是三挑四選,其中一條就是要身家清白,祖上五代都是鴻蒙本國人,以防有刺客奸細的混入。如果兒臣要找殺手也好,刺客也罷,必然是從鐵衣衛中挑人,怎麼會有個出身都說不清的刺客混跡其中?”
鴻蒙國主沒有回答,卻微微點了點頭。
褚雁德怒道:“誰說他一定是從鐵衣衛出來的?就不能是妳重金在江湖上買的殺手嗎?”
| FindBook |
有 2 項符合
碎心劫(7)完結篇的圖書 |
 |
碎心劫07(完結篇) 作者:東野蘭 出版社:欣然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4-10-06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平裝 / 320頁 / 25k正 / 14.8 x 21 cm / 普通級/ 單色印刷 / 初版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碎心劫(7)完結篇
★ 知名作者,全新筆名,最新力作!
★ 暢銷作品:華髮官人、天子從良、太傅戲醫女……等
羅曼史濃烈的愛、相思的苦、曖昧的甜,盡在碎心劫!
童濯心最怕決戰的那一天是用鮮血和生命堆積出來的。
她不想與親人在淚眼中訣別,更不願意看到金碧和飛雁兩國兵戎相見。
她擔心了那麼久的日子卻終究還是要來的。
金碧太子南隱的發難和挑釁,步步設局,招招狠毒,竟以越晨曦的生命作為賭注和籌碼。
而另一邊,裘千夜卻願意捐棄前嫌,全心全意地幫助她和金碧闖過這個難關。
她和裘千夜,越晨曦與胡紫衣,胡錦旗和錦靈,褚雁翎與莫岫媛,甚至是鴻濛的太子褚雁德、金碧皇帝……所有人都面臨著最後的抉擇。
童濯心相信,只有攜手闖過難關,才能看到海闊天空。
她堅信著,期待著,那一天的到來……
作者簡介:
東野蘭
在羅曼史小說的世界中浸淫十幾年,筆耕十幾年,對羅曼史小說的熱情始終持續燃燒中。
相信自己不是天才,也相信勤奮必然能夠有所成。
願意以筆寫我心,寫出感動讀者的作品。
愛美食,愛美人,愛美麗的人生。
易感動,擅敗家,最喜歡送禮物給朋友們,看到她們驚喜的笑臉。
所以,希望寫給讀者的每一部作品,都是讓讀者們驚喜的禮物。
★ 知名作者,全新筆名,最新力作!
★ 暢銷作品:華髮官人、天子從良、太傅戲醫女……等
TOP
章節試閱
第一章
清晨,褚雁翎輕手輕腳地下了床,莫岫媛本來還在睡,但她向來睡得很輕,睡眼迷蒙地看著他,問道:“妳要去上朝了?”
“嗯。”褚雁翎輕輕撫摸著她的臉頰,細心體貼地幫她把被子蓋好:“妳再睡會兒吧。我去看一下麟兒就走。”
“一早別去鬧他了。”莫岫媛拉住他,問道:“今天父皇會向朝臣們宣佈昨天答應妳的那些事情吧?”
“嗯,應該是的。”
“這一招,不知道能不能擋得住太子對妳的猜忌和群臣的悠悠眾口。”莫岫媛憂心地說:“父皇昨天說得對,妳這樣做,是有些像‘此地無銀三百兩’。昨天妳和裘千夜商量過...
清晨,褚雁翎輕手輕腳地下了床,莫岫媛本來還在睡,但她向來睡得很輕,睡眼迷蒙地看著他,問道:“妳要去上朝了?”
“嗯。”褚雁翎輕輕撫摸著她的臉頰,細心體貼地幫她把被子蓋好:“妳再睡會兒吧。我去看一下麟兒就走。”
“一早別去鬧他了。”莫岫媛拉住他,問道:“今天父皇會向朝臣們宣佈昨天答應妳的那些事情吧?”
“嗯,應該是的。”
“這一招,不知道能不能擋得住太子對妳的猜忌和群臣的悠悠眾口。”莫岫媛憂心地說:“父皇昨天說得對,妳這樣做,是有些像‘此地無銀三百兩’。昨天妳和裘千夜商量過...
»看全部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東野蘭 繪者: 書亦飛
- 出版社: 欣然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4-10-08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320頁
- 類別: 中文書> 漫畫/輕小說> 羅曼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