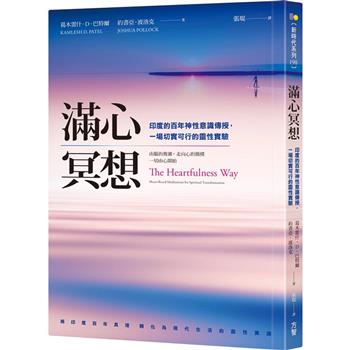〈專文推薦〉
徒法不足以自行,還須有文學相隨
謝志偉
文學把法律運作隱喻為人生戰場,本書則把文學大作當成實習法庭。《法律與文學》初版於一九八八年在美國問世,七年後,一九九五年,太平洋此岸的台灣「十九屆全國比較文學會議」的主題就是「文學、法律、詮釋」,後者有否直接或間接受了前者的影響,不得而知,(註一)倒是有兩點可以確認:其一,那場研討會的發表人和評論人,清一色全是來自本地英語文學界,沒有一個是法律學界人士,而在場的聽眾,筆者印象所及,亦如是。其二,文學界對法律的興趣遠早於法律學界對文學的興趣。如今,《法律與文學》增修版(2000)的中譯本在台問世,若能引起文學界與法學界雙邊的對話,想必將能激出精彩的火花,這點其實也是本書作者波斯納(Richard A. Posner)的想法之一。
正義、命運和法律之間的三角兼辯證關係從來就是文學裡面一個包羅萬象,變化多端的主題,此所以波斯納敢於斷言,「西方文化從一開始就充斥著法律的方法和意象。法律這個題材一直吸引著文學作家。」雖然此說絕非新意,但在該書裡,遠自古希臘的悲劇,近至近代、當代的歐洲小說(德、法、俄、西等),旁徵博引,波斯納都舉了例。當然,法律學者撰述專文而引文學例子,於西方,波氏並非第一人,台灣讀者可自行徵引者,譬如就有德國法學大儒拉德布魯赫(Gustav Radbruch,1878-1949)在一九一○年出版的《法學導論》,(註二)其中所引多例就出自聖經、希臘悲劇和十八、十九世紀的德語文學作品,而儘管波氏認為,「一九七三年詹姆斯?懷特出版教科書《法律的想像》(The Legal Imagination)前,『法律與文學』根本稱不上一個有系統的研究領域」,法律學者針對r文學裡的法律」之研究,歐陸甚至早於十九世紀即已出現。(註三)或者,光看台灣,著名法政學者薩孟武將近半個世紀前寫的《水滸傳與中國社會》(註四)和《西遊記與古代中國政治》(註五)亦有傲人之處,尤其後者第七章從民、刑法解讀捲簾大將(即沙和尚)犯小過而受重刑部分更是饒有文趣和法意。在此順便一提的是,著名的法律學者蔡墩銘則直接為多本法庭推理小說(或稱法律懸疑小說)撰寫「法律解析」。(註六)
然而,波斯納這本《法律與文學》令人驚豔之處,正在於西方現代法律人以其觀點另闢蹊徑深入進出西方文學文本。大學時代讀了英文系,當然有助於他撰寫本書,但文學理論的建構既非其所長,亦非本書標的。較之於文學人的法律觀點,波斯納法律人的文學觀點絕對有引人人勝之處。儘管他的對象顯然以法律人為主,但是本書無論對法律人或對文學人來說,都兼有挑戰的難度和挑逗的爽度--光是看他從法律角度評析莎士比亞的《威尼斯商人》及注釋內所附資料就值回票價。
波氏在本書中從法律的觀點解讀希臘悲劇及莎士比亞、梅爾維爾、狄更斯、馬克吐溫、杜斯妥也夫斯基、卡夫卡、卡繆、狄倫馬特等人的作品,一直到當代的美國暢銷作家約翰?葛里森(John Grisham,本身亦是律師),(註七)並從比較法學的觀點反覆討論各作品裡的相關情節(文學界的朋友有意以「法律」為主題作研究者,可在本書找到相當豐富的文本資料)。波氏正確地指出,雖然許多文學作品對圍繞著「法律本質」的主題展現了高度的興趣,但是就算作者本身曾為律師或具有法學素養,對「法律程序」則相對地較不在意。沒錯,因為,精確地來說,文學是對法律背後的「正義」之辯證有興趣,而非青睞其門前的「法務」之鋼硬。但是這並非意味著,法律與文學在此議題上就該分道揚鑣,相反地,文學與法律,尤其是法理學之共同基礎--哲學--是兩者之間的觸媒和黏著劑,(註八)易言之,兩者之間除了「修辭學」(註九)外,更有「形上學」的介面。而尤其就在「形而上」這一部分,東∕西(漢民族∕歐美)文學和法律都在此分流。這當然牽涉到「法律」、「宗教」和「政治」或「權力」的緊密關係了。而依筆者之見,於西方,法律和法理學在神話解魅後,其源頭就定位在基督教及猶太教的舊約和上帝及世俗政權之間,並逐步由前者向後者移動,而對漢民族來說,神話不但過早解魅且之後定調在政治中,而終於由禮入法(內儒外法)的結果。(註十)從文學回應來看,有上帝,有聖經,固然生前有禁令,死後有裁判,但也意味著,存在時就有「甘之若素的慰藉」和「苦不堪言的掙扎」兩種之間的選擇或擺盪,前者在中古世紀過後就漸失影響,後者就發展出懷疑、辯證和抗爭的人文精神,是以人文主義、啟蒙思想、理性主義伴隨著自然法的觀念及法國大革命出現在歐洲而非亞洲。
於是,在歐洲,個人權利意識逐步突破君王諸侯以法控民的掌握,呈現在文學裡,就出現了譬如與歌德並享文壇盛名的席勒(Friedrich Schiller, 1759-1805)所寫的「威廉泰爾」(Wilhelm Tell,就是射蘋果的故事)裡,蓋真正激起威廉泰爾和其瑞士同胞起來推翻統治者的引爆點,即是:統治者派人在廣場上豎了一隻柱子,上面掛著統治者的帽子代表其人,而要求路過行人一律屆膝脫帽致敬,也就是要求「敬,如王在」,並稱,國王就是要藉此認清誰是臣服,若有不從者連人帶產沒人官中。(註十一)最後的結果是,人民戰勝了統治者,瑞士脫離羅馬帝國,從此獨立。而回頭看看漢語文學《水滸傳》裡的梁山泊好漢,廝殺半天,劫法場,殺昏官,開山立寨,佔地為王,都是罪無可逭,就靠一個「義」字撐著,最後卻被招安效忠去也,而這一切只因宋江認為,奸臣儘管昏昧,皇上卻是至聖至明。(註十二)以傅柯的話解讀西方文學裡的「瑞士建國」和中國文學裡的「水滸招安」,就是,權力擁有者之所以能順利統治權力對象,即是因為他們做到了只讓人民認同「君權」或「國家主權」,但是不讓他們意識到「支配者」或「統治者」,只讓他們意識到「服從」的必要,而不能讓他們感受到「屈從」的事實。(註十三)做不到這點的統治者就受到挑戰。於是,羅馬帝國失利,瑞士人民勝利:於是,帝王朝廷招安成功,水滸英雄雲消霧散。
波斯納在本書中展現了對卡夫卡甚濃的興趣,不是沒有原因的。除了兩人係法律同行外,卡夫卡將法律謎樣化的作法最是令人著迷,波氏很實務地指出,卡夫卡的《審判》(1914)忠實地呈現了奧匈帝國刑事訴訟程序的許多細節,並點出文學裡已成定論的一句話:主角約瑟夫.K的行為和懲罰都脫離了關係。卡夫卡不但將法律裡罪與罰的邏輯順序顛覆了(先起訴,再任由被告苦苦追尋罪名為何),甚至將罪與罰脫鉤!法律的嚴密被演繹成神祕,程序的邏輯被翻轉成荒謬,人生不是常常如此嗎?這種形而上的法律文學化當然會成為他們的特質,因為他們有宗教及既迫人又救贖的上帝。(註十四)另一方面--這個文學手法的推論,波斯納應該會同意--卡夫卡這種在其作品裡將法律詭異化以隱喻存在意義之不定,其實和修辭及詭辯在法律實務上所扮演的角色也可看成是平行比照的,《威尼斯商人》裡女扮男裝再假扮法官的波希霞讓夏洛克由狂喜變慘痛的表現就是一例。而這裡的兩假--假男人和假法官--使得何謂「正義」和「真理」成為極為弔詭的問題,更別提隱藏在夏洛克和安東尼兩人後面猶太教和基督教的正統之爭了。
回頭看傳統中國統治者以「禮」和「法」的兩種手段來駕馭人民,也有可對照之處,蓋治者以禮治民,則人民不知其被治也,若搬出刑罰,也就是「齊之以刑」,則恰好點醒人民注意到其臣屬與被治之處境。不管怎麼說,至少孔子聽到晉國將刑法鑄於鼎上並公佈天下時的反應,是非常氣急敗壞的:
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衍,所謂度也。∕。。。∕今棄是度也,而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貴賤無序?何以為國?(註十五)
持這種看法的人,也不只是孔子而已,左傳昭公六年也記載著類似的看法:
三月,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書,曰:「吾始有虞於子,今嚴斷其罰,以威其淫。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注:辟,法也),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閒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制為祿位,以勸其從,∕。。。∕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僥幸以成之,弗可為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行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如是,何辟之有?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註十六)
很清楚的,叔向並不是在要求取消對庶民的刑罰,相反的,他強調「嚴斷刑罰,以威其淫。」(註十七)然而,一旦刑鑄於鼎,即為成文法,於是,他和孔子就擔心了,「因為鄭、晉的刑書均是專對百姓用的而管不到貴族,公佈之後,使人民知道法有例外,當然會成為爭亂之源。」(註十八)直言之,這就是『權移於法,故民不畏上也』,同時也是「刑不可知,威不可測」(註十九)的現象。至於韓非子,很清楚地強調成文法,也強調「刑鑄於鼎」的作法:「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而布之於百姓也」,(註二十)「法莫若一而固,使民知之」。(註二十一)當然,韓非子並非純為人民著想,這些看法主要是替人君立威、立信,蓋其上文為「賞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罰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也。(註二十二)
其實,有關類似鑄刑於鼎的關鍵問題,並非中國所獨有。十九世紀末德國著名社會學家齊默爾(Georg Simmel,1858-1918)就對類此現象作出觀察。他指出:
如果在一個專制獨裁的政體之下,統治者以賞賜和刑罰來處理命令之執行與否及成果優劣,則意味著,他願意被徵於令〔或被徵於書〕,也就是說,屬下百姓應有權利要求,不管刑罰定的多高,一旦明文形諸文字,則獨裁者亦不得逾越之。(註二十三)
在此,不能不提到聖經。波斯納在本書中並未將聖經列為重點,連帶地宗教所扮演的角色亦十分薄弱,這顯然是因為他的現代性和實務性所致。不過從舊約來看,聖經可說是西方法律和文學的共同源頭之一。(註二十四)而在十六世紀時,聖經的翻譯還曾經被政教聯合嚴法禁止,原因就是教廷除了擔心翻譯過程中會出現謬誤外,更擔心詮釋聖經的專屬權會被稀釋掉。易言之,只要是僅有少數人看得懂拉丁文、希伯來文或古希臘文,人民就難徵於書,神職系統的威嚴始能長保不墜。(註二十五)
到了現代,卡繆的《異鄉人》(1940寫成,1942出版)則以另類方式解構這些「徵於書」的法律,波斯納也以法律實務探討了此問題,他指出,小說主角莫梭被判死刑,不是因為他殺了一個阿拉伯人,而是因為他對母親生前不理(送她進養老院),死後不悲(不但未哭,第二天還和女人上床),檢察官怒斥他比另案弒父的兇手之罪孽還要深重。波斯納卻忽略了,小說裡的檢察官和神父,甚至辯護律師等人都不是真的在指責莫梭不孝,而是指責他不信上帝,人子否認上帝,此即等於宗教上的的弒父了。相較於卡夫卡把約瑟夫?K困在如五里霧中的層層法網和建築物裡而猶不知犯了何罪,卡繆則讓莫梭在海邊的豔陽下犯下清清楚楚的殺人罪(開了五槍),之後在心理上卻完完全全置身事外,與約瑟夫?K事實上是一體兩面。
總之,西方的文學裡自始即不乏人倫∕人性與法律∕律法正面衝突,或以後來的概念來看,是自然法挑戰實證法的實例,古希臘悲劇的《安蒂岡妮》、《伊底帕斯王》、《奧瑞斯提亞》等都是例子,但是他們也鍛鍊出將法律形而上化的思維,而傳統中國庶民與法接觸的結果卻多僅是傷害、挫敗和畏懼。東漢王充在《論衡?四諱篇》文末指出,時人忌諱在井上磨刀,原因有二,一為實務理由,「恐刀墮井中」也,一為心理因素,怕「厲刀井上,井刀相見,恐被刑也」。(註二十六)後者十分值得吾人深思,若非談「刑」色變,必不至於迷信∕驚嚇到深恐「井」與「刀」和為「刑」,而「刑」之古字還真是「井」與「刀」的結合,(註二十七)縱算「兵刑一體」的看法仍有爭議,這總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繩的加碼版。(註二十八)再看「法」、「罰」同音,音同意近,觀諸《尚書?呂刑》的黥(剌面)、劓(割鼻)、臏(斷足)、宮(閹割)、大辟(「辟」即「法」也,大辟者,處死)的五刑,對照《禮記》所載的「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註二十九)今人不難想像,何以會有「井上磨刀」之忌了--「傳統中國法所稱之『法』,通常等於『刑』,接近『制裁』」,非獨特見解,乃尋常事也。(註三十)蓋中國歷代的刑法都體現了統治階級的政治需要,無法不威,庶民一旦犯了王法,對統治者來說,就是觸一「法」而動「權」身,是可忍孰不可忍,一旦上了刑,就難保庶民不會「觸一法而洞全身了」,動刑的目的不在匡民,在正法也。(註三十一)
當然,刑要比酷,中古歐洲相對於封建中國亦不遑多讓,(註三十二)只是中國改朝換代皇帝還在,只有循環,沒有演進的歷史對照著,西方一方面有聖經可遵守,另一方面又有上帝可背叛,先有黑暗裡的中古世紀,繼有啟蒙後的理性主義,才會使得黑格爾認為,中國的法律裡只有君主的權力,沒有人民的權利之嘲諷及不屑。(註三十三)日後,清廷到了不得不與與西方列強交往而涉法律情事時,其傳統法律仍被視為是「重法酷刑」。(註三十四)
波斯納在此書所處理的其他面向,諸如法律的文體文學化,法律詮釋向文學批評取經是可行抑或可惜,女性主義和法律的關係--自然法和實證法之間的爭鬥,官檢(註三十五)和著作權保障等等,有些是歷史悠久,有些則是方興未艾,長期看來,顯將有發展和精緻化的空間。只是,習慣漢語文學內直挺挺控訴司法不公、政權不義的讀者,如賴和那篇精彩的短篇小說《一桿稱仔》、包青天公案小說或關漢卿的《竇娥冤》,比較具體期盼的還是,這輩子可千萬別再從「摘奸發伏」等到「中年發福」了。
本書原著係以英語撰寫,波斯納曾為律師,復為芝加哥大學法學院教授,現為美國聯邦第七巡迴上訴法院院長,是西方文化的一員,《法律與文學》裡的舉例也純屬西方文學,因此,每位華人在閱讀本書中譯本時,除了橫越語言柵欄外,同時也在跨越文化邊境和穿越學界藩籬,都將因辨同而見異,多賴「訝異解放壓抑,叉義凸顯差異」,所謂「閱讀延引新意」是也,收穫多多,自不待言。
法律界人讀此書,可激發同情心和同理心,如波斯納所認為。文學界人讀此書,可開闊視野和觸角。其他人讀此書,則將明瞭,他們根本不是「其他人」。總之,作者的收入和作品的意涵同時成長,讀者居功厥偉,利人利己,筆者特為此文,「建議勇為」。
注釋:
註一、該會議由中華民國比較文學學會和東吳大學英文系合辦。隔年三月,由中外文學月刊社發行會議論文集,馬建君∕廖炳惠主編:《文學、法律、詮釋》,計收十篇論文,每篇並各附評論一篇。論文及評論均有可觀之處。波斯納的名字和該書均未出現在各篇論文和評論裡,不過反過來看,波氏由於語言關係,顯然亦未能接觸這些論文和評論,也是他的損失。
有趣的是,該會議主題的英文名稱Interpreting Law and Literature,與一九八八年在美國出的一本書同名:Interpreting Law and Literature, Sandford Levison and Steven Mailloux eds. 顯示該主題的確已為東西兩方所重視。
註二、德文原版標題為Einf?hrung in die Rechtswissenschaft, 中文譯本為《法學導論》,台北:商周,2000。此外,也可參考阮文泉,〈法律與文學——以德沃金教授的論述為中心〉,《法律評論》,六十四卷,7-8期合刊,頁32-40, 注2,3,4,5裡均提供了一些美國早於二十世紀的八零年代初即陸續寫出的相關論文或專書。
註三、見普林斯頓大學德語文學教授Theodore Ziolkowski於1990年出版的鉅作German Romanticism and It’s Institutions(德國浪漫主義與其體制)第三章〈法律與浪漫主義作家〉注一和注二裡就指出椰林(Rudolf von Jhering)1872的一篇著名的相關專論及另外兩位知名法律學者分別於1903年和1912年針對有法學專家專文討論歌德的《浮士德》裡有關訂約的法律意涵,注一所提的第十九屆全國全比較文學會議論文集裡古佳豔(頁56-77)的論文多處引用本書,有意者可參考,本人使用者為該書德文譯本Das Amt der Poeten. Die deutsche Romantik und ihre Institutionen, Stuttgart: Klett-Cotta, 1992.
註四、台北:三民,1999(1967初版)。
註五、台北:三民,1999(1957初版,1967再版)。
註六、例如高木彬光,《法庭魔女》,台北:月房子,1994,頁236-238。讀者若對刑案寫成劇場故事有興趣的話,也可參閱法務部出版,台灣雲林地方法院編輯的《窗外有藍天一法律劇場》,1996。
註七、另一在此值得一提的是近年崛起的德國法律學者兼作家徐林克(B. Schlink),他的《我願意為你朗讀》(台北:皇冠,2000。德文原題為Der Vorleser, 1995)波斯納要是讀到,一定會喜歡,這是當代小說,另一本雨果(1802-1885,今年二百週年冥誕!)的《悲慘世界》,波氏沒有提到,在這裡介紹給讀者,這是一本環繞法律、人性、犯罪、宗教、執法者及等的社會小說,非常適合拿來探討本書《法律與文學》的主題。
註八、波斯納在1990年出版的The Problems of Jurisprudence裡於十三章再論「法律和文學」、「女權主義」等議題,更可見文學與法理學之間的緊密關係。該書中文譯本已出版:《法理學問題》,蘇力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
註九、對此有興趣者,可參考王潔(「潔」字應為簡體字),《法律語言研究》,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1999。懂德文者另可參考,Fritjof Haft, Juristische Rhetorik, Freiburg: Karl Albert, 1990(初版1978),對欲提升法庭辯論實戰能力的人來說,相當值得推薦。
註十、此乃定論,別的不提,瞿同祖的《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第一章,第一節就從家族談起,已是明證。
註十一、參閱Fr. Schiller, Wilhelm Tell, in, Fr. Schiller, Werke in vier B?nden, Bd. 4, Hamburg: EMA-Verlag 1983, p. 115。
註十二、除了前提薩孟武的《水滸傳與中國社會》外,另請參閱一篇精闢論文,陳鋕雄,〈盜匪的正義觀一論梁山泊的恩義世界〉,《月旦法學雜誌》,53期,1999/10,頁23-34。
註十三、參閱Michel Foucault, Dispositive der Macht, Berlin: Merwe 1978, p.79.另請參閱筆者拙作,〈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知識與權力」,從德語文學的一個例子談起〉,《東吳哲學學報》,第二期,1987,頁159-184。
註十四、像這種將法律荒謬化以凸顯生命困境在《軍規22條》裡也呈現了出來,法規本身的輾轉二律悖反使人手足無措而僅能乖乖就範。
註十五、春秋左傳註,楊伯駿編著,台北,中華書局,(無出版日期),頁1504(昭公二十九年)。
註十六、仝上,頁1274-1276。
註十七、參閱張純,王曉波合著之《韓非思想的歷史研究》,台北,聯經,民72,頁19。
註十八、沈剛伯,〈從中國古代禮刑的運用探討法家的來歷〉,《中國哲學思想論集》,總論篇,台北,水牛,民1988(初版:1976),頁223。從階級鬥爭的觀點來看,要求成文法的公佈,正反應著「在奴隸制時代,法律不公佈出來,這樣貴族可以任意斷罪量刑。新興地主反對貴族壟斷法律,堅決要求把成文法律公佈出來,以保護他們的私有財產權和其他權利。代表新興地主的法家,要求公佈成文法」(李用兵,《中國古代法制史話》,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民83,頁39-40)。
註十九、《左氏會箋》,杜預集解,台北,廣文書局,民59,第二十一,昭六,頁第三冊,頁44。
註二十、《韓非子今註今釋》,上冊,邵增樺注釋,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民76,頁415(第四卷,難三)。
註二十一、仝上,第一卷,五蠹,頁36。
註二十二、仝上。高柏園語:「法一經編訂而公佈之後,法之標準性即告生效,其權威性亦隨之而建立了,即使君王亦不宜隨意更改。」(《韓非哲學研究》,台北,文津,民83,頁159),這裡須強調的是,「即使君王亦不宜隨意更改」僅是公佈法之後的結果,不是目的。
註二十三、Georg Simmel,Soziologie. Untersuchungen ?ber die Formen der Vergesellschaftung, hg. v. OttheinRammstedt, F./a.M.: Suhrkamp l992, p. 165, 166. 此處尤其關鍵者為:”Der Untergeordnete soll das Recht haben, etwas von ihm zu fordern, der Despot bindet sich mit der Straffestsetzung, so horrend sie sei, keine h?here aufzuerlegen” (p.166).齊默爾接著又指出,拉丁文的「法律」這個字”Lex”原義即為和約,而雖然是由統治者制定,再交由被統治者接受,但是由於這個動作的前提是,雖有主體客體之別,當雙方均互為個體。雙方都看得到「法有明文」。(參閱頁167).
註二十四、參閱亞蘭?德修茲,《法律的創世紀》,林為正譯,台北:先覺,2001. 另請參閱伯爾曼,《法律與宗教》梁治平譯,北京:新華,1991。(原著為Harold J. Berman, The Interaction of Law and Religion, SCM Press Ltd., 1974)。
註二十五、參閱卡洛萊茲∕伯德∕索瓦合著,《禁書》,吳庶任譯,台北:晨星,2002,頁214-219。
註二十六、有關此部分,可參考趙慧平,《忌諱》,台北:新雨,1992,頁184-188。
註二十七、參閱正中形音義綜合大字典「井」字條,台北:正中,1977。
註二十八、有關「兵刑一體說」可參閱楊鴻烈,《中國法律思想史》,頁238-241。
註二十九、但是,大夫也沒敢偷笑,因為代誌大條時,仍可由皇帝賜死。此外,我們別忘了源自明太祖朱元璋的廷杖,這部分可參閱杜婉言,《中國宦官史》,台北:文津,1996,頁252-258。
註三十、劉恆妏,〈由包公系列小說看傳統中國正義觀〉,《月旦法學雜誌》,53期,1999/10,頁37。
註三十一、這與受了啟蒙思潮和理性主義,乃至法國大革命影響的的席勒在其中篇小說《失去尊嚴而犯罪的人——一個真實的故事》呼籲法官不能只看法條而須將犯罪情境及犯人心理狀態、背景納入考慮之舉可說是大相逕庭。參閱彭雙俊譯的該文,《台灣新文學》,10期,1998.6,頁338-357。
註三十二、請參閱王永寬,《中國古代酷刑》,北縣:雲龍,1995,及川端博,《揭開歐洲拷問史祕辛},時佩猛譯,北縣:台灣實業文化,2001。但是,西方對「酷刑」的定義不一定與我們完全一致,譬如當初接受了啟蒙思想的歐洲人是把斷頭臺(Goulliotine, 係以發明人之名命名)的發明視為是一種較符合人道的進步——因為它既快又乾脆。
註三十三、對於這點之解說,請參閱石元康,〈黑格爾的中國觀〉,傅偉勳∕周陽山主編,《西方思想家論中國》,台北:正中,1993, 頁23-74.
註三十四、參閱徐振雄,〈從「典範轉移」觀點論中國傳統法律文化與現代法律價值〉,《月旦法學雜誌》,53期,1999/10,頁50。
註三十五、波斯納是把焦點放在有關色情方面,不過吾人可順便想想看中國的文字獄和德國威瑪時期前後及納粹帝國時的焚書、禁書。
(本文作者為東吳大學德文系教授兼外語學院院長)
〈專文推薦〉
法學界的莫札特——波斯納法官
劉靜怡
當我答應在數天內寫出一篇關於本書作者理察?波斯納的文章後,在接下來的幾天,我每天便在回憶和困惑中度過。回憶的不只是五、六年前難脫台灣傳統法學教育影響的我在芝加哥大學法學院一邊「苦戀」法律經濟分析(economic analysis of law),一邊和博士論文進度掙扎不已時的生活點滴,更想念當時有幸身處的那個雖然嚴肅、但是卻對汲取知識和理性論辯充滿誠意和包容的求學環境。至於困惑不已的,則是對於大家慣稱波斯納法官這一位當代法學界傳奇人物學思歷程和生活背景,到底應該如何描繪才能既切合重心,又不失之瑣碎。最近二十年來同時兼具法官和教授身分的波斯納,雖然通常只有在忙完聽審工作之後的下午才會出現在芝加哥大學法學院,波斯納法官低調沈靜、不喜交際甚或單純規律的上課與生活節奏(據說他是法學院最排斥出國旅行的教授;他自認此生至今最後悔的事情,便是大學時看了太多電影。你最好丟掉一些既有的成見,才能夠將這樣的人和心目中所謂法學權威連結在一起),他也讓學生覺得不夠刺激,但卻是我最為敬佩的老師之一。
在深夜或週末,許多研究室仍然燈火通明,學生幾乎隨時可以從容走進教授研究室或直接發電子郵件要求解惑請益,這是芝加哥大學法學院教授群之所以能在眾多出色法學院中傲視群雄之處。不過,波斯納其人其事,更具傳奇色彩。我在芝加哥大學法學院的論文指導教授勞倫斯?萊西格(Lawrence Lessig)自擔任波斯納法官助理時期起,便視波斯納為可以接受無盡辯難的學術導師,他曾將波斯納的學術寫作能力和莫札特創作音樂的天才相比擬:而身為法律經濟分析先鋒之一的諾貝爾獎經濟學得主若納?寇斯(Ronald Coase),曾經戲稱波斯納的寫作出書速度遠比寇斯自己閱讀的速度來得快(或許這句話並非戲言:筆者書架上所蒐集的波斯納著作,永遠比已經閱讀過的來得多)。
究竟,波斯納到底是怎樣的一個法律人?波斯納的法學論著又有哪些特色呢?《法律與文學》這本書的詳細內容,以及這本書所探討的諸多介於法學、文學、哲學和美學等領域之間的有趣問題,有待讀者自己去咀嚼,這篇短文能闡述的相當明確而有限:我希望根據自己的親身經驗和觀察做出的描述,可以為讀者提供一塊理解波斯納其人其事其文的敲門磚。
波斯納法官的專業養成過程,幾乎循著所有美國法學界菁英的模式:出生於紐約一位律師和一位左傾中學老師組成的猶太中產階級家庭,十六歲就進入耶魯大學主修英文,二十歲大學畢業後進入哈佛法學院,以最頂尖的學業成績傲視同儕,法學院畢業後擔任當時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布瑞南的助理,並成為史丹佛和耶魯法學院競相延攬的對象,之後在芝加哥大學奠定學術地位。波斯納從來不自認天賦異稟,他長期所投注的努力和幾近嚴苛的自我要求,證明這一切均非僥倖。然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種美國法學界菁英幾乎都具備的經歷,甚至,波斯納法官還培養他的兒子艾瑞克,波斯納(Eric Posner)成為法律經濟分析新秀學者,兩三年前剛從賓州大學法學院轉到芝大法學院任教。這種法學世家的特色,不免教人感到極度乏味而無趣。比較令人好奇的,思考深刻精確且文風流暢犀利的波斯納法官,除了能夠長期秉持其準確的穿透力,言之有物之外,何以幾乎每本著作都有引發熱烈的討論?
無論你對波斯納法官著作的內容和主張同意與否,他的作品質量長期維持在一定以上的水準,應該足得以說明個中理由的不爭事實,其勇於發掘問題和突破既有框架,也更應該是原因之一。然而,以其著作之豐、聲名之盛,波斯納法官所選擇的學術研究和著述方向,卻不同於相對而言趨於向傳統認同、擅長從傳統中尋求有利於自己發展的踏腳石的多數菁英份子會願意選擇、或者有勇氣選擇的道路。「波斯納法官」這個名字,在美國法學界一直都是具有先鋒意義或者身處論述爭議核心的名號,如同大家所熟知的,波斯納法官濃厚的法律經濟分析傾向,雖然為美國最近數十年來的法學發展,寫下幾近革命性的重要史頁,但卻也向來是引發不少法學界人士持續反對的理由。波斯納法官近年來對於道德哲學批評甚力的態度,讓許多法律哲學家如坐針氈,早已不是新聞,引發其好友之一芝加哥大學哲學系和法學院合聘教授瑪莎?努斯波姆(Martha Nussbaum)嚴肅探究其對當代道德哲學的不滿和批評,是否肇因於自幼時起便受到左傾的母親相當深刻的影響,故而潛意識裡反其道而行,以接近功利主義的基調,對於標榜人文精神、浪漫主義和理想主義的道德哲學絲毫不加留情地提出一連串系統化的質問。波斯納的主張,嚴重時甚至引發波斯納法官是否應該顧及其法官身分,稍稍收斂起其進行公共評論的範圍和風格,以免違背法官倫理規範的尺度,晚近最為著名的例子,便是波斯納針對柯林頓總統彈劾案所引發的爭議以及爭議過程中所出現的各種主張進行研究後,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國家大事》(An Affair pf State: The Investigation, Impeachment, and Trial of President Clinton)這本書上市之後,執教於紐約大學法學院和牛津大學的法律哲學家德沃京(Ronald Dworkin)針對這本書的內容和出現時點,公開在《紐約時報書評》上指責波斯納針對正在進行中的案件發表評論、不做自我節制,違背法官倫理守則所引發的爭議,以及接下來波斯納法官透過《紐約時報》的專訪做自我辯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