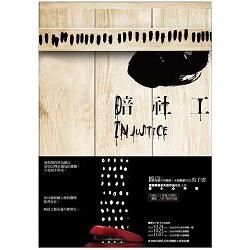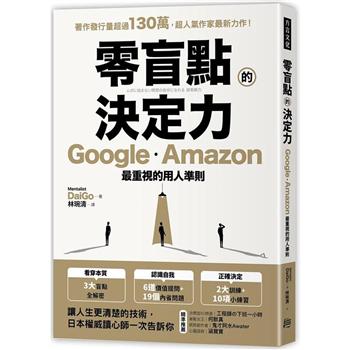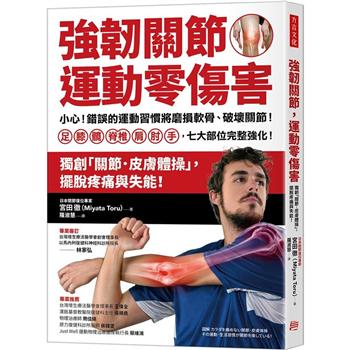小說暢銷天王 吳子雲 首部黑暗系失控作品
【限量木殼版】
量身打造專用木殼,將暗社工的人性與祕密,鎖進木殼裡……
【限量木殼版】
量身打造專用木殼,將暗社工的人性與祕密,鎖進木殼裡……
曾經,我是個在出版界呼風喚雨的暢銷書作家。因為爸爸開旅行社,我在當兵前就已經去過二十多個國家,因此出了幾本類似旅遊指南的書。後來因為旅行讓我看見世界有多大,人的生活文化有多不相同,於是我開始寫一些與社會關懷有關的內容,挖掘大城市小鄉鎮裡,天天在發生的,平凡人的故事。我的書開始登上暢銷書排行榜。這樣的書寫多了,練就了說故事的本領,於是我試著寫小說。大概是故是說得還不錯,有些電視台前來洽談,買了我的作品去改編成電視劇。
正當我意氣風發之際,我家就出事了。我爸的旅行社周轉不靈倒閉,欠了一屁股債,家裡四間房子賣光了還賠不完,數百名消費者委請律師對我家興起集體訴訟。在被告之前,我爸偷偷離開台灣,逃到越南。
新聞記者跑來問我對我爸這麼不負責任的行為有什麼看法,我沒經大腦便回答:「我不能說什麼,他是我爸。」從此,我成了「包庇自己人」的共犯,加上後來的酒駕及打人風波,我整個人只能說是毀了,書籍銷售慘不忍睹,連出版社都不再接我的電話,從此只能避居偏遠的山區,好換取一些平靜。
然後,他出現了。這個陌生人在網路上寫信給我,書信往來兩個星期左右後,他問我想不想再一次呼風喚雨,於是我決定跟他見面。但說穿了,我其實沒想過要回到從前的日子,我之所以答應見他,只因為他讓我感覺自己仍然被重視。
我覺得自己有點悲哀。
於是,在八月的某一天,我跟他約在公園裡見面,那天,有個叫「閃電」的颱風正在逼近台灣本島。
他開始跟我說起他的故事,並要求我詳實記錄,他說,寫好這個故事,這本書絕對可以大賣。而故事,要從他的職業開始說起:
「我有兩份工作,工人和社工。前者有薪水,一個月含加班大概是三萬塊出頭,後者沒薪水,也沒人叫我做,但我就是想做。我的社工工作跟一般人了解的完全不一樣。也因為太不一樣了,所以從事這份社會工作的,目前只有我一個人。也就是說,除了我之外,沒有人知道。因此,有時我覺得很孤獨……」
他說著,而直到他說到某個段落,我才知道,他才不是什麼社工……他是「暗社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