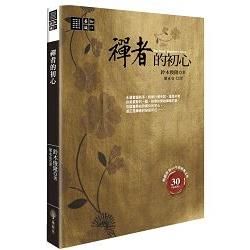「永遠當個新手。對修行者來說,這是非常、非常要緊的一點。
如果你開始禪修的話,你就會開始欣賞你的初心。這正是禪修的秘密所在……」
──鈴木俊隆禪師
本書暢銷英語世界30年,提攜對佛法、禪感興趣的西方讀者不計其數
渴望親近禪的你也將必然受惠……
鈴木俊隆曾說:「我們必須抱著初學者的心,放開一切執著,了解萬物莫不處於生滅流轉之中。除剎那生滅的顯現於目前的色相以外,別無一物存在,一物會流轉為另一物,讓人無法抓住……」
禪修的心應該始終是一顆初心、初學者的心。那個質樸無知的第一探問──「我是誰?」,有必要貫徹整個禪修的歷程。
初學者的心是空空如也的,不像老手的心那樣飽受各種習性的羈絆。他們隨時準備好去接受、去懷疑、去對所有的可能性敞開,只有這樣的心能如實看待萬物的本然面貌,一步接著一步前進,然後在一閃念中證悟到萬物的原初本性。這種禪心的修行全書遍處可見。
這本書的每一章節都直接或間接地碰觸到這個問題──如何才能在修行生活和日常生活中保持初心?這是一種古老的教學法,利用的中介是最簡單的語言和日常生活的情境。它的精神是,學禪的人應該自己教育自己。
作者簡介:
鈴木俊隆(Shunryu Suzuki)
是一位謙遜無飾、廣受愛戴的精神導師,生於1904年,父親亦是一位禪師。鈴木俊隆禪師自年少即開始禪修之訓練,經過多年的修習而臻成熟境界。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當多數法師皆改行從事其他職業時,鈴木禪師仍堅守他的禪師生涯。1959年,他遷移至美國舊金山。當時不少法師以「嶄新的西裝及閃亮的皮鞋」前來西方國家,鈴木禪師卻決定以「老舊的僧袍及光亮(新剃)的頭顱」到臨。
幾年內,他的教授吸引了許多西方學生,他在舊金山建立了禪中心,並在加州卡梅爾谷地的塔撒加拉(Tassajara)成立西方第一所禪修院。
由於長年的疾病纏身,1971年12月,他因癌症而辭世。
譯者簡介:
梁永安
專職譯者,台灣大學哲學碩士。譯有《牛的印跡》、《來自深淵的吶喊:王爾德獄中書》、《小天使艾絲梅拉達:唐.德里羅短篇精選集》、《沒有神的宗教》等。
推薦序
【序】他就在我們之中/休士頓.史密斯
兩位鈴木禪師。半世紀以前,鈴木大拙隻手將禪帶了到西方,這個移植的歷史重要性,被認為可媲美亞里斯多德和柏拉圖這兩位的作品分別在十三和十五世紀被翻成拉丁文。五十年後,鈴木俊隆做出了幾乎不遑多讓的貢獻。在他唯一留下的這本書中,那些對「禪」感興趣的美國人所找到的,正好是他們所需要的最佳補充。
鈴木大拙的禪是風風火火的,反觀鈴木俊隆的禪則顯得平實無奇。「開悟」是鈴木大拙禪道的核心,而他的作品會引人入勝,這個眩目的觀念居功不少。但在鈴木俊隆的這本書裡,「開悟」或是其近義詞「見性」卻從沒出現過。
鈴木俊隆禪師入寂前四個月,我找到個機會問他:「這本書為什麼沒有談到開悟?」禪師還未開口,他太太就湊過來,調皮地輕聲說︰「因為他還沒開悟嘛!」禪師裝出一臉驚恐的樣子,用扇子拍拍太太,一根手指豎在嘴邊說︰「噓,千萬別說出去!」大家都笑翻了。等到笑聲沉寂下來,禪師說出了真正的原因︰「開悟不是不重要,只是它並非禪需要強調的部分。」
鈴木禪師在美國弘法僅僅十二年(十二年在東亞是一個週期),然而成果豐碩。經過這位文靜且個子小小的人的努力,一個曹洞宗的組織如今在美國已然欣欣向榮。他的人與曹洞宗的禪道水乳交融,是這種禪道活生生的表現。「他的無我態度極為徹底,不留下任何我們可以渲染的奇言怪行。而儘管他沒有留下任何世俗意義下的豐功偉績,但他的腳印卻帶領著看不見的世界歷史向前邁進。」(語出瑪莉法爾拉斯, Mary Farlas)他遺下的功蹟包括了美國塔撒加拉山(Tassajara Moutain)的禪山禪修中心(西方的第一家曹洞宗禪寺)以及舊金山的禪修中心;而對一般大眾而言,他留下的,則是這本書。
不抱任何僥倖心理,他早就為弟子們做好心理建設,讓他們可以面對最艱難的時刻──也就是目睹他形體從這世界消失、歸於虛空的那個時刻︰
我臨終時若受著痛苦,那不打緊,不要在意;那就是受苦的佛祖。你們可別因此產生混淆。或許每個人都要為肉體的痛苦與精神的痛苦而努力掙扎,但那並不打緊,不是什麼問題。我們應該深深感激自己擁有的是一個有限的身體……像是我的身體、你們的身體。要是人擁有無限的生命,那才是真正的大問題。
他也事先安排好傳法事宜。在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舉行的「山座儀式」(Mountain Seat ceremony)上,他立理查.貝克(Richard Baker)為其法嗣。當時,他的癌症已惡化到必須由兒子摻扶才能行走的地步。然而,每走一步,他的禪仗都叩地有聲,透露出這個人雖然外表然溫文,內心卻有著鋼鐵般的禪意志。貝克接過袈裟時,以一首詩作為答禮︰
這炷香
我執持良久
現在要以「無手」
奉給我的師父、我的朋友
也是這寺廟的創立者
鈴木俊隆大師
你有過的貢獻,無可衡量
與你走在佛祖的微雨中
我們衣袍濕透
但蓮花瓣上
卻無滴雨停駐
兩星期後,禪師入寂了。在十二月四日舉行的喪禮上,貝克禪師向出席者朗誦了以下的讚辭︰當師父或弟子都是不容易的事,儘管那必然是此生中的至樂。在一片沒有佛教的土地弘法也不容易,但他卻度化了許多弟子、僧眾、俗眾,讓他們走在佛路上,為全國數以千計人的生命帶來了改變。要開創和維持一家禪寺很不容易,何況還加上一個市區的禪修團體、加州和美國其他地區的許多禪修中心。
但這些「不容易」的事、這些非凡的成就在他手裡卻是舉重若輕,因為他倚仗的是自己的真實本性,也就是我們的真實本性。他留下的遺澤不亞於任何人,而且無一不是要緊的︰佛的心、佛的修行、佛的教誨與人生。他就在這裡,就在我們每一個人之中,只要我們想他。
──休士頓.史密斯(Huston Smith)
麻省理工學院哲學系教
【序】他就在我們之中/休士頓.史密斯
兩位鈴木禪師。半世紀以前,鈴木大拙隻手將禪帶了到西方,這個移植的歷史重要性,被認為可媲美亞里斯多德和柏拉圖這兩位的作品分別在十三和十五世紀被翻成拉丁文。五十年後,鈴木俊隆做出了幾乎不遑多讓的貢獻。在他唯一留下的這本書中,那些對「禪」感興趣的美國人所找到的,正好是他們所需要的最佳補充。
鈴木大拙的禪是風風火火的,反觀鈴木俊隆的禪則顯得平實無奇。「開悟」是鈴木大拙禪道的核心,而他的作品會引人入勝,這個眩目的觀念居功不少。但在鈴木俊隆的這本書裡,「開悟」...
作者序
出版緣起
一個完全自由的人
對鈴木禪師的弟子而言,這本書就是鈴木禪師的心──但不是他的一般心或是人格心,而是他的禪心。這心是他師父玉潤祖溫大和尚的心,是道元禪師的心,也是自佛陀以降全部真實或虛構的祖師、和尚,以及居士的心。它也是佛陀本人的心,是禪修的心。
但是,對大部分讀者而言,這本書則是一位禪師如何講禪和教禪的榜樣。這是一部指導人們如何修行的書,其中也說明了何謂禪生活,以及禪修是以何種態度和了解為前提等等。它鼓勵讀者去實現自己的真實本性、自己的禪心。
◎何謂「禪心」?
禪心是禪門老師常用的謎樣字眼之一,他們用這字眼來提醒弟子們跳出文字障礙,刺激弟子對自己的心和自身的存在產生驚奇。這也是所有禪訓練的目的──讓你產生驚奇,迫使你用你本性最深邃的表現來回答此一驚奇。
這本書(編按:指英文版)封面上的毛筆字寫的是「如來」二字。如來是佛陀的十種名號之一,意思是說,「他已完成佛道,從真如而來,就是真如、如實、實相、空性,完全的悟道者。」真如(或說是「空性」)乃是一個佛可以示現的基本憑藉。真如就是禪心。當鈴木禪師用筆尖已磨損、分叉的毛筆寫下這兩個字時,他說︰「我要用它來表現『如來』是整個世界的身體。」
◎何謂「初心」?
禪修的心應該始終是一顆初心(初學者的心)。那個質樸無知的第一探問(「我是誰?」)有必要貫徹整個禪修的歷程。
初學者的心是空空如也的,不像老手的心那樣飽受各種習性的羈絆。他們隨時準備好去接受、去懷疑、去對所有的可能性敞開,只有這樣的心能如實看待萬物的本然面貌,一步接著一步前進,然後在一閃念中證悟到萬物的原初本性。
這種禪心的修行全書遍處可見。這本書的每一章節都直接或間接地碰觸到這個問題──如何才能在修行生活和日常生活中保持初心?這是一種古老的教學法,利用的中介是最簡單的語言和日常生活的情境。它的精神是,學禪的人應該自己教育自己。
初心是道元禪師愛用的詞語。書頁上隨處可見的兩個毛筆字:「初心」,也是出自鈴木禪師的手筆。書法的禪道注重坦率簡樸,較不在意技巧或美觀,寫書法時應該像個初學者那樣,全神貫注去寫,儼如是第一次發現你所要寫的東西那般,如此一來,你的全部性情就會表現在書法裡。禪修之道也是如此。
◎將聲音變成文字
將這本書出版的構想源自瑪麗安‧德比(Marian Derby),她是鈴木禪師的入室弟子,也是洛斯拉圖斯(Los Altos) 禪修團的負責人。鈴木禪師固定一或兩星期參加該團的坐禪一次。
禪師坐禪後會講講話,為學員們加油打氣,幫忙解決他們的各種疑難雜症,瑪麗安就把這些對話錄了起來。
不久之後,她就意識到這些對話具有連貫性和系統性,值得整理成書,也可藉此為禪師非凡的精神和教誨留下一個彌足珍貴的記錄。於是,瑪麗安花了幾年時間,把錄音帶的內容整理出來,也就成為本書的第一份初稿。
接著,負責把這份初稿加工的人是鈴木禪師另一位入室弟子──楚蒂‧狄克遜(Trudy Dixon)。她的編輯經驗很豐富,一直以來都負責禪修中心刊物《風鈴》(Wind Bell ) 的編務。
她要把初稿整理和組織成為可以出版的形式。但要編這樣的一本書並不容易,我們在這裡把這些「不容易」的理由一一說明,有助於讀者對這本書能有更好的理解。
鈴木禪師談佛法時,採取的是最困難但也最有說服力的方式──從人們的日常生活情境切入。他還試圖以一些極簡單的語句(例如「喝茶去吧!」)來傳達佛教的整個精神。因此,編輯必須十分警覺,才不會為求文字的清晰或文法的通順而犧牲掉這些別具深意的語句。
另外,如果不是對禪師很熟悉或是曾與他共事過的人,也很容易誤刪掉一些可以表現禪師人格、精力或意志的背景性說明。再來還有重複的部分、一些看似晦澀的語句以及所引用的詩句,編輯一不小心,就會把這些能加深讀者印象的成分給刪掉。事實上,讀者若能仔細閱讀那些看似晦澀或多餘的語句,反而會發現它們其實充滿了啟發性。
◎語言的轉換充滿挑戰
讓編輯在整理稿件的工作上更為困難的是,英語的基本假設完全是二元性的,不像日語歷經了幾百年,而發展出一套可以表現佛教非二元性觀念的語彙。鈴木禪師講話的時候,時而使用日文的思考方式,時而使用英文的思考方式,兩種文化的語彙交替運用,隨心所欲。在他的禪語之中,這兩種語言帶著詩意和哲學氣息而融合在一起了。
然而在轉寫的過程中,停頓、節奏和語氣的強調,這種種可帶給他的話語更深意涵和整合性的語言手段,卻都很容易流失。為此,楚蒂花了好幾個月的時間去跟禪師討論,以求儘可能保留一些原來的用字和味道,與此同時又兼顧到英文
書稿的可讀性。
楚蒂依重點的不同而把本書畫分為三部分:「身與心的修行」、「在修行的道路上」,以及「用心理解」。這樣的區分,分別大致對應於身體、感覺與心靈的部分。她還為每一章節的談話選擇一個標題,並附以一兩句引言(通常都是引自該節的講話內容)。楚蒂的選擇多少有點武斷,但她這樣做,卻可以在標題、引言和談話內容間製造出一種張力,鞭策讀者更深入地思索話語的內容。
書中的談話唯一不是在「洛斯拉圖斯禪修團」發表的,是〈後記〉的部分,這部分是禪修中心搬入舊金山現址時,禪師兩次講話內容的濃縮版。
◎用生命編輯此書
結束這本書的編輯工作沒多久,楚蒂就死於癌症,當時她年僅三十,留下了丈夫麥克和兩個小孩(安妮和威爾)。麥克是位畫家,本書第六十頁(編按:指英文版)的蒼蠅就是他畫的。麥克學禪多年,當他應邀為本書畫些什麼時,他說︰「我畫不出一幅禪畫。除了這幅畫以外,我想不出能畫點什麼。我更絕對畫不出蒲團或蓮花或諸如此類的圖畫,但我卻想到『蒼蠅』這個點子。」
在麥克的畫作上,常可見到一隻現實主義筆觸的蒼蠅。鈴木禪師對青蛙一向讚譽有加,因為青蛙坐著的時候,安靜得好像睡著了一樣,但牠實際上充滿了警覺性,不讓任何一隻從牠面前飛過的昆蟲跑掉。說不定麥克的「蒼蠅」就是在等待這隻「青蛙」。
在編排《禪者的初心》這本書的整個過程,楚蒂全程與我共事,她要求我把最後的整理工作完成,並負責安排及監督印刷和出版事宜。我考慮過幾家出版商,最後選定「魏特山」(Weatherhill)出版公司,它的設計、排版完全符合這本書應有的樣子。稿子付梓前曾經過水野弘元教授過目,他是駒澤大學佛教學部部長,同時也是印度佛教的知名學者。他慨然幫助我們把一些梵文和日文的佛教術語給翻譯出來。
◎禪師的弘法人生
鈴木禪師只會偶一在講話中談起他的過去,以下是我盡己所能,為他的生平組織起來的一份個人簡介。他是玉潤祖溫大和尚的弟子,但另外還有一些師父,最著名的一位就是岸澤惟安禪師。岸澤禪師是道元佛學思想的研究權威,一向強調學佛者對道元思想、禪公案(特別是《碧巖錄》),以及佛經,均應有深入仔細的理解。
鈴木禪師從十二歲那年,即開始跟著父親的一名弟子(也就是玉潤祖溫禪師),展開了禪修的學徒生涯。與師父一起生活若干年後,他先後在駒澤佛教大學和曹洞宗的兩個專修道場(永平寺和總持寺)繼續進行修行和研究。他也在一位臨濟宗禪師座下短期學習過一段時間。
玉潤禪師在鈴木禪師三十歲那年入寂。因此,鈴木禪師儘管年輕,仍必須同時照管兩座寺院,一座是師父的林宗院,另一座是父親的禪寺(他的父親在玉潤禪師入寂後不久也逝世了)。林宗院是一座小禪寺,也是為數約兩百座小寺的總寺。鈴木禪師擔任林宗院住持任內,其中一個主要任務就是要遵照師父遺願,依傳統方式將林宗院加以改建。
在一九三○和四○年代,禪師在林宗院帶領一些討論小組,對日本政府的軍國主義作風和行動提出質疑,這在當時相當罕見。大戰前夕,襌師就有到美國弘法的念頭,當時因為師父堅不應允,他就只好放棄。但在一九五六年和五八年,一位朋友(日本曹洞宗的領導人)兩次力邀他到舊金山,帶領一個當地的日本曹洞宗團體。力邀第三次時,鈴木禪師終於答應前往。
◎將禪帶到西方世界
一九五九年時,五十五歲的鈴木禪師來到了美國。經過好幾次的延後歸程,最後,他決定留在美國弘法。禪師會留下來是因為他發現,美國人都懷有一顆「初心」,對禪很少有既定的成見,相當願意對禪敞開,相信禪能為他們的人生帶來幫助。此外,禪師也發現,美國人問問題的方式可以為禪注入新的生命。
在禪師抵達美國不久,就有好些人圍聚在他身邊,請求跟從他學禪。禪師的回答是︰「我每天大清早都會坐禪,如果你們有興趣,不妨來與我同坐。」自此,追隨鈴木禪師的人與日俱增,至今在加州已有六個據點。
當時他最常待的地方是舊金山市佩奇街(Page Street) 三百號的禪修中心(共有六十名弟子住在那裡,固定來坐禪的人數就更多了),以及位於卡梅爾谷(Carmel Valley )上方的塔撒加拉泉(Tassajara Springs) 的禪山禪修中心。後者是美國的第一座禪寺,固定會有為數大約六十名的學員,從事為期三個月或更長時間的修行。
師徒之間
楚蒂認為,如果能讓讀者明白弟子們對鈴木禪師有何感受,將比任何事情都更能幫助讀者理解禪師在這本書裡的談話。這位師父所給予弟子們的,名副其實就是這些談話內容的一個活生生的例證──證明他所倡導的那些看似不可能實現的目標,真的可以在這一生中體現。
各位若修行得愈深,就愈能明瞭師父的心,並且終究會明白,自己的心和師父的心都是佛心。各位還將會明白,坐禪乃是各位真實本性完美的表現。以下是楚蒂對禪師的兩段讚辭,很能說明禪師與徒弟之間的關係︰
一位禪師就是實現了完全自由的人,而這種完全自由是所有人類的潛能。他無拘無束地生活在他整個存在的豐盈裡。他的意識之流不是我們一般自我中心意識那種固定的重複模式,而是會依實際的當下環境自然地生發出來。結果就是,他的人格表現出各種不凡的素質︰輕快、活力充沛、坦率、簡樸、謙卑、真誠、喜氣洋洋、無比善悟與深不可測的慈悲。他的整個人見證了何謂「活在當下」的真實之中。
但到頭來,讓眾弟子感到困惑、入迷和被深化的,並不是老師的不平凡,而是他的無比平凡。因為他只是他自己,所以得以成為眾弟子的一面鏡子。與他在一起時,我們意識到了自己的優點和缺點,但與此同時又不會感受到他有一絲讚美或責難。在他面前,我們看到了自己的本來面目,也看到了他的各種不平凡只是我們自己的真實本性。當我們學會把本性釋放出來,師徒之間的界線就會消失,消失在佛心展開而成的一道存在與歡愉的深流裡。
理查.貝克(Richard Baker)
京都,1970
(編按:本文中所提的內容編排構想與呈現方式,與中譯本略有出入。)
出版緣起
一個完全自由的人
對鈴木禪師的弟子而言,這本書就是鈴木禪師的心──但不是他的一般心或是人格心,而是他的禪心。這心是他師父玉潤祖溫大和尚的心,是道元禪師的心,也是自佛陀以降全部真實或虛構的祖師、和尚,以及居士的心。它也是佛陀本人的心,是禪修的心。
但是,對大部分讀者而言,這本書則是一位禪師如何講禪和教禪的榜樣。這是一部指導人們如何修行的書,其中也說明了何謂禪生活,以及禪修是以何種態度和了解為前提等等。它鼓勵讀者去實現自己的真實本性、自己的禪心。
◎何謂「禪心」?
禪心是禪門老師常用的謎樣...
目錄
【序】他就在我們之中/休士頓.史密斯
【出版緣起】一個完全自由的人/理查.貝克
【前言】初心
第一部 身與心的修行
1坐禪的姿勢
2我呼吸,所以我存在
3獲得完全的自由
4漣漪就是你的修行
5拔除心中的野草
6一錯再錯也是禪
7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8叩頭、叩頭,再叩頭
9開悟沒啥特別
第二部 在修行的道路上
1千里長軌人生路
2日復一日打坐
3遠離興奮
4要努力,不要驕傲
5不留一絲痕跡
6布施就是無所執著
7避開修行中的錯誤
8吃飯時吃飯,睡覺時睡覺
9研究佛法,研究自己
10於煩惱之中靜坐
11空性使你理解一切
12說你想說的話
13一切作為都算是修行
14對死亡的新體會
第三部 用心理解
1坐禪不是為了開悟
2接受無常
3那一下電閃
4順應自然
5專注於「無」
6當下的一念又一念
7相信「無中生有」
8守一之道
9安靜地坐禪
10佛法是一種體驗
11真正的佛教徒
12心也需要休息
13人人都可以是佛
【後記】 禪心
【序】他就在我們之中/休士頓.史密斯
【出版緣起】一個完全自由的人/理查.貝克
【前言】初心
第一部 身與心的修行
1坐禪的姿勢
2我呼吸,所以我存在
3獲得完全的自由
4漣漪就是你的修行
5拔除心中的野草
6一錯再錯也是禪
7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8叩頭、叩頭,再叩頭
9開悟沒啥特別
第二部 在修行的道路上
1千里長軌人生路
2日復一日打坐
3遠離興奮
4要努力,不要驕傲
5不留一絲痕跡
6布施就是無所執著
7避開修行中的錯誤
8吃飯時吃飯,睡覺時睡覺
9研究佛法,研究自己
10於煩惱之中靜坐
11空性使你理解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