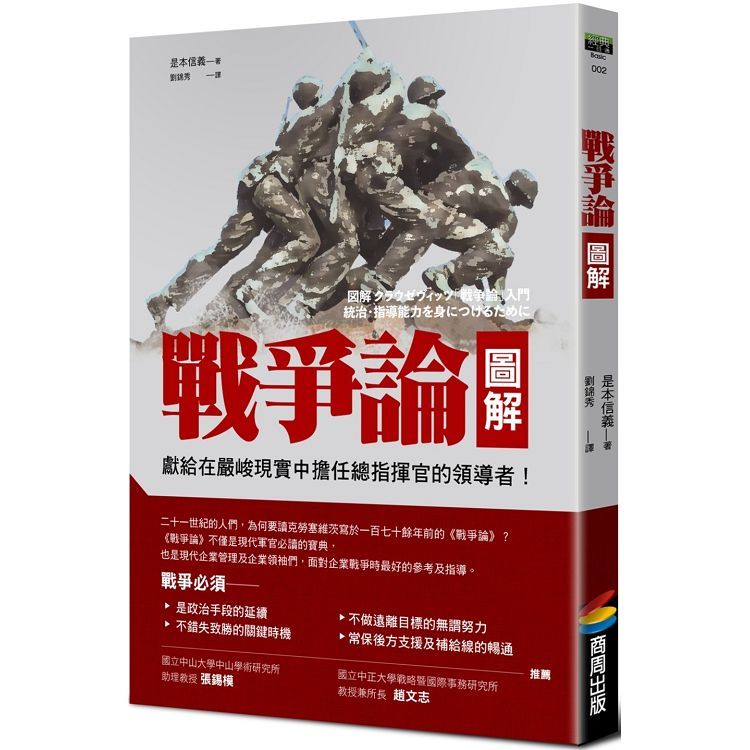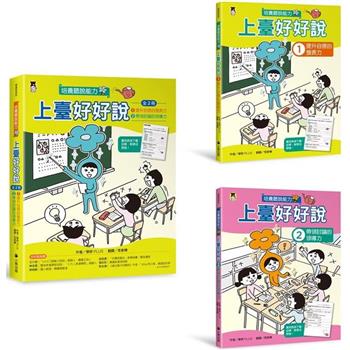導讀 古典的復權
張錫模 國立中山大學中山學術研究所助理教授
●二十一世紀的人們,為何讀克勞塞維茨寫於一百七十餘年前的《戰爭論》?
克勞塞維茨的時代
普魯士軍隊思想家克勞塞維茨(Karl von Clausewitz),一七八〇年生於普魯士馬格德堡附近布格鎭的一個貴族家庭。一七九二年普魯士與奧地利出兵干涉法國革命,克勞塞維茨被送入普魯士軍步兵團充當士官生,自此參加法國大革命引動的一系列歐陸戰爭。一八〇一年進入柏林軍官學校修業,一八一〇年出任柏林軍官學校教官,一八一二年脫離普魯士軍,以中校參謀身分參加俄羅斯帝國沙皇軍隊,在拿破崙遠征莫斯科之役中,從事沙皇軍里加要塞防衛的參謀工作。一八一五年再以普魯士軍參謀長沙恩霍斯特(Gerhard Johann David Scharnhorst,一七五五年至一八一三年)幕僚的身分,參加滑鐵盧之役,戰後出任柏林陸軍軍官學校校長,開始對十八至十九世紀的戰爭經驗進行理論總結,著手寫作《戰爭論》(未完),其後不幸罹患霍亂,一八三一年死去,鉅著在其歿後由遺孀瑪莉出版。
克勞塞維茨生活在軍事事務產生巨大變革的時代,法國大革命與相關戰爭,是克勞塞維茨一生中最重要的軍事經驗。美國革命戰爭與法國大革命前的十七、十八世紀戰爭,是由遮斷敵軍的退路來決定勝負,戰鬥的主力是「君主的軍隊」,且經常是君主的契約雇傭兵。一七六〇年代以降的產業革命所帶動的軍事技術發展,使軍隊的組織與戰鬥方法為之一變。在此一技術變革的背景下,搭配著以人民武裝和游擊戰為中心的美國獨立戰爭,連同法國大革命推翻王權、導入的全國徵兵制,以及人民主權義理的傳播,為軍事事務帶來全新的變革,「君主的軍隊」急速轉變為「國民(民族)的軍隊」(national army)。在此一變革中,大規模兵力與武器動員組織被發展出來,通過拿破崙的歐洲征服,戰爭進入以強大軍力及火力盡量殺傷與破壞敵軍來決定獲勝的新階段。
拿破崙戰爭展示著「國民軍隊」的優勢,迫使歷經嚴酷戰敗經驗的普魯士等國謀求變革。以一八〇七年出任軍制改革委員會主席的夏恩霍爾斯特,以及見習過美國獨立戰爭並在拿破崙戰爭後晉升普魯士陸軍元帥的古納伊謝納烏(August, Graf Neidhardt von Gneisenau,一七八二年至一八三一年)為代表,倡導重建普魯士王國的軍隊,要求將敗戰前的傭兵(「君主的軍隊」)改造為國民皆兵的徵兵制(「國民的軍隊」)。
再者,變革的時代,使軍人充分意識到體系性把握戰爭的必要性,從而體察到「軍事科學」的重要性。特別是,若要進行兵制的根本改革,導入徵兵制,建立「國民的軍隊」,就必須重視專業化的軍事教育與軍隊管理,尤其是對管理部隊之指揮官的教育更為重要。要精化軍官團教育,自然必須有教科書,有體系地、組織性地傳授最低必要限度的知識,並施與應用這些知識的訓練。
此一時代背景,連同自身的經驗,構成克勞塞維茨著書立論的出發點,他的目標是繼承夏恩霍爾斯特和古納伊謝納烏的衣缽,致力將普魯士軍從「君主的軍隊」改造為「國民的軍隊」,並希望為這支新生的「國民軍隊」提供「永遠不變的軍事理論、戰爭理論」。要言之,克勞塞維茨著述《戰爭論》的根本動機,就是為民族國家(nation-state)的「國民軍隊」提出一部體系性的戰爭學「教科書」。就像所有的教科書一樣,《戰爭論》的最大特徵,是對戰爭的所有層面所涉及的現象,進行明快且有體系的記述。
高等軍事學教科書
在其後的歷史過程中,《戰爭論》確實扮演著軍事學教科書的角色。普魯士王國得以在俾斯麥的政治領導下,通過對奧地利、丹麥與法國三次戰爭而成長為德意志帝國(一八七一年)的關鍵,是普魯士陸軍當時稱霸歐洲的戰力;普魯士陸軍戰力的中軸,是普魯士參謀本部的力量;參謀本部的力量,來自(老)毛奇元帥(Helmuth, Graf von Moltke,一八〇〇至一八九一年)排除所有障礙而達成的建設成果——他要求參謀本部在平時發揮著兩種機能:研擬戰時的作戰計劃(含動員計劃),以及給予第一線指揮官當時世界最高水準的軍事科學之理論武裝,亦即扮演著「軍隊之頭腦」,以及軍隊指揮官「養成學校」等雙重功能。在整建參謀本部的過程中,毛奇元帥指導方針的基準,就是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因此,在實踐意義上,《戰爭論》是德意志帝國武裝力量的思想靈魂。
十九世紀後半,《戰爭論》已有英、法、義(大利)、俄等多國譯本,漸次成為當時歐洲列強共通的「高等軍事學教科書」。
作為軍官團的「高等軍事學教科書」,《戰爭論》分為八篇:第一篇「戰爭的性質」,第二篇「論戰爭的理論」,第三篇「戰略通論」,第四篇「戰鬥」、第五篇「戰鬥力(軍隊)」,第六篇「防禦」,第七篇「攻擊」,第八篇「戰爭計劃」,其中篇幅份量最多的是第六篇。
《戰爭論》是未完成的著作,但對戰爭的定義很明快:「戰爭是政治的延續」。這個命題經常被引用與推崇,但其原意也經常被誤解——這個命題的關鍵字,德文原文Politik,具有雙重含義,即政治(Politics)與政策(Policy)。一方面,政策一詞,用來描繪一個理性過程,目標、方法與資源之有意識連結的過程。另一方面,政治則屬於人類社會存在的領域,而非科學或藝術的領域;在本質上,政治總帶有互動的屬性,政治事件與結果,很少是參賽者單方面意圖的產物,而是相互競爭的個人與團體互動、偶然性、摩擦與大眾情感等相互糾結的結果,個別人物或團體基於理性計算的互動,經常造成全體非理性的支出。
因此,克勞塞維茨著名的命題——「戰爭是政治/政策的延續」,不僅是在說明戰爭的有意識行動(如戰略),應是理性計算與政策的延長,同時也在強調,戰爭不可避免地產生而存在於混亂的、不可預測的政治領域之中。
這種對戰爭、政治與政策的思考,充分反映出克勞塞維茨的辯證思維——黑格爾式的唯心辯證思維。在這層意義上,《戰爭論》是黑格爾哲學與拿破崙戰法在克勞塞維茨思想上的綜合產物。
因此,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觀,帶有強烈的辯證思維,用當代賽局理論的術語來說,即帶有嚴整的「互動決策」思維:「在像戰爭這樣危險的事情中,由仁慈而產生的這種錯誤思想,正是最有害的」;「必須看到,由於厭惡暴力而忽視其性質的作法,毫無益處,甚至是錯誤的」(第一篇第一章第三節),言簡意賅,明快地打破「非武裝中立論」或「非武裝和平論」的流俗迷思。
要求從戰爭的內在運動規律而非倫理上的好惡觀點來理解戰爭,使克勞塞維茨進一步提出著名的「弔詭式三位一體」(paradoxical trinity)——有時也被譯成「神奇的三位一體」(wonderful trinity):
「作為一種總體的現象,其支配性趨勢總是使戰爭成為弔詭的三位一體——由被視為盲目的自然力量之原生的暴力、仇恨與敵意;由在其中創造性精神自由發揮的意外性機會與機率之戲劇;以及由作為一種政策工具之屈從因素,僅受理性所支配這三者所構成。這三個側面的第一點,主要牽涉到人民;第二是指揮官及其軍隊;而第三則是政府」(第一篇第一章第廿八節)。
換言之,在克勞塞維茨眼中,戰爭由三大要素所支配:第一是大眾的感情,這是戰爭的心理能源(psychological energy)之所在;第二是在戰場上圍繞著軍隊的「戰爭之霧」(fog of war)——即「偶然與或然率」(chance and probability),「戰爭之霧」是武裝鬥爭的物理脈絡(physical context of armed struggle),標誌出戰爭的動態性格;第三是政府為了其本身的政治目的,將理性施加於戰爭之上的企圖。「這三種傾向像三條不同的規律,深藏在戰爭的性質之中」(同上)。
據此,克勞塞維茨闡述戰爭的基本作用。首先,「戰爭是一種暴力行為,而暴力的使用是沒有限度的。因此,交戰的每一方都使對方不得不像自己那樣地使用暴力,這就產生一種交互作用,從概念上來說,這種交互作用必然會導致極端」。此一暴力衝突升高的運動規律,稱為「第一交互作用」(第一篇第一章第四節)。
其次,「使敵人無力抵抗是戰爭行為的目標……如果要以戰爭行為迫使敵人服從我們的意志,就必須使敵人真正無力抵抗或陷入勢將無力抵抗的地步。由此可以得出結論:解除敵人武裝或者打垮敵人,不論說法如何,必然是戰爭行為的目標。……我們要打垮敵人,敵人同樣也要打跨我們,這是第二種交互作用」(同上)。
再者,「想要打垮敵人,我們就必須根據敵人的抵抗力來決定應該使用多大的力量。敵人的抵抗力等於現有資材的多寡與意志力的強弱。現有資材的多寡是可以確定的,因為它有數量可做根據;意志力的強弱卻很難確定,只能根據戰爭動機的強弱做概略的估計。假如我們能用這種方法大體上估計出敵人的抵抗力,那麼我們也就可以據此決定自己應該使用多大力量,或是加大力量以造成優勢,或是在力所不及的情況下,盡可能地增強我們的力量。但是敵人也會這樣做。這又是一個相互間的競爭,從純概念上講,它又必然會趨向極端。這就是我們遇到的第三種交互作用和第三種極端」(第一篇第一章第五節)。
根據這些原理分析,克勞塞維茨進一步申論戰爭的唯一手段是戰鬥,從而展開第二篇以下的討論。第二篇「論戰爭的理論」共有六章,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一章(「戰爭術的區分」),界定戰爭術為「在戰鬥中運用擁有武器裝備的戰鬥力的技術。在這層意義上的戰爭術,稱為戰爭指導最為恰當;而廣義的戰爭術,當然還包括一切為戰爭而存在的活動,也就是包括建立軍隊的全部工作——」。
這就點出了,遂行戰爭的理論研究,不僅必須包含戰略、戰術與軍隊本身,而且必須涵蓋深受一國人口、資源、經濟力、政治與社會等因素所影響的「軍事行政」層面。換言之,若不能充分掌握軍隊以外的人口、經濟、社會、政治等層面的變化並予以活用,便不可能實現該國最佳的「軍事行政制度」(臺灣的軍官教育,欠缺的就是這種理解臺灣社會、人口、經濟、政治的廣闊視野)。
第三篇以下迄第七篇,共五篇,是戰爭論的主要內容。在作為「高等軍事學教科書」的十九世紀下半葉,《戰爭論》第三至七共五篇,是當時「軍事科學」的最先進著作,也是當時歐陸各國軍官團學習的重點。然而,對於當代讀者而言,這五篇可能稍嫌難以理解,且許多見解受限於作者執筆的時代,無論從政治體制或軍事技術等角度來看,都未必適用於今日的戰爭研究。
正是在這層意義上,《戰爭論》的角色,逐漸從「教科書」轉變為「古典」,而「古典」總有其限制。
《戰爭論》的影響與限制
《戰爭論》從「教科書」到「古典」的轉變過程,可以從這本鉅著在二十世紀的影響歷程中清晰看出。一般的論述宣稱,《戰爭論》是「西方的兵學聖經」,對「西方」的戰略思想與作為產生深遠的影響。這種說法誠屬泛泛。「西方」本身就是個模糊的概念,而對今日「西方」的第一代表國美國而言,《戰爭論》的影響不應被高估——放置在小羅斯福總統書案上的唯一一部兵書,並非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而是馬漢的《海軍力對歷史的影響:一六六〇年至一七八三年》(初版一八九〇年,即俗稱的《海權論》)。在實踐上,支配美國國防戰略的中心思想,是馬漢,而不是克勞塞維茨。甚至,米契爾的《空權論》,或是二次戰後美國複雜多歧的核武戰略思維,對美國軍事思想的影響,也都勝過《戰爭論》。
事實上,正如同黑格爾的國家主義哲學影響最力的區域,是「東方」而非「西方」,受到《戰爭論》影響最大的區域,與其說是「西方」,毋寧說是「東方」,尤其是蘇聯/俄羅斯與中國。
列寧一生最熟讀的軍事書籍,就是《戰爭論》,他在一九一五年閱讀此書時所寫下的眉批與筆記,足以構成另一本專書。列寧的整套軍事思想,核心源自克勞塞維茨,差別只在於:第一,列寧追隨批判性繼承黑格爾思想的馬克思唯物辯證,而克勞塞維茨則是黑格爾式的唯心辯證;第二,列寧將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觀擴大為政治觀,他以戰爭的觀點來看待政治,社會主義革命被他界定為「終結所有戰爭的戰爭」。據此,第三,列寧對克勞塞維茨的「三位一體」進行修改式繼承,將人民/民族改為「階級」,民族國家的政府,則被改為「(共產)黨」。
通過列寧的修改式繼承,《戰爭論》的見解成為蘇聯政治體系與軍事思想的根本基礎,並通過蘇聯的示範作用,影響著中國共產黨人的政治體制思維與軍事思想。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根本意義是在打造一部戰爭經濟機器,而「黨指揮槍」的思想,迄今仍有力地殘留在中國共產黨人的大腦中。因此,在歷史意義上,《戰爭論》對「東方」的影響力,其實遠勝過對「西方」的影響力。
此一比較在歷史上饒富意義,因為二十世紀軍事技術與思想的先進區域,是「西方」而不是「東方」:空權與核武戰略的登場,都是二十世紀的「西方」產物。
更重要的是,空軍的最初運用出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核武的運用則出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這兩場戰爭標誌出人類進入「總力戰」(Total War)的時代。
美國南北戰爭與一九〇四年爆發的日俄戰爭,是人類史上「總力戰」的先驅,而第一次世界大戰是人類戰爭「總力戰」的代表。戰爭發展到此一階段,決勝關鍵已非純粹軍事力,而是國力所有要素(國土的戰略地勢、人口、政府統治力、國民士氣、國民素質、產業•經濟力、外交力、軍事力)的總合。
當戰爭進入「總體國力決定勝負」的階段時,「勝利」必須通過打擊(包括使敵人遭受打擊的恐懼感)來完成。打擊由火力與衝擊力(突擊)來進行。若在現實上難以打擊敵人,也可以設法使其陷入會遭受打擊的不利態勢。若能做到這一點,敵人通常會因為恐懼感而敗走。若是必須通過戰鬥才能獲得勝利,則必須使我方的損害比率較敵方的損害率為小,因為戰爭通常不會只打一次戰鬥就宣告結束。
如此,持續性成為戰爭的特性。每一次戰鬥,都會蒙受一定損害,而損害的回復需要時間與勞力。因此,因為進行戰鬥而有所損害的兩軍,都會努力地要求己方較敵方更快且更強地做到「戰鬥力的回復」。如此,兩軍其實是在進行著忍受被消耗與搶先回復戰鬥力的競賽。在這場競賽中失敗的一方,最終將在整場戰爭中敗北。簡言之,戰爭的最終性質是「消耗戰」。
「消耗戰」必然是「持久戰」,而且必然要求火力集中與尋求主力決戰,期使敵軍主要戰鬥部隊的戰鬥力在決定性戰鬥中陷入無法回復的狀態。只要能在此類「決定性戰鬥」(如第二次世界大戰太平洋戰爭中的中途島海戰戰役)獲勝,戰爭的態勢便可被確立,據此贏得最終勝利。
總力戰、消耗戰、持久戰、主力決戰、集中打擊,構成過去兩百年來所有戰爭理論的教義基礎。總力戰的現實,要求著空權論的登場,也要求著核武戰略的登場,甚至要求著「太空權論」的登場。戰爭的型態、性質與思想變化如此巨大,《戰爭論》的「教科書」角色自然無可避免地下降,漸次轉變為頗負盛名但很少人仔細研讀的「古典」。
《戰爭論》的復權
意義深長的是,若說《戰爭論》的角色,因「總力戰」時代的到來而從「教科書」轉為「古典」,那麼,當人類漸次告別「總力戰」時代之際,作為古典的《戰爭論》,便開始展現出「古典復權」的力量。
一九九〇年代加速發展的當代軍事事務革命(RMA),深刻地改變著戰爭的本質。此一革命的起點,是來自電腦計算能力加速發展為基礎的資訊革命(information revolution)。資訊型軍事革命的核心,與其說是新登場的精密打擊武器的出現(用什麼打),毋寧說是「怎麼運用新軍事技術與武器?」(戰法/戰鬥綱領),以及「什麼樣的軍事組織最適合未來的戰爭?」(戰鬥組織與編制的改變)。
一九九一年波灣戰爭,活用資訊科技(IT)與精密誘導技術的武器登場,戰鬥力因此倍增,但美軍只是針對傳統的戰法與組織編制略加調整而已。然則,一九九九年三月的柯索伏戰爭,產生出全新型態的軍隊運用法與編制/組織,戰鬥型態也跟著完全改觀。例如,在該次戰爭中,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軍一方面大大地活用電腦控制兵器(cyber weapons)與媒體來混淆南斯拉夫軍,另一方面則大量使用精密誘導兵器與非殺傷性武器來抑制雙方軍隊與民間設施的物理性損害。二〇〇一年十月的阿富汗戰爭,以及二〇〇三年三月發動的美國對伊拉克之戰,進一步加速此一趨勢。
此一武器/技術、戰法、戰鬥組織/編制的三位一體的改變,意味著軍事事務革命產生的新軍種——RMA軍的運用原則,已非傳統的教義。新的關鍵原則是「要害打擊」(打擊敵方之神經中樞等要害以促使其喪失戰鬥機能而非大量死亡)與「同步打擊」(同時間不容髮地攻擊複數目標以促使敵方措手不及而無力回應)。
「要害打擊」與「同步打擊」的出現,反映著資訊化社會的特質,即「情報的共有」、「精確」(精密與正確)、「速度」、以及「對人命敏感」。將這兩大原則適用在真實的戰場上,將使迄今為止的戰爭型態出現巨變。
第一,傳統的「火力戰」與「機動戰」漸次讓位予「資訊戰」,後者對勝負的影響力漸次高於前者。第二,「平面次元」與「空間次元」的戰鬥之外,新增的「電腦控制/電子次元」(cyber dimension)與「時間次元」戰鬥越來越重要。第三,「前線陣地」對戰鬥的重要性漸次荒廢。第四,「攻擊」遠較「防禦」來得有利。
如此,戰爭型態的改變,催化著戰爭性質出現革命性的變化,百年來被奉為圭臬的總力戰與消耗戰,迅速地讓位給RMA軍的「麻痺戰」。「消耗戰」是揭櫫殺傷與破壞敵軍主力部隊為目標的戰法,而「麻痺戰」之目標則是使對手的指揮統制等機能陷入無能,藉此造成敵軍主力戰鬥部隊的機能麻痺與癱瘓,且因其僅攻要害,不傷全體的特性,因而又有「不對稱戰爭」(asymmetric warfare)之稱。
這就促成克勞塞維茨《戰爭論》的復權。作為軍事教科書,《戰爭論》第一、二篇闡述的「戰爭是政治的延續」,已在核武時代出現嚴重的限制(核武戰就是人類/政治的終結),而第三篇至第七篇的戰略、戰術、防禦、攻擊等討論,也明顯難以因應「總力戰」時代的戰爭型態。然而,清晰論述政治目的與戰爭目標及相應作為的第八篇「戰爭計劃」,卻一貫地通過近兩百年的漫長考驗,展示著恆久智慧的價值。
新軍事事務革命要求著戰爭從「總力戰」走向「麻痺戰」,而「麻痺戰」的性質,要求著武器系統、軍事組織與戰鬥綱領的新思維。在根本意義上,要求著新的戰爭計劃。在所有戰爭計劃的背後,都存在著戰爭目標。戰爭計劃的任務在運用適當的方法並搭配著擁有的資源來達成戰爭目標。戰爭目標決定戰爭計劃,戰爭計劃決定戰鬥行為,並據此決定戰爭的結果。進一步,最好的戰爭計劃就是那些目標最單純的計劃,也就是那些能夠確認克勞塞維茨所謂「單一重心」(single center of gravity),藉以避免導致兵力與戰鬥努力分散化的戰爭計劃。戰爭目標越多樣,戰爭的進行就越困難,戰爭計劃之間彼此矛盾而自我敗北的機率就越高。
正如同物理學(機械力學)中的重心一樣,用足夠的力量攻擊重心,可導致目標物體失衡及倒塌。因此,重心不是力量的來源,而是一個平衡的要素。如果能夠在戰爭中讓敵方失衡,就可以快速取得勝利。這意味著,在根本意義上,界定重心之所在,成為戰爭計劃的關鍵。在「麻痺戰」或「不對稱戰爭」的時代,標定與破壞敵人的重心,更成為戰爭中最關鍵的事務。
進一步,如果人們願意將他們對戰爭的視野放入當代社會經濟來考察,就會更明白《戰爭論》第二篇有關「軍事行政」的洞見。
這就是我們這些生活在二十一世紀的人們,為何閱讀克勞塞維茨《戰爭論》這部寫於一百七十餘年前舊著的因由——《戰爭論》的時代已經終結,其中大半篇幅並未經得起「總力戰」時代的嚴峻考驗,但圍繞著政治目的、戰爭目標、重心、軍事行政及其他關鍵概念與思維,《戰爭論》不僅通過了二十世紀「總力戰」的近百年考驗,而且在新軍事事務革命下的「麻痺戰」時代,再度展現著持之非強但來之無窮的思想力量。
很自然地,對此一脈絡的理解,將促生出一種批判性的閱讀——《戰爭論》作為軍事學教科書的第三篇至第七篇,當代人可以省略,但充滿恆久洞見的第一、二、八篇,卻仍值得當代人咀嚼品味。
| FindBook |
有 10 項符合
戰爭論圖解(改版)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1 則評論 |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182 |
社會科學 |
$ 182 |
歷史 |
$ 195 |
概論 |
$ 205 |
Social Sciences |
$ 221 |
社會人文 |
$ 221 |
戰略/戰役 |
$ 229 |
中文書 |
$ 229 |
軍事 |
$ 234 |
戰略/戰役 |
$ 234 |
社會人文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圖書名稱:戰爭論圖解(改版)
《戰爭論》是領導者欲增進統御、指導能力的最佳選擇,
也是企業領袖們面對企業戰爭時最好的參考指南。
《戰爭論》與《孫子兵法》並稱為人類歷史上兩大兵法書,
更是培育出眾多知名將領與商界菁英----西點軍校的必讀書籍。
想在企業戰爭中搶得致勝先機,必須知道的戰略法則!
1. 何謂「戰爭」?為遂行國家意義的政治手段
2. 如何以理論說明「戰爭」?基本三要素為戰略、戰術、後勤
3. 何謂「戰略」?戰略上的失敗,無法靠戰術挽回
4. 何謂「戰鬥」?洞穿勝敗的分界點非常重要
5. 什麼決定「戰鬥力」?戰鬥力≠絶對兵力
6. 「守勢」(防禦)和「攻勢」何者有利?攻撃時防禦亦不可缺
7. 為什麼「戰爭計劃」非常重要?因為可讓政略和戰略做有機結合
戰略:作戰的策略,因應戰爭目的所做的戰術「構成案」。
戰術:遂行個人的戰鬥,爭取達成目標或致勝的方術。
後方支援(logistics):後勤。包括物資的補給、醫療、造橋修路、教育等等。
戰爭必須──
》是政治手段的延續
》不做遠離目標的無謂努力
》不錯失致勝的關鍵時機
》常保後方支援及補給線的暢通
★本書特色
以圖解方式,將經典名著《戰爭論》的內容拆解,以易讀好懂的方式呈現給讀者。
內容精準扼要,是吸納經典知識的最好途徑,適合各界想要理解領導素質的讀者閱讀。
★專業推薦
國立中山大學中山學術研究所助理教授 張錫模(導讀)
國立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趙文志
(依姓氏筆畫排序)
「這部寫於一百七十餘年前的《戰爭論》,不僅經得起二十世紀『總力戰』的近百年考驗,
在新軍事事務革命下的『麻痺戰』時代,再度展現出持之非強但來之無窮的思想力量。」
──國立中山大學中山學術研究所助理教授 張錫模
作者簡介:
是本信義
1936年出生於福岡。1956年自防衛大學畢業之後,即進入海上自衛隊服役。主要都是擔任艦隊勤務。曾任護衛艦艦長、護衛隊司令、艦隊司令部作戰幕僚、總監部防衛部長等職。1991年自海上自衛隊除役。除役後轉往和國安相關企業服務,現為一專職作家。撰寫過無數有關戰爭史、國際政治、經營管理、航海技術(seamanship)、武術、格鬥技等等的論文。著有《羅馬帝國的末裔》(行研)《戰史名言》(東洋經濟新報社)《戰史名言(文庫版)》(PHP研究所)《學習圖解「孫子兵法」的書(中經出版)《日本海軍為什麼戰敗?》(光人社)《圖解克勞塞維茨「戰爭論」很有趣!》(中經出版)。
相關著作:《君王論圖解(改版)》
譯者簡介:
劉錦秀
東吳大學日文系畢。曾任職出版社國際版權部經理。譯有《非連續時代》、《思考的技術》、《明日的記憶》、《成語經濟學》(商周出版)等數十本書。
推薦序
導讀 古典的復權
張錫模 國立中山大學中山學術研究所助理教授
●二十一世紀的人們,為何讀克勞塞維茨寫於一百七十餘年前的《戰爭論》?
克勞塞維茨的時代
普魯士軍隊思想家克勞塞維茨(Karl von Clausewitz),一七八〇年生於普魯士馬格德堡附近布格鎭的一個貴族家庭。一七九二年普魯士與奧地利出兵干涉法國革命,克勞塞維茨被送入普魯士軍步兵團充當士官生,自此參加法國大革命引動的一系列歐陸戰爭。一八〇一年進入柏林軍官學校修業,一八一〇年出任柏林軍官學校教官,一八一二年脫離普魯士軍,以中校參謀身分參加俄羅斯帝國沙皇軍...
張錫模 國立中山大學中山學術研究所助理教授
●二十一世紀的人們,為何讀克勞塞維茨寫於一百七十餘年前的《戰爭論》?
克勞塞維茨的時代
普魯士軍隊思想家克勞塞維茨(Karl von Clausewitz),一七八〇年生於普魯士馬格德堡附近布格鎭的一個貴族家庭。一七九二年普魯士與奧地利出兵干涉法國革命,克勞塞維茨被送入普魯士軍步兵團充當士官生,自此參加法國大革命引動的一系列歐陸戰爭。一八〇一年進入柏林軍官學校修業,一八一〇年出任柏林軍官學校教官,一八一二年脫離普魯士軍,以中校參謀身分參加俄羅斯帝國沙皇軍...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導讀 古典的復權 張錫模
序章 對《戰爭論》的基本認識
1 克勞塞維茨
理論是觀察而非口號
2 不斷上演戰爭的戲碼
腓特烈一世成為普魯士國王
第1章 何謂「戰爭」?
1 戰爭就是暴力的行為
殘酷的和解
迦太基的無妄之災
最可恥的戰爭
2 政治支配戰爭
冷戰時代的軍備擴張競爭
冷戰因利害關係而終結
3 戰爭不會有兩個目的
在「擊滅敵軍」及「土地占領」中二擇一
採取愚蠢作戰策略的德軍
意見不一造成德軍戰敗
4 戰爭是以其他的手段延續政治
織田信長的政治手段——將戰爭和政治分開
截斷重重包圍網
一...
序章 對《戰爭論》的基本認識
1 克勞塞維茨
理論是觀察而非口號
2 不斷上演戰爭的戲碼
腓特烈一世成為普魯士國王
第1章 何謂「戰爭」?
1 戰爭就是暴力的行為
殘酷的和解
迦太基的無妄之災
最可恥的戰爭
2 政治支配戰爭
冷戰時代的軍備擴張競爭
冷戰因利害關係而終結
3 戰爭不會有兩個目的
在「擊滅敵軍」及「土地占領」中二擇一
採取愚蠢作戰策略的德軍
意見不一造成德軍戰敗
4 戰爭是以其他的手段延續政治
織田信長的政治手段——將戰爭和政治分開
截斷重重包圍網
一...
顯示全部內容
圖書評論 - 評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