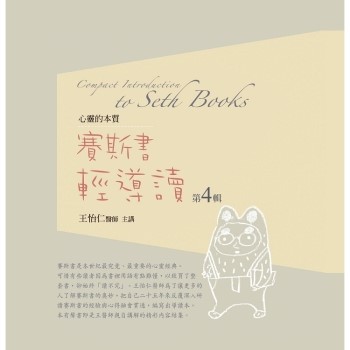■序
二○一三年二月二十八日 星期四
深夜十一點四十三分
香川縣S市、S北派出所
──二十四分鐘。
太過短促的短暫時間。
身穿老舊外套的男人屈身沉默一下之後,補充說明說:「我說完了。」
隔著桌子坐在對面的年輕警官對男人說:「最後請你再說一遍姓名和出生年月日。」
「若田久志,四十五歲。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四日生,原本是每關報社的記者。」
「──謝謝。」
身穿制服的警官這麼說著,停下錄音機,液晶螢幕上浮現一行數字【00:25:21】。
派出所一隅被螢光燈照到白得發亮,深夜的小派出所只有一位警官,空蕩蕩的樓層貼滿呼籲防止犯罪的海報。
北風咯嗒咯嗒搖晃入口的窗框。當風一停下來,人口密度低的鄉下就連車子的聲響都聽不到。
火爐上的熱水煮沸發出咻咻聲,從黯淡鋁水壺冒出來的水蒸氣好像快要融化房間的輪廓了。
花費的時間甚至短到不需要休息。
會花上四天,還是五天呢?
要說出若田埋藏心中長達十五年的秘密,總覺得需要長到令人難以想像的時間,實際上花費的時間卻不超過三十分鐘。不是說得不夠多,而是若田知道的事實就這麼多,無論再怎麼擠也擠不出來了。
「……」
若田說完以後稍微陷入恍惚。把一直用驚人壓力持續佔領內心的東西發洩出來,由於作嘔的衝擊而感到虛脫。
並非嘔吐物之巨大所導致。
看似會冒出海洋,或是嘔吐出足以撕裂喉嚨般巨大雪球一樣的團塊。和這樣的想像正好相反,拚死說出口的事實不過是司空見慣的小事罷了。
對於這份短促最吃驚的正是若田自己。難道我任意在心中培養妄想了嗎?忘記警官人在眼前的事情,若田詢問自己。闔上雙眼,回溯方才向警官坦白說出的內容,心想並非如此。
那確實是犯罪沒錯。
但遙遠的感情記憶卻比親眼所見的事實更加激烈。若田沒有方法可以傳達,這份沉重壓力等同於若田十五年來的人生。
若田之所以感到困惑,是因為若田心中記憶之巨大和被吸入小錄音機中的事實,在質量上的分歧。對於一說出口就彷彿融化在空氣中消失的情報量落差感到困惑。
面對光是茫然默不作聲的若田,警官投以憐憫的視線。
「謝謝你說出來,若田先生。你身為事件的關係人,我想今後還會再找你問話」
警官抬頭仰望嵌上日期的壁鐘,安慰說「雖然趕不上了」。
二○一三年二月二十八日,二十三點四十六分。
事到如今,若田並不是想逮捕「他們」。因為若田當時確信和他們永遠訣別,確實感覺到應該不會有任何人遭到逮捕,或是藉由他人之手而真相大白。那又為什麼要在一切時效成立的現在過來做出這種告白呢?
既非受到罪惡意識的驅使,也非前來懺悔。
若田認為,我是來做結束的。
告知真相,宣洩密封於心中的重量,向作為現實窗口的警方傳達「結束了」,想將「他們」從過去解放開來。
電流在腦髓深處發出聲響。
從那一天起連一時片刻都不曾消失,低沉轟鳴的高壓電流侵犯空氣的聲音。無論如何試圖活在當下,瞬間就把若田拉回那一天,如油般滲透鼓膜的聲響。
或許是若田自己想要從這道聲響之中獲得解放吧。
心裡這麼想的時候。
──啊,這就是我的病的本質。
突然想通了,若田闔上雙眼。
真相和心中空虛的質量分歧;響個不停的電壓聲響。
若田的病無論接受什麼檢查都查不出來,並非神經外科、精神內科、教堂,只有透過在事務性接受事實申告的警方桌前告白才能治癒。
警官在桌子對面打電話到某處。
他在詢問要怎麼處理若田,他的嗓音聽來只比醉鬼麻煩一點的程度。看來武裝警車和搜查一課不會突然蜂擁而至的樣子。
我的病治不好了嗎?
若田朝著變得什麼都吸不進去的錄音機,彷彿訴說病情般發出不安的嗓音。
「……我的二月少了三天。」
果然在化為聲音的瞬間,被記憶的低周波消滅,變得像是在自言自語。
警官只有一次用視線一隅看了若田一眼。
若田愣愣地把意識拋在頭蓋骨裡電磁波低沉起伏的迴響中,側耳傾聽暴風的聲響。在被北風吹得咯嗒咯嗒不停晃動的玻璃窗彼端,看得到白色燈光。
寫著「S北派出所」的招牌浮現。
偶而有白色的東西橫穿從海上吹來的風。
總覺得每年下沒幾次的雪,在這十五年間變得更少了。
那一天也是這樣的夜晚。
在強烈的海風中,參雜雪花的電壓聲響完全壟罩夜空,像這樣的夜晚。
| FindBook |
有 2 項符合
二月病的圖書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二月病
高中同學兼好友的蒼司突然向千夏告白,千夏選擇比戀人更能長久相伴的朋友關係,委婉地拒絕蒼司。
隔天,蒼司曠課沒來上學,擔心的千夏打電話到蒼司家裡和他手機聯絡,
但接電話的不知為何卻是個陌生男人,男人說著根本聽不懂的異國語言;
感到不安的千夏來到蒼司家登門造訪,卻不見他的身影──改變他們命運的懸疑愛情故事。
本書特色:
插畫家黑沢要的插圖讓本書更加出色
以倒述法做為本書開頭,以一個長達十五年深藏心中的祕密,在向警察敘述時,將兩位主角熾熱且執著、純真且坦率的愛戀在故事中完整表達出來,深深打動人心。
作者簡介:
作者: 尾上与一
日本BL小說作家。
台灣出版的作品有《二月病》。
繪者: 黑沢要
日本插畫家。
台灣出版的作品有《二月病》。
TOP
章節試閱
■序
二○一三年二月二十八日 星期四
深夜十一點四十三分
香川縣S市、S北派出所
──二十四分鐘。
太過短促的短暫時間。
身穿老舊外套的男人屈身沉默一下之後,補充說明說:「我說完了。」
隔著桌子坐在對面的年輕警官對男人說:「最後請你再說一遍姓名和出生年月日。」
「若田久志,四十五歲。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四日生,原本是每關報社的記者。」
「──謝謝。」
身穿制服的警官這麼說著,停下錄音機,液晶螢幕上浮現一行數字【00:25:21】。
派出所一隅被螢光燈照到白得發亮,深夜的小派出所只有一位警官,空蕩蕩的樓層貼...
二○一三年二月二十八日 星期四
深夜十一點四十三分
香川縣S市、S北派出所
──二十四分鐘。
太過短促的短暫時間。
身穿老舊外套的男人屈身沉默一下之後,補充說明說:「我說完了。」
隔著桌子坐在對面的年輕警官對男人說:「最後請你再說一遍姓名和出生年月日。」
「若田久志,四十五歲。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四日生,原本是每關報社的記者。」
「──謝謝。」
身穿制服的警官這麼說著,停下錄音機,液晶螢幕上浮現一行數字【00:25:21】。
派出所一隅被螢光燈照到白得發亮,深夜的小派出所只有一位警官,空蕩蕩的樓層貼...
»看全部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尾上与一、黒沢要
- 出版社: 青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5-04-15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322頁 開數:32
- 商品尺寸:長:188mm \ 寬:127mm \ 高:17mm
- 類別: 中文書> 漫畫/輕小說> B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