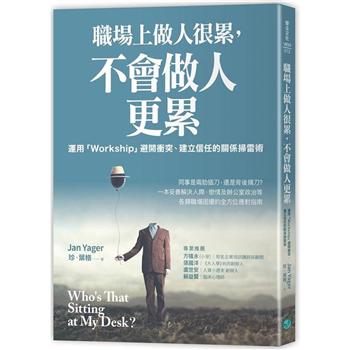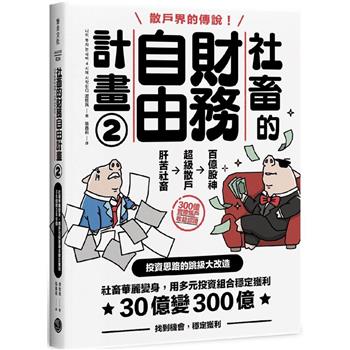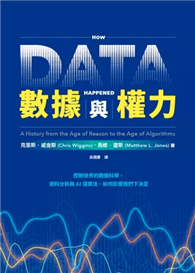※2015年法布爾逝世百年‧珍藏昆蟲詩人法布爾永恆的經典!
※雨果、達爾文、梅特‧林克、羅曼‧羅蘭、羅斯丹、周作人、魯迅、手塚治虫、楊平世、劉克襄等中外名人一致讚譽!
在這些天才式的觀察中,融合熱情與毅力,簡直就是藝術品的傑作,令人感動不已。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羅曼‧羅蘭
法布爾實地的記錄昆蟲的生活現象,本能和習性之不可思議的神妙與愚蒙。……他的敘述,又特別有文藝的趣味,更使他不愧有昆蟲的史詩之稱。
──中國著名學者 周作人
當完整版的【法布爾昆蟲記全集】出現時,我相信,像我提到的狂熱的「昆蟲王」,以及早熟的十七歲少年,恐怕會增加更多吧!
──自然作家 劉克襄
【法布爾昆蟲記全集】第一次讓國人有機會「全覽」法布爾這套鉅作的諸多面相,體驗書中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欣賞優美的用字遣詞,省思深刻的人生態度,並從中更加認識法布爾這位科學家與作者。
──台灣大學昆蟲系名譽教授 楊平世
【閱讀焦點】
★一部涵跨文學與科學領域的百年之作
【法布爾昆蟲記全集】是被譽為「昆蟲學的荷馬」的法布爾耗費四十多年心血完成的名著。書中融合了細膩的自然觀察與法國式的幽默,娓娓道來十九世紀南法的自然人文風情,並以大量翔實的第一手觀察、實驗資料,將紛繁複雜的昆蟲世界,真實生動地呈現。是至今最鉅細靡遺、蘊含哲思的昆蟲觀察經典鉅著,亦是一部涵跨文學與科學領域的百年之作!值得沒讀過的人一讀,更值得讀過的人再讀!
★一部深入探討昆蟲行為奧祕的觀察記錄
在【法布爾昆蟲記全集】中,無論是六隻腳的昆蟲或是八隻腳的蜘蛛,每個對象都耗費法布爾數年到數十年的時間去觀察並實驗。在書中法布爾不厭其煩地交代他的思路和實驗,帶領您融入情景去體驗實驗與觀察結果所呈現的意義。在他仔細有趣的實驗、層層漸進的科學推理;夾敘夾議、生動流暢的敘述中,您不僅可以窺知昆蟲行為的奧秘,更往往會因為那些:糞金龜如何製作出光滑細緻的梨形育兒糞球、蠍子如何兩螯互夾來談情說愛、狩獵蜂如何只將獵物麻醉好讓幼蟲吃到新鮮食等讓人眼睛為之一亮的故事,以及法布爾在觀察昆蟲生命過程時所抒發的哲思理趣,感動得一讀便無法釋手。
★跨越自然與人文,是知識與文學的饗宴
【法布爾昆蟲記全集】並不僅是一部嚴謹的科學紀錄,其在文學上非凡的成就更屢獲諾貝爾文學獎青睞。為了不淪於曲高和寡,法布爾揚棄生冷的科學筆調,以文學家細膩優美的文筆、哲學家的哲思理趣、藝術家的獨特美感、博物學家的知識廣度;為人們鑑照出栩栩如生的昆蟲世界,進而激發人們去親近去了解自然與人文風采的慾望。閱讀【法布爾昆蟲記全集】,無疑是一次智識與靈性的提昇,一場藝術與人文的盛宴,更是一場無與倫比的生命感動。
★完整譯自法文原著,經過學者嚴謹審校
【法布爾昆蟲記全集】目前已被譯成五十種語言版本,國內的版本多半是轉譯,或是節譯、摘譯改編而成。經過學者嚴謹的審訂之後,遠流的【法布爾昆蟲記全集】全套十冊、共四百多萬字,直接譯自法文原著,不加任何改寫,讓您直接感受昆蟲大師的言思哲學,全覽鉅作的諸多面相。更特別收錄法文原著珍貴的昆蟲手繪插圖300餘幅,筆觸精細、栩栩如生,首度展現給台灣讀者!另附有作者、譯者、編者三重注解說明,及昆蟲、人物、地名的中文譯名對照索引表,幫助您更深入理解相關的昆蟲研究,與當時的文化、哲學背景。絕對是華文世界唯一也是最優秀的中文全譯集本。
★一部超跨越領域、超越年齡的不朽傳家經典
在橫跨兩個世紀後,【法布爾昆蟲記全集】依然深深地扣動著全世界讀者的心弦,其影響了許多熱愛自然的讀者走出象牙塔與自然蠻荒對話;喚起對人們對萬物、對人類、對科普、對文學,甚或對鄉土的深刻省思;並繼續在世界各地擔負起對昆蟲行為學的啟蒙角色;因此早已被公認為超越領域、跨越年齡、值得您咀嚼回味,一讀再讀的不朽傳家經典!
【各冊內容簡介】
《法布爾昆蟲記1:高明的殺手》
究竟昆蟲是用怎樣高明的手法讓牠的獵物保有活力,甚至連蝶翅上精細的彩色鱗片都絲毫不損?是靠後天苦練而成?抑或受到本能無意識啟發?且看法布爾如何用漸進的科學推理解開這個謎!此外在本書法布爾也研究蜂的方向感、築巢方法等議題。
《法布爾昆蟲記2:樹莓樁中的居民》
法布爾遷居到荒石園後,總愛在冬日午後造訪於乾枯的莓樹樁安居的昆蟲鄰居們。他透過觀察與實驗,縝密細膩地探討昆蟲孵化本能的議題。此外在本書法布爾也發現到芫菁幼蟲多次變態的現象,並且首次提出「過變態」的概念。
《法布爾昆蟲記3:變換菜單》
「告訴我你吃的是什麼?我就能說出你是哪種人?」在昆蟲世界裡這個法則是否也成立?本書法布爾針對各種昆蟲的進食方式做了詳細的觀察。此外還觀察寄生的蜂、虻與被寄生的蜂類,討論牠們之間的關係、寄生行為與寄生理論。
《法布爾昆蟲記4:蜂類的毒液》
究竟土蜂是如何讓捕獵來當幼蟲食物的獵物保持新鮮?是體內毒液的酸鹼成份在作怪?抑或是取決於牠獵殺獵物時的高度準確性?法布爾針對各種捕獵性昆蟲的毒液與捕獵手法做實驗觀察,此外本書他還討論昆蟲的本能與判斷力。
《法布爾昆蟲記5:螳螂的愛情》
究竟是怎樣的愛情,讓雄螳螂甘心丟了頭,至死才肯放棄擁抱?讓雌螳螂等不及婚禮的結束,就咀嚼起牠的情人?還是,這只是凶殘的天性使然,跟愛情壓根扯不上邊?本書法布爾針對螳螂捕食、交配等習性做了詳細的觀察記錄。並研究聖甲蟲、糞金龜、蟬等昆蟲的生活習性。
《法布爾昆蟲記6:昆蟲的著色》
究竟被譽為潘帕斯的首飾──食糞性甲蟲法那斯,那如寶石般的美貌,是天生麗質?還是後天保養有道?法布爾針對昆蟲著色的議題,對昆蟲進行體色研究,發現牠們那身美麗的衣服,其實說穿只是「尿」的傑作!此外法布爾也研究埋葬蟲、白面螽斯、蝗蟲等昆蟲的生活習性。
《法布爾昆蟲記7:裝死》
究竟是什麼原因使得昆蟲必須具備裝死的防禦巧計?是身處險境時必須耍點詭計?還是柔弱的和平愛好者為了保命不得不為的下策?法布爾對各類昆蟲進行實驗,所得結果卻大異其趣,有的很輕易就進入裝死的境地,有的猶豫不決,有的卻頑固地拒絕裝死。本書法布爾也研究象鼻蟲、金花蟲、大天蠶蛾等昆蟲的習性。
《法布爾昆蟲記8:昆蟲的幾何學》
如果用量角器去測量胡蜂所搭建的六角形蜂房,你會驚訝於牠的計算結果與幾何學最精準的計算結果完全相符!究竟是什麼原因讓這些昆蟲建築師生來就具有幾何學知識,對建築程序無師自通?法布爾針對昆蟲築巢的習性做了詳細的觀察記錄。此外法布爾也研究香樹蚜蟲、閻魔蟲、拿魯波狼蛛等昆蟲的習性。
《法布爾昆蟲記9:圓網蛛的電報線》
究竟患有深度近視的蜘蛛如何在第一時間探知網獲獵物的喜訊?其實祕訣就在那一根從蛛網中心點延伸而出的電報線,牠用一個腳趾抓住電報線,用腳聽著,神奇的是,牠能感覺到最細微的顫動,分辨出哪種顫動來自於俘虜?哪種顫動又只是風吹所致?此外本書法布爾也研究隆格多克大毒蠍、白蠟蟲、聖櫟胭脂蟲等昆蟲的生活習性。
《法布爾昆蟲記10:素食昆蟲》
究竟是何種原因讓每位光臨素食宴會的昆蟲們都只吃牠愛吃的植物?是安於亙古不變的飲食習慣?還是受限於胃的功能?法布爾在本書中針對素食昆蟲的進食習性做了詳細的觀察記錄,並討論金步行蟲、藍蒼蠅、螢火蟲等昆蟲的生活習性。
作者簡介:
法布爾(JEAN-HENRI FABRE 1823-1915)
1823年12月21日出生於法國南部的小山村聖雷翁。從孩提時代起,就表現出對於自然和昆蟲的喜愛,具有強烈的好奇心和敏銳的觀察力。這個喜歡沈思的小男孩,炯炯有神的雙眼,一直到老都是他給人的重要印象。
法布爾的家境貧困,使他選擇了公費的師範學校就讀,畢業後擔任小學與師範學校的老師多年,期間仍然不斷自修,取得數學、物理學、博物學學士的學位,並兼任博物館的館長。他的興趣廣泛,涵蓋數學、博物學、物理學、植物、昆蟲等學門,早期的研究與發表的論文也分散在這些領域。其中,關於昆蟲的研究受到達爾文的推崇,讚譽為「無與倫比的觀察家」。
45歲時,因授課方式受到保守勢力的反對,辭去教職,以撰寫科學讀物的文章,收取版稅維生。他在南法塞西尼翁村買了一小塊地,命名為荒石園,開始專心地觀察、研究昆蟲。此後的時間,他所有的研究、思想與生活都投注在昆蟲身上,也完整的記錄在十冊《法布爾昆蟲記全集》中。
55歲時,第一冊出版,接著平均每三年出版一冊。直到83歲時,第十冊出版,這三十多年的大部份時間,他的生活相當清苦,但是卻一點都不影響他對昆蟲投注的熱情。86歲時,他的鉅著終於揚名於世,各種獎項與讚譽也隨之而來,年邁而衰弱的他,對於這些榮耀淡然視之,仍然繼續著手第十一冊的內容,直到91歲過世。
譯者簡介:
梁守鏘
中山大學外語學院教授退休,主要著作及譯作有《法語詞匯學》、《法語詞匯學教程》、《法語搭配詞典》、《布阿吉爾貝爾選集》,《風俗論(上)》,《法國辯護書》,《波斯人信札》,《威尼斯女歌手》等。
方頌華
畢業於南京大學外語學院,法語文學碩士。現任職於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主要著作及譯作有《夏多布里昂作品精選》、《人類死刑大觀》、《杜拉斯文集》等。
鄒琰
畢業於南京大學外語學院。現任廣州大學外國語學院法語教授。主要著作及譯作有:《拉魯斯百科大詞典》、《夜》、《在我父親逝去的前夜》、《寫作》、《螞蟻與人----〈一個野蠻人在亞洲〉中的「中國自然史」》、《歐洲文學中的貞德》中國》等。
吳模信
畢業於北京大學西語系。南京大學教授退休。主要譯著及著作有《黑非洲政治問題》、《傅立葉選集》、《路易十世時代》、《風俗論(中)》、《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第二卷)》、《凱撒》、《猶太教史》、《19世紀法國名家名作選》、《雨果評論匯編》等。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推薦序】
相見恨晚的昆蟲詩人
劉克襄(自然觀察、自然旅行家)
我和法布爾的邂逅,來自於三次茫然而感傷的經驗,但一直到現在,我仍還沒清楚地認識他。
第一次邂逅
第一次是離婚的時候。前妻帶走了一堆文學的書,像什麼《深淵》、《鄭愁予詩選集》之類的現代文學,以及《莊子》、《古今文選》等古典書籍。只留下一套她買的,日本昆蟲學者奧本大三郎摘譯編寫的《昆蟲記》(東方出版社出版,1993)。
儘管是面對空蕩而淒清的書房,看到一套和自然科學相關的書籍完整倖存,難免還有些慰藉。原本以為,她希望我在昆蟲研究的造詣上更上層樓。殊不知,後來才明白,那是留給孩子閱讀的。只可惜,孩子們成長至今的歲月裡,這套後來擺在《射鵰英雄傳》旁邊的自然經典,從不曾被他們青睞過。他們朗朗上口的,始終是郭靖、黃藥師這些虛擬的人物。
偏偏我不愛看金庸。那時,白天都在住家旁邊的小綠山觀察。二十來種鳥看透了,上百種植物的相思林也認完了,林子裡龐雜的昆蟲開始成為不得不面對的事實。這套空擺著的《昆蟲記》遂成為參考的重要書籍,翻閱的次數竟如在英文辭典裡尋找單字般的習以為常,進而產生莫名地熱愛。
還記得離婚時,辦手續的律師順便看我的面相,送了一句過來人的忠告,「女人常因離婚而活得更自在。男人卻自此意志消沈,一蹶不振,你可要保重了。」
或許,我本該自此頹廢生活的。所幸,遇到了昆蟲。如果說《昆蟲記》提昇了我的中年生活,應該也不為過罷!
可惜,我的個性見異思遷。翻讀熟了,難免懷疑,日本版摘譯編寫的《昆蟲記》有多少分真實,編寫者又添加了多少幾分已見?再者,我又無法學到法布爾般,持續著堅定而簡單的觀察。當我疲憊地結束小綠山觀察後,這套編書就束之高閣,連一些親手製作的昆蟲標本,一起堆置在屋角,淪為個人生活史裡的古蹟了。
第二次邂逅
第二次遭遇,在四、五年前,到建中校園演講時。記得那一次,是建中和北一女保育社合辦的自然研習營。講題為何我忘了,只記得講完後,一個建中高三的學生跑來找我,請教了一個讓我差點從講台跌跤的問題。
他開門見山就問,「我今年可以考上台大動物系,但我想先去考台大外文系,或者歷史系,讀一陣後,再轉到動物系,你覺得如何?」
哇靠,這是什麼樣的學生!我又如何回答呢?原來,他喜愛自然科學。可是,卻不想按部就班,循著過去的學習模式。他覺得,應該先到文學院洗禮,培養自己的人文思考能力。然後,再轉到生物科系就讀,思考科學事物時,比較不會僵硬。
一名高中生竟有如此見地,不禁教人讚歎。近年來,台灣科普書籍的豐富引進,我始終預期,台灣的自然科學很快就能展現人文的成熟度。不意,在這位十七歲少年的身上,竟先感受到了這個科學藍圖的清晰一角。
但一個高中生如何窺透生態作家強納森.溫納《雀緣之謎》的繁複分析和歸納?又如何領悟威爾森《大自然的獵人》所展現的道德和知識的強度?進而去懷疑,自己即將就讀科系有著體制的侷限,無法如預期的理想。
當我以這些被學界折服的當代經典探詢時,這才恍然知道,少年並未看過。我想也是,那麼深奧而豐厚的書,若理解了,恐怕都可以跳昇去攻讀博士班了。他只給了我「法布爾」的名字。原來,在日本版摘譯編寫的《昆蟲記》裡,他看到了一種細膩而充滿文學味濃厚的詩意描寫。同樣近似種類的昆蟲觀察,他翻讀台灣本土相關動物生態書籍時,卻不曾經驗相似的敘述。一邊欣賞著法布爾,那獨特而細膩,彷彿享受美食的昆蟲觀察,他也轉而深思,疑惑自己未來求學過程的秩序和節奏。
十七歲的少年很驚異,為什麼台灣的動物行為論述,無法以這種議夾敘述的方式,將科學知識圓熟地以文學手法呈現?再者,能夠蘊釀這種昆蟲美學的人文條件是什麼樣的環境?假如,他直接進入生物科系裡,是否也跟過去的學生一樣,陷入既有的制式教育,無法開啟活潑的思考?幾經思慮,他才決定,必須繞個道,先到人文學院裡吸收文史哲的知識,打開更寬廣的視野。其實,他來找我之前,就已經決定了自己的求學走向。
第三次邂逅
第三次的經驗,來自一個叫「昆蟲王」的九歲小孩。那也是四、五年前的事,我在耕莘文教院,帶領小學生上自然觀察課。有一堂課,孩子們用黏土做自己最喜愛的動物,多數的孩子做的都是捏出狗、貓和大象之類的寵物。只有他做了一隻獨角仙。原來,他早已在飼養獨角仙的幼蟲,但始終孵育失敗。
我印象更深刻的,是隔天的戶外觀察。那天寒流來襲,我出了一道題目,尋找鍬形蟲、有毛的蝸牛以及小一號的熱狗(即馬陸,綽號火車蟲)。抵達現場後,寒風細雨,沒多久,六十多個小朋友全都畏縮在廟前避寒、躲雨。只有他,持著雨傘,一路翻撥。一小時過去,結果,三種動物都被他發現了。
那次以後,我們變成了野外登山和自然觀察的夥伴。初始,為了爭取昆蟲王的尊敬,我的注意力集中在昆蟲的發現和現場討論。這也是我第一次在野外聽到,有一個小朋友唸出「法布爾」的名字。
每次找到昆蟲時,在某些情況的討論時,他常會不自覺地搬出法布爾的經驗和法則。我知道,很多小孩在十歲前就看完金庸的武俠小說。沒想到《昆蟲記》竟有人也能讀得滾瓜爛熟了。這樣在野外旅行,我常感受到,自己面對的常不只是一位十歲小孩的討教。他的後面彷彿還有位百年前的法國老頭子,無所不在,且斤斤計較地對我質疑,常讓我的教學倍感壓力。
有一陣子,我把這種昆蟲王的自信,稱之為「法布爾併發症」。當我辯不過他時,心裡難免有些犬儒地想,觀察昆蟲需要如此細嚼慢嚥,像吃一盤盤正式的日本料理嗎?透過日本版的二手經驗,也不知真實性有多少?如此追根究底的討論,是否失去了最初的價值意義?但放諸現今的環境,還有其他方式可取代嗎?我充滿無奈,卻不知如何解決。
那時,我亦深深感嘆,日本版摘譯編寫的《昆蟲記》居然就如此魅力十足,影響了我周遭喜愛自然觀察的大、小朋友。如果有一天,真正的法布爾法文原著全譯本出版了,會不會帶來更為劇烈的轉變呢?沒想到,我這個疑惑才浮昇,譯自法文原著、完整版的《法布爾昆蟲記全集》中文版就要在台灣上市了。
說實在的,過去我們所接觸的其它版本的《昆蟲記》都只是一個片段,不曾完整過。你好像進入一家精品小鋪,驚喜地看到它所擺設的物品,讓你愛不釋手,但那時還不知,你只是逗留在一個小小樓層的空間。當你走出店家,仰頭一看,才赫然發現,這是一間大型精緻的百貨店。
完整版的《法布爾昆蟲記全集》
當完整版的《法布爾昆蟲記全集》出現時,我相信,像我提到的狂熱的「昆蟲王」,以及早熟的十七歲少年,恐怕會增加更多吧!甚至,也會產生像日本博物學者鹿野忠雄、漫畫家手塚治虫那樣,從十一、二歲就矢志,要奉獻一生,成為昆蟲研究者的人。至於,像我這樣自忖不如,半途而廢的昆蟲中年人,若是稍早時遇到的是完整版的《法布爾昆蟲記全集》,說不定那時就不會急著走出小綠山,成為到處遊蕩台灣的旅者了。
名人推薦:【推薦序】
相見恨晚的昆蟲詩人
劉克襄(自然觀察、自然旅行家)
我和法布爾的邂逅,來自於三次茫然而感傷的經驗,但一直到現在,我仍還沒清楚地認識他。
第一次邂逅
第一次是離婚的時候。前妻帶走了一堆文學的書,像什麼《深淵》、《鄭愁予詩選集》之類的現代文學,以及《莊子》、《古今文選》等古典書籍。只留下一套她買的,日本昆蟲學者奧本大三郎摘譯編寫的《昆蟲記》(東方出版社出版,1993)。
儘管是面對空蕩而淒清的書房,看到一套和自然科學相關的書籍完整倖存,難免還有些慰藉。原本以為,她希望我...
推薦序
兒時記趣與昆蟲記
楊平世(臺灣大學昆蟲系名譽教授)
「余憶童稚時,能張目對日,明察秋毫。見藐小微物必細察其紋理,故時有物外之趣。」
清 沈復 《浮生六記》之「兒時記趣」
「在對某個事物說"是"以前,我要觀察、觸摸,而且不是一次,是兩三次,甚至沒完沒了,直到我的疑心在如山鐵証下歸順聽從為止。」
法國 法布爾 《法布爾昆蟲記全集 7 》
《浮生六記》是清朝的作家沈復在四十六歲時回顧一生所寫的一本簡短回憶錄。其中的「兒時記趣」一文是大家耳熟能詳的小品,文內記載著他童稚的心靈如何運用細心的觀察與想像,為童年製造許多樂趣。在浮生六記付梓之後約一百年(1909年),八十五歲的詩人與昆蟲學家法布爾,完成了他的昆蟲記的第十冊,也是最後一冊,並印刷問世。
這套耗時卅餘年寫作、多達四百多萬字、以文學手法、日記體裁寫成的鉅作,是法布爾一生觀察昆蟲所寫成的回憶錄,除了紀錄他對昆蟲所進行的觀察與實驗結果外,同時也記載了研究過程中的心路歷程,對學問的辨證,和對人類生活與社會的反省。在昆蟲記中,無論是六隻腳的昆蟲或是八隻腳的蜘蛛,每個對象都耗費法布爾數年到數十年的時間去觀察並實驗,而從中法布爾也獲得無限的理趣,無悔地沉浸其中。
遠流版《法布爾昆蟲記全集》
昆蟲記的原法文書名《SOUVENIRS ENTOMOLOGIQUES》,直譯為「昆蟲學的回憶錄」,在國內大家較熟悉《昆蟲記》這個譯名。早在1933年,上海商務出版社便出版了本書的首部中文節譯本,書名當時即譯為《昆蟲記》。之後於1968年,台灣商務書店復刻此一版本,在接續的廿多年中成為在臺灣發行的唯一中文節譯版本,目前已絕版多年。1993年國內的東方出版社引進由日本集英社出版,奧本大三郎所摘譯改寫的《昆蟲記》一套八冊,首度為國人有系統地介紹法布爾這套鉅著。這套書在奧本大三郎的改寫下,採對小朋友說故事體的敘述方法,輔以插圖、背景知識和照片說明,十分生動活潑。但是,這一套書卻不是法布爾的原著,而僅是摘譯內容中科學的部分改寫而成。
今天,遠流出版公司的這一套《法布爾昆蟲記全集》十冊,則是引進2001年由大陸花城出版社所出版的最新中文全譯本,再加以逐一修潤、校訂、加註、修繪而成的。這一個版本是目前唯一的中文版全譯本,而且直接譯自法文版原著,不是摘譯,也不是轉譯自日文或英文;書中並有三百餘張法文原著的昆蟲線圖,十分難得。《法布爾昆蟲記全集》第一次讓國人有機會「全覽」法布爾這套鉅作的諸多面相,體驗書中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欣賞優美的用字遣詞,省思深刻的人生態度,並從中更加認識法布爾這位科學家與作者。
法布爾小傳
法布爾(Jean Henri Fabre, 1823-1915)出生在法國南部,靠近地中海的一個小鎮的貧窮人家。童年時代的法布爾便已經展現出對自然的熱愛與天賦的觀察力,在他的〈遺傳論〉一文中可一窺梗概。(文見《法布爾昆蟲記全集 6 》)靠著自修,法布爾考取亞維農(Avignon)師範學院的公費生;十八歲畢業後擔任小學教師,繼續努力自修,在隨後的幾年內陸續獲得文學、數學、物理學和其他自然科學的學士學位與執照(近似於今日的碩士學位),並在1855年拿到科學博士學位。
年輕的法布爾曾經為數學與化學深深著迷,但是後來發現動物世界更加地吸引他,在取得博士學位後,即決定終生致力於昆蟲學的研究。但是經濟拮据的窘境一直困擾著這位滿懷理想的年輕昆蟲學家,他必須兼任許多家教與大眾教育課程來貼補家用。儘管如此,法布爾還是對研究昆蟲和蜘蛛樂此不疲,利用空暇進行觀察和實驗。
這段期間法布爾也以他豐富的知識和文學造詣,寫作各種科普書籍,介紹科學新知與各類自然科學知識給大眾;他的大眾自然科學教育課程也深獲好評,但是保守派與教會人士卻抨擊他在公開場合向婦女講述花的生殖功能,而中止了他的課程,也由於老師的待遇實在太低,加上受到流言中傷,法布爾在心灰意冷下辭去學校的教職,隔年甚至被虔誠的天主教房東趕出住處,使得他的處境更是雪上加霜,也迫使他不得不放棄到大學任教的願望。法布爾求助於英國的富商朋友,靠著朋友的慷慨借款,在1870年舉家遷到歐宏桔(Orange)由當地仕紳所出借的房子居住。
在歐宏桔定居的九年中,法布爾開始殷勤寫作,完成了六十一本科普書籍,有許多相當暢銷,甚至被指定為教科書或輔助教材。而版稅的收入使得法布爾的經濟狀況逐漸獲得改善,並能逐步償還當初的借款。這些科普書籍的成功使《昆蟲記》一書的寫作構想逐漸在法布爾腦中浮現,他開始整理集結過去卅多年來觀察所累積的資料,並著手撰寫。但是也在這段期間裡,法布爾遭遇喪子之痛,因此在《昆蟲記》第一冊書末留下懷念愛子的文句。
1879年法布爾搬到歐宏桔附近的塞西尼翁小村,在那裡買下一棟義大利風格的房子和一公頃的荒地定居。雖然這片荒地滿是石礫與野草,但是法布爾的夢想「擁有一片自己的小天地觀察昆蟲」的心願終於達成。他用故鄉的普羅旺斯語將園子命名為荒石園(L'Harmas)。在這裡法布爾可以不受干擾地專心觀察昆蟲,並專心寫作(相關文見《法布爾昆蟲記全集 2 》)。這一年《昆蟲記》的首冊出版,接著並以約三年一冊的進度完成全部十冊的寫作;法布爾也在這裡度過他晚年的卅載歲月。
除了《昆蟲記》外,法布爾在1862年到1891年的這卅年間,共出版了九十五本十分暢銷的書,像1865年出版的LE CIEL(天空)一書便賣了十一刷,有些書的銷售量甚至超過《昆蟲記》。除了寫書與觀察昆蟲之外,法布爾也是一位優秀的真菌學家和畫家,曾繪製採集到的七百種蕈菇,張張都是一流之作;他也留下了許多詩作,並為之譜曲。但是後來模仿《昆蟲記》一書體裁的書籍越來越多,且書籍不再被指定為教科書而使版稅減少,法布爾一家的生活再度陷入困境。一直到人生最後十年,法布爾的科學成就才逐漸受到法國與國際的肯定,獲得政府補助和民間的捐款才再脫離清寒的家境。1915年,法布爾以九十二歲的高齡於荒石園辭世。
這位多才多藝的文人與科學家,前半生為貧困所苦,但是卻未曾稍減對人生志趣的追求;雖曾經歷許多攀附權貴的機會,依舊未改其志。開始寫作《昆蟲記》時,法布爾已經超過五十歲,到八十五歲完成這部鉅作,這樣的毅力與精神與近代分類學大師麥爾(Ernst Mayr)高齡近百還在寫書同樣讓人敬佩。在《昆蟲記》中,讀者不妨仔細注意法布爾在字裡文間透露出來的人生體驗與感慨。
科學的《昆蟲記》
在法布爾的時代,以分類學為基礎的博物學是主流的生物科學,歐洲的探險家與博物學家在世界各地採集珍禽異獸、奇花異草,將標本帶回博物館進行研究;但是有時這樣的工作會流於相當公式化且表面的研究。新種的描述可能只有兩三行拉丁文的簡單敘述便結束,不會特別在意特殊的構造和其功能。
法布爾對這樣的研究相當不以為然:「你們(博物學家)把昆蟲肢解,而我是研究活生生的昆蟲;你們把昆蟲變成一堆可怕又可憐的東西,而我則使人們喜歡他們……你們研究的是死亡,我研究的是生命。」在今日見分子不見生物的時代,這一段話對於研究生命科學的人來說仍是諍諍建言。
法布爾在當時是少數投入冷僻的行為與生態觀察的非主流學者,科學家雖然十分了解觀察的重要性,但是對於「實驗」的概念還未成熟,甚至認為博物學是不必實驗的科學。法布爾稱得上是將實驗導入田野生物學的先驅者,英國的科學家路柏格(John Lubbock)也是這方面的先驅,但是他的主要影響在於實驗室內的實驗設計。法布爾說:「僅僅靠觀察常常會引人誤入歧途,因為我們遵循自己的思維模式來詮釋觀察所得的數據。為使真相從中現身,就必須進行實驗,只有實驗才能幫助我們探索昆蟲智力這一深奧的問題……通過觀察可以提出問題,通過實驗則可以解決問題,當然問題本身得是可以解決的;即使實驗不能讓我們茅塞頓開,他至少可以從一片混沌的雲霧中投射些許光明。」(見《法布爾昆蟲記全集 4 》)
這樣的正確認知使得《昆蟲記》中的行為描述變得深刻而有趣,法布爾也不厭其煩地在書中交代他的思路和實驗,讓讀者可以融入情景去體驗實驗與觀察結果所呈現的意義。而法布爾也不會輕易下任何結論,除非在三番兩次的實驗或觀察都呈現確切的結果,而且有合理的解釋時他才會說「是」或「不是」。比如他在村里用大砲發出巨大的爆炸聲響,但是發現樹上的鳴蟬依舊故我鳴個不停,他沒有據此做出蟬是聾子的結論,只保留地說他們的聽覺很鈍 (見《法布爾昆蟲記全集 5 》)。類似的例子在整套《昆蟲記》中比比皆是,可以看到法布爾對科學所抱持的嚴謹態度。
在整部《昆蟲記》中,法布爾著力最深的是有關昆蟲的本能部分,這一部份的觀察包含了許多寄生蜂類、蠅類和甲蟲的觀察與實驗。這些深入的研究推翻了過去權威所言這是既得習慣的錯誤觀念,了解昆蟲的本能是無意識地為了某個目的和意圖而行動,並開創「結構先於功能」這樣一個新的觀念(見《法布爾昆蟲記全集 4 》)。法布爾也首度發現了昆蟲對於某些的環境次機會有特別的反應,稱為趨性(taxis),比如某些昆蟲夜裡飛向光源的趨光性、喜歡沿著角落行走活動的趨觸性等等。而在研究芫青的過程中,他也發現了有別於過去知道的各種變態型式,在幼蟲期間多了一個特殊的擬蛹階段,法布爾將這樣的變態型式稱為「過變態」(hypermetamorphosis),這是不喜歡使用學術象牙塔裡那種艱深用語的法布爾,唯一發明的一個昆蟲學專有名詞。(見《法布爾昆蟲記全集 2 》)
雖然法布爾的觀察與實驗相當仔細而有趣,但是《昆蟲記》的文學寫作手法有時的確帶來一些問題,尤其是一些擬人化的想法與寫法,可能會造成一些誤導。還有許多部分已經在後人的研究下呈現出較清楚的面貌,甚至與法布爾的觀點不相符合。比如法布爾認為蟬的聽覺很鈍,甚至可能沒有聽覺,因此蟬鳴或其他動物鳴叫只是表現享受生活樂趣的手段罷了。這樣的陳述以科學角度來說是完全不恰當的。因此希望讀者沉浸在本書之餘,也記得「盡信書不如無書」的名言,時時抱持懷疑的態度,旁徵博引其他書籍或科學報告的內容相互佐證比較,甚至以本地的昆蟲來重複進行法布爾的實驗,看看是否同樣適用或發現新的「事實」,這樣法布爾的《昆蟲記》才真正達到了啟發與教育的目的,而不只是一堆現成的知識而已。
人文與文學的《昆蟲記》
《昆蟲記》並不是單純的科學紀錄,它在文學與科普同樣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在整部書中,法布爾不時引用希臘神話、寓言故事,或是家鄉普羅旺斯地區的鄉間故事與民俗,不使內容成為曲高和寡的科學紀錄,而是和「人」密切相關的整體。這樣的特質在這些年來越來越希罕,學習人文或是科學的學子往往只沉浸在自己的領域,未能跨出學門去豐富自己的知識,或是實地去了解這塊孕育我們的土地的點滴。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如果《昆蟲記》能獲得您的共鳴,或許能激發您想去了解這片土地自然與人文風采的慾望。
法國著名的劇作家羅斯丹說法布爾「像哲學家一般地思,像美術家一般地看,像文學家一般地寫」;大文學家雨果則稱他是「昆蟲學的荷馬」;演化論之父達爾文讚美他是「無與倫比的觀察家」。但是在十八世紀末的當時,法布爾這樣的寫作手法並不受到一般法國科學家們的認同,認為太過通俗輕鬆,不像當時科學文章艱深精確的寫作結構。然而法布爾堅持自己的理念,並在書中寫道:「高牆不能使人熱愛科學。將來會有越來越多人致力打破這堵高牆,而他們所用的工具,就是我今天用的、而為你們(科學家)所鄙夷不屑的文學。」。
以今日科學的角度來看,這樣的陳述或許有些情緒化的因素摻雜其中,但是他的理念已成為科普的典範,而《昆蟲記》的文學地位也已為普世所公認,甚至進入諾貝爾文學獎入圍的候補名單。《昆蟲記》裡面的用詞遣字是值得細細欣賞品味的,雖然中譯本或許沒能那樣真實反應出法文原版的文學性,但是讀者必定能發現他絕非鋪陳直敘的新聞式文章。尤其在文章中對人生的體悟、對科學的感想、對委屈的抒懷,常常流露出法布爾作為一位詩人的本性。
《昆蟲記》與演化論
雖然昆蟲記在科學、科普與文學上都佔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但是有關《昆蟲記》中對演化論的質疑是必須提出來說的,這也是目前的科學家們對法布爾的主要批評。達爾文在1859年出版了《物種原始》一書,演化的概念逐漸在歐洲傳佈開來;廿年後,《昆蟲記》第一冊有關寄生蜂的部分出版,不久便被翻譯為英文版,達爾文在閱讀了《昆蟲記》之後深深佩服法布爾那樣巨細靡遺且求證再三的記錄,並援以支持演化論;相反地,雖然法布爾非常敬重達爾文,兩人並相互通信分享研究成果,但是在《昆蟲記》中,法布爾不只一次地公開質疑演化論,如果細讀《昆蟲記》,可以看出來法布爾對於天擇的觀念相當懷疑,但是卻沒有一口否決過,如同他對昆蟲行為觀察的一貫態度。我們無從得知法布爾是否真正仔細完整讀過達爾文的《物種原始》一書,但是《昆蟲記》裡面展現的質疑,絕非無的放矢。
十九世紀末甚至二十世紀初的演化論知識只能說有了個原則,連基礎的孟德爾遺傳說都還是未能與演化論相結合,遑論其他許多的演化概念和機制,都只是從物競天擇去延伸解釋,甚至淪為說故事,這種信心高於事實的說法對法布爾來說當然算不上是嚴謹的科學理論;同一時代的科學家有許多接受了演化論,但是無法認同天擇是演化機制的說法,而法布爾在這點上並未區分二者。但是嚴格說來,法布爾並未質疑物種分化或是地球有長遠歷史這些概念,而是認為選汰無法造就他所見到的昆蟲本能,並且以明確的標題「給演化論戳一針」表示自己的懷疑。(文見《法布爾昆蟲記全集 3 》)
而法布爾從自己研究得到的信念,有時也成為一種偏見,妨礙了實際的觀察與實驗的想法。昆蟲學家巴斯德(George Pasteur)便曾在《Scientific American》(台灣譯為《科學人》雜誌,遠流發行))上為文,指出法布爾在觀察某種蟹蛛(Thomisus onustus)在花上的捕食行為,以及昆蟲裝死行為的實驗的錯誤。法布爾認為很多發生在昆蟲的典型行為就如同一個原型,但是他也觀察到這些行為在族群中是或多或少有所差異的,只是他把這些差異歸為「出差錯」,而未從演化的角度思考。
法布爾同時也受限於一個迷思,這樣的迷思即使到今天也還普遍存在於大眾,就是既然物競天擇,那為何還有這些變異?為什麼糞金龜中沒有通通變成身強體壯的個體,甚至反而大個兒是少數?現代演化生態學家主要是由「策略」的觀點去看這樣的問題,比較不同策略間的損益比,進一步去計算或模擬發生的可能性,看結果與預期是否相符。有興趣想多深入了解的讀者可以閱讀更多的相關資料書籍再自己做評價。
今日《昆蟲記》
《昆蟲記》迄今已被翻譯成五十多種文字與數十種版本,並橫跨兩個世紀,繼續在世界各地擔負起對昆蟲行為學的啟蒙角色。希望能藉由遠流這套《法布爾昆蟲記全集》的出版,引發大家更多的想法,不管是對昆蟲、對人生、對社會、對科普、對文學,或是對鄉土的。曾經聽到過有小讀者對《昆蟲記》一書抱著高度的興趣,連下課十分鐘都把握閱讀,也聽過一些小讀者看了十分鐘就不想再讀了,想去打球。我想,都好,我們不期望每位讀者都成為法布爾,法布爾自己也承認這些需要天份。社會需要多元的價值與各式技藝的人。同樣是觀察入裡,如果有人能因此走上沈復的路,發揮想像沉醉於情趣,成為文字工作者,那和學習實事求是態度,浸淫理趣,立志成為科學家或科普作者的人,這個社會都應該給予相同的掌聲與鼓勵。
楊平世 2002.6.18於台灣大學農學院
兒時記趣與昆蟲記
楊平世(臺灣大學昆蟲系名譽教授)
「余憶童稚時,能張目對日,明察秋毫。見藐小微物必細察其紋理,故時有物外之趣。」
清 沈復 《浮生六記》之「兒時記趣」
「在對某個事物說"是"以前,我要觀察、觸摸,而且不是一次,是兩三次,甚至沒完沒了,直到我的疑心在如山鐵証下歸順聽從為止。」
法國 法布爾 《法布爾昆蟲記全集 7 》
《浮生六記》是清朝的作家沈復在四十六歲時回顧一生所寫的一本簡短回憶錄。其中的「兒時記趣」一文是大家耳熟能詳的小品,文內記載著他童稚的心靈如何運用細心的觀察與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