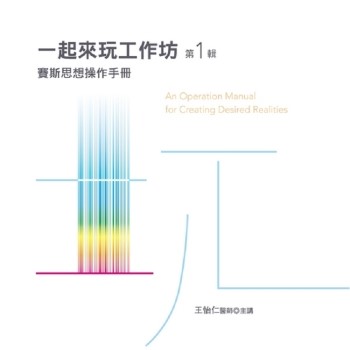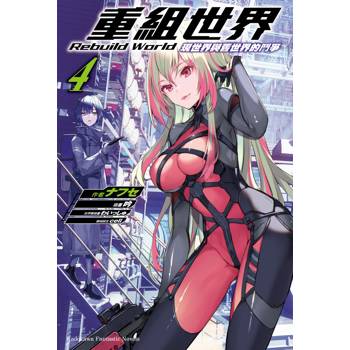推薦序
地心的黑光
01.
曾看過一部紀錄片,拍的是藏傳佛教尋找轉世靈童的故事。
在尊者袞卻格西逝世之後,弟子梭巴隨身帶著尊者生前使用的念珠,在各個村落尋覓男童,遇到孩子就問他們:你認得它嗎?
大多數的孩子不明所以,不是搖搖頭,就是把念珠抓來把玩之後便還給他。如此行走一年,直到遇見一歲半的巔律沃度。他甫看到念珠就哭著要,梭巴無論如何都拿不回去。後來便將他接回寺中,沃度一一指認出尊者生前使用的法器與日常用具,最後通過了達賴的認證,故事至此算是確認尊者轉生。
印象最深刻的幾幕,是當梭巴帶著糖果和彩色氣球,滿懷期待去親近孩子,卻發現他們皆是普通嬰孩而難掩失落。他在清晨打坐,傍晚祈禱,靜候上蒼賜與他足夠的幸運和啟示。然後沃度出現。從梭巴拿出水晶念珠的瞬間,沃度那任性、霸道的模樣,如立足於世界之上的別種存在,他用他的小手緊握著念珠,對梭巴說:這是我的。熟識地指認所有物件。梭巴終於流下了眼淚,知道自己尋回了他的尊者。
靈童沃度直覺而堅信的形象,使我想到顧城的身世,和他的字。
恍若世界的夢,純粹詩意的轉世。
02.
樹膠般
緩緩流下的淚
粘合了心的碎片
使我們相戀的
是共同的苦痛
而不是狂歡
──〈悟〉
這是讓我走入顧城的第一首詩,已忘了是何年何月。畫面上,兩個人相視而笑。笑是因為懂得掙扎的無用,眼淚是明白,行至如此的唯一與決絕。
他們確實分享了快樂和傷口,可總是傷口讓人敞開,交換性命,隨後失速墜跌。
顧城的詩句乾淨,口語地像熟識的友人站在眼前對你訴說,但那親密中帶著絕望,那故事令你斷盡肝腸:一切都明明白白/但我們仍匆匆錯過/因為你相信命運/因為我懷疑生活〈錯過〉。真正失之交臂的當然不會是命運和生活,而是一人寧願相信,一人始終懷疑──或許在某個層面上他們是一樣的,都來自內發的虔誠,可相信是因為接受,而懷疑則是拒斥:是有世界/有一面能出入的鏡子/你從這邊走向那邊/你避開了我的一生〈我承認〉。
自己被顧城深深吸引,大多是因為他詩中美麗的無助。如風暴前夕的海面,看似平靜卻蘊含著死亡的拉扯。難以想像是何等悲憤的眼瞳,才能對所有事物平等地哀切。如〈佛語〉:我的職業是固定的/固定地坐在那/坐一千年/來學習那種最富有的笑容/還要微妙地伸出手去/好像把什麼交給了人類。
佛在梵文的原意是覺者,是超越生命的個體,卻在詩中被荒謬地扭轉為某種俗世的職業;渡化眾生也不過是工作,帶著尋常的厭膩、虛矯和無奈:我不知道能給什麼/甚至也不想得到/我只想保存自己的淚水/保存到工作結束。
可這悲哀的日子會有結束的一天嗎。幾近永恆的生命竟也變成了詛咒。
什麼樣的人能夠寫出這樣的字?能寫出這樣文字的人又是怎麼渡過日常?存著這樣的疑問,一次又一次地讀。直到查了顧城的生平,知道了後來發生在激流島上的事。
無法將偏執和瘋狂從生活中除去,也許是因為詩人對生命與自我的絕對忠誠。在他的小說《英兒》裡有這樣一段自白的描述:……你們是生活所生,我也是。但我的靈魂卻是死亡所生,它願意回到那裡去,就像你們願意回家,這是無法改變的事情,也是我們時聚時散的原因……〈死囚〉。
於是便明白了。這是唯一的可能,他僅有的命運。
沒有一隻鳥能躲過白天
正像,沒有一個人能避免
自己
避免黑暗
──〈熔點〉
03.
走入顧城的詩歌,有一些漸進的過程。誠如他將自我的狀態劃分為四個時期:「自然」,「文化」,「反文化」和「無我」。也許是因為生命經驗的關係,自己最先喜歡的是他文化與反文化的時期,之後才愛上自然和無我。
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卻用它尋找光明
──〈一代人〉
這是顧城最著名其中一首的短詩。駑鈍的自己初讀並無太深的感觸,甚至覺得意象過於簡單。直到後來,某次與內心搏鬥的時刻,突然感受到文字底下的深意:黑是最沉重混濁的顏色,如人的慾望和陰暗;黑色的眼睛象徵原生的身體,形成世人所見之形象。縱然每個人都有這樣的一副,擁有無數暗沉的肉身,但他卻說沒關係,這並不重要,你可以用它來行光明。
你以為你只能是人,只能固守僵化的世界,但顧城不這麼認為:「我曾像鳥一樣飛翔,用翅膀去摸天空,像樹枝一樣搖動,像水草一樣沉浸在透明的夢中,我曾是男孩,也是女孩,是金屬,也是河流,是陣陣芳香在春天裡的流動。我曾經是,所以現在也是,我感到了自身在萬物中無盡流變的光明。」(註一)乃是你心之所夢所想,才刻鑿出真實自我的輪廓。
此番「看懂」的過程彷彿靈犀一點。再重讀過去喜愛的詩句,便有了更多的奇趣與想像。然而顧城的超越性遠不只如此,當我讀到〈布林的檔案〉、〈鬼進城〉,視野的轉換,已從人類,變成其他難以名狀的事物。而後「無我」時期的代表作〈頌歌世界〉和〈水銀〉,幾乎重新賦予詞句意義,以至每一個字,皆像落地生根,看似凌亂,無情,卻又自然而冷靜,有重重生命的層次混雜其中。組詩〈城〉,如重返生命現場的註解,棄絕了闡釋、溝通,只扣問自身過去,紀錄,再現曾經的境況。那是詩人最終的故鄉,記憶的本源。創作是為了自證自明,不再渴求理解。
他曾在訪談中如此自述:「對於我來說,『無我』就是不再尋找『我』,我做我要做的一切,但是我不抱有目的。一切目的和結果讓命運去安排,讓各種機緣去安排。當我從目的中解脫出來之後,大地就是我的道路。」(註二)即便如此,在看似無序的書寫中,仍有些洞察和靈光,不時敲擊;我們摘下熟了的果子/我們創造早已成功的東西〈案〉;我們寫東西/像蟲子 在松果裡找路/一粒一粒運棋子/有時 是空的〈我們寫東西〉
隨著時序漫讀顧城的變化,感受自己走過想像的四季:「自然」如生意盎然的早春,「文化」如炙熱赤誠的盛夏,「反文化」是內省蕭索的晚秋,「無我」如內聚返璞的嚴冬。樹的風景,從綠葉,繁花,結果,掉落,到最後盡褪鉛華,徒留枝幹。樹的背景反成為了樹的風景──那片住著太陽和星月,擁有無限可能的宇宙。
04.
在落筆寫這篇序文之前,內心忐忑了許久。
極其不願意談自己的解讀和詮釋,因為相信閱讀始終有其霸道,不欲與他人溝通的部分。那是詩與讀者最純粹,最神祕無解的交會。分享的過程雖有助於普及,也許排遣孤獨,卻亦可能消泯原初的喜愛。
顧城的詩殺死了我無數次,也拯救了我無數次,至今依然是我認知華語詩的頂點。從開始投入寫作至今,最能夠表達他詩歌對我影響的,大抵也是他自己的話:「美是一種狀態,它足以使我感到這個世界的虛幻。因為美出現的時候,它太真實了。」(註三)
不只一次想像,自己窮盡餘生奔逐,只為了觸碰那模糊身形的影子(是的只可能是影子)。
「他無所知又全知,他無所求又盡求;他全知所以微笑,他盡求所以痛苦。」(註四)顧城曾在訪談中,這樣形容自己心目中偉大的詩人。我想他也確實身體力行了,將詩當命在活,也把命當詩在寫。
感謝他在有生之年,完成了這些詩歌。它們將是人類傳世的寶藏。
感謝他,讓我們得以窺見深藏於生活表土之下,熾盛如岩漿,溫暖而無邊的黑暗之光。
文╱任明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