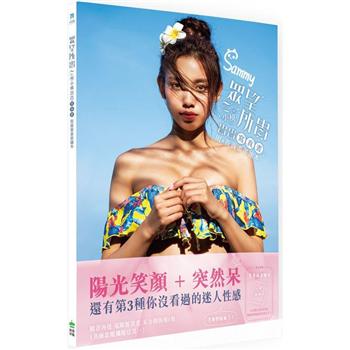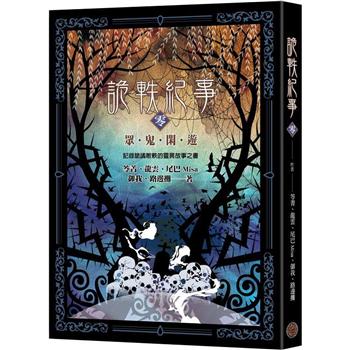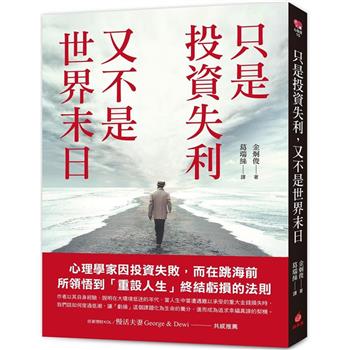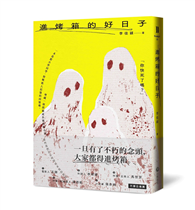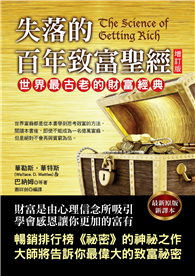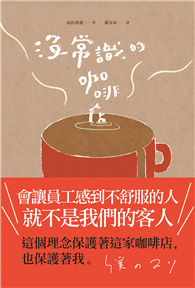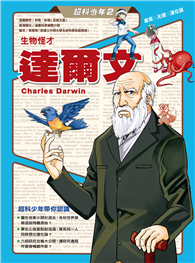後記
我對社頭的第一個記憶,是大姊。
大姊要結婚了,嫁去社頭的枋橋頭。我問她,社頭在哪裡?很遠嗎?海邊?山上?結婚是什麼東西?好不好玩?她表情複雜,沒回答。
那待嫁表情留存腦中,長大後,世故後,終於能解讀。舊時代女性結婚,從原生父權家庭,被拋擲到另一個婚姻父權家庭,恐懼與幸福拉扯,海邊或山上,城市或鄉村,遠或近,都非完全自主,嫁去哪裡,就困在哪裡。
第二個記憶,我上小學了,在洗手檯聽到兩個女生對話。
「老師說妳是社頭人,來我們永靖讀書。」
「對。」
「妳姓蕭。」
「對。」
「我媽說,社頭都是痟查某。」
蕭姓女同學立刻大哭:「我不是痟查某,我不是痟查某啦!」
二○一九年12月出版《鬼地方》,我搭火車返回永靖,傻看車廂站名顯示:員林→永靖→社頭,心想,永靖下一站是大姊的婆家,那要不要下一本小說,就寫社頭呢?耳邊忽然響起小時洗手檯那兩位女生的對話。
寫作如人生難料,當時已經有一些人物來敲門,決定要寫三姊妹,但就是少了許多故事元素與人物,社頭小說先擱置,時機未到。《樓上的好人》先完成,場景是員林。讀者當面問我:「永靖跟員林都寫了,彰化縣還有很多地方啊,那什麼時候寫社頭?我社頭人,跟你講,社頭很神經啦。很多瘋子。」
二○二三年秋天,愛荷華市,斐濟作家Mary Rokonadravu與菲律賓美籍作家Noelle De Jesus約我在河邊散步,橋上我們遇見了一位常來參加作家朗讀活動的沈默白髮非裔男士,他總是抱著一本厚厚的書,橋上我終於看到書名,是但丁的《神曲》。當天晚上我在房間裡開始寫《社頭三姊妹》的大綱,抵達了,我需要的關鍵人物,出現了,可以開始動筆。
回臺灣做田調,二姊開車載我去社頭,清水岩,芭樂市場,芭樂田,二姊的孫女大哭,那宏亮哭聲與社頭交融,當下決定寫進小說。
另一次,大姊從永靖騎機車載我回社頭,經過她婆家枋橋頭,路過襪子工廠,騎進社斗路,在社頭火車站前停下,她說,社頭都沒變。我獨自在社頭徒步晃蕩,亂走亂看,在鄉公所前方,有位阿嬤對我說了好多話。她說,社頭這麼無聊?寫小說?寫給鬼看喔?去找份工作啦,去台積電,你好瘦,要不要來我家吃飯?
二○二四年十月,我完成了社頭小說。
員林→永靖→社頭。
《樓上的好人》→《鬼地方》→《社頭三姊妹》。
完成了,這三本小說,是我的「彰化三部曲」。
跟小說家王仁劭線上聊天,他外婆家在社頭,我說寫了一本社頭小說,他立刻說:「猜一定會有角色姓蕭。」
寫社頭,真是躲不了蕭,查詢一下歷任社頭鄉長,幾乎都姓蕭。我自己數度去踏查,接收了滿滿的故事能量。蕭。痟。
太有趣了,但阿嬤說無聊。阿嬤是以在地人的口吻,告誡我這個外地人,鄉野無趣,人口外流,景觀無變異,無高樓缺繁華,如何寫小說?各種民間調查也呼應阿嬤,彰化縣數度榮登「全臺灣最無聊縣市」寶座。
什麼叫做無聊?
所謂的觀光客視角。觀光旅遊,眼睛需要輝煌,聲光燦爛,大型地標建築,大山大海,拍照上傳。
彰化缺了這些,所以人稱無聊。
太好了,吸引我的,就是最平凡的人,最平淡的地景。小說不是到此一遊,而是深掘。最不起眼的,在我眼中,金礦銀礦。
彰化是我的故鄉,小時我跟著爸媽進出許多宮廟與神壇。神壇自創教派,組仙女班,眾仙女服侍壇主,早就打破一夫一妻制。各式各樣的宗教民俗儀式,都是人類社群的焦慮體現,想生男,要賺大錢,病痛,考大學,投入政壇,進科技產業,神鬼之境,就是貪念聚集之地。我小時鑽進某神壇的神桌,目睹桌下某種機關,讓神桌能左右搖晃,信徒稱「神蹟」。臺灣醫療先進,但至今很多人病痛或抑鬱,先尋求的不是醫生,而是宮廟神壇。
不,不是「迷信」而已。鬼神文化,是繽紛多彩的生活紋理。
慶典儀式裡,人們用力喧囂,求神問鬼,或許,抵銷一點點孤獨。
最無聊的,最平淡的,最孤獨的。
襪子,羊駝,芭樂,戴勝,Jimi Hendrix。
這是我虛構的社頭。對不起,也,謝謝,社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