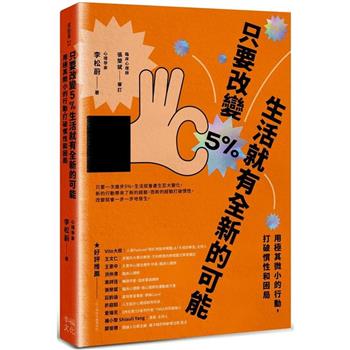合作出版總序
樹立典範 給新一代醫療人員增添精神滋養
我一直很慶幸這四十幾年習醫與行醫的生涯,適逢生命科技蓬勃發展,醫學進步最迅速的時期,在這段時間內,人類的平均壽命幾乎加倍,從戰前的四十幾歲增加到今天已接近八十歲。如今,我雖然己逐漸逼近退休年齡,卻很幸運的能夠與年輕的一代同樣抱著興奮的心情迎接基因體醫療的來臨,一同夢想下一波更令人驚奇的醫學革命。
我更一直認為能夠在探究生命奧祕的同時,協助周遭的人們解除疾病帶給他們的痛苦,甚至改變他們的生命,這種經常與病人分享他們生命經驗的職業,是一件極具挑戰性、極有意義的工作。在我這一生所接觸的師長、同僚和後輩中,我不斷地發現樂在工作的人,都是從照顧病人的過程中獲得滿足,從為病人解決問題的過程中找到樂趣。而驅使他們進一步從事教育、研究、發現的工作最強有力的動機也是為了解決病人的問題。自從我進入醫療工作後,因著這些典範的激勵,支持我不斷的往前走,也常讓我覺得能與他們為伍是個極大的光榮,更讓我深深感受到典範對我的影響力和重要性。
除了周遭生活中所遇到的典範外,我相信在每個人的生命中,必定也經常從書籍中找到令我們欽慕的人物和值得學習的經驗,這些人、這些觀察也常具有相同的影響力和重要性。因此,我過去曾推薦一些有關醫療的好書給天下文化出版社,建議他們請人翻譯出版,這次當天下文化出版社反過來提議與黃達夫醫學教育促進基金會合作出版有關醫療的好書,由基金會贊助提供給國內的醫學院學生和住院醫師時,我認為是件非常值得嘗試的工作,董事會也欣然認同這是件值得投入的事情,目前計劃每年出版三本書,給國內新一代醫療人員增添一些精神上的滋養,希望能激勵他們從醫療工作中找到生命的意義和生活的樂趣。
黃達夫醫學教育促進基金會董事長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院長 黃達夫
二○○二年一月十五日
序
穿上白袍之後∕賴其萬
二○○一年底,好友黃達夫醫師送我一本《White Coat》,我在看完以後,寫了一篇導讀在《當代醫學》的「每月一書」專欄裡介紹了這本好書。之後我陸續接到了幾位不同學校的醫學生寫信告訴我,他們很希望這本書能譯成中文,讓更多台灣的讀者共享。有一位同學甚至告訴我她已開始著手翻譯了,我這才趕快告訴她,如果我們要出中譯本的話,一定得先要有版權才行。而在這同時,黃達夫院長與我也都認為這本書實在值得譯成中文,列入黃達夫醫學教育促進基金會與天下文化合作出書的第四本好書。於是天下文化就找了專業的朱珊慧女士著手翻譯,而很高興地看到這本書的中譯本終於問世了。
幾個星期前天下文化邀我幫她們審閱譯稿時,我正好要動身去波士頓參訪哈佛醫學院一個星期,於是我就帶著譯稿與原著一起動身。我一邊重讀作者羅絲曼(Ellen Lerner Rothman)醫師在這書裡,娓娓道出她在哈佛大學醫學院從入學到畢業的四年中,對同學、老師、病人、醫護人員以及醫療環境的各種觀察與感觸,一邊又正好在這所醫學院與她們的師生在一起。走在她所描述的建築物裡,與她書中所提到的師長交談,也有機會與她的學弟妹談他們在這裡受教育的感想,使我對這本書更產生一種分外的親切感。
第一天到哈佛與前院長費德曼教授交談時,我與他提及《白袍》這本書,我告訴他我很想知道目前羅絲曼醫師在做什麼工作。想不到他說我問對了人,因為他目前正是負責哈佛醫學院校友會的事。於是他立即轉頭在電腦上查了一下,就發現這位醫生現在在亞利桑那州的印地安人保留區服務。這老人家臉色愉悅地告訴我,當他讀《白袍》這本書時,對這學生的印象是「這女孩子很會說話,很會寫文章」,但他沒有把握她真的會作一位有愛心、能奉獻的醫生。今天在獲知她居然真的秉持理想不為利誘,選擇在印地安人保留區服務時,他有說不出的快慰。他說現在的醫學生在他們的生涯規劃裡,不少人都把「生活方式」(life style)擺在理想之上,而讓他十分感慨。我們交換了許多有關這方面的意見,而我們都同意醫生這職業與其他行業非常不一樣的就是,我們不能單純以金錢物質的酬庸來衡量我們的成就,這身白袍的確具有更深遠的意義。
全書總共分為三大部分,「醫學院第一年」包括如何走入學醫之路、經歷解剖學科、急診室、安寧病房臨終照顧以及醫學生學習如何探詢病人性方面的病史等等。「醫學院第二年」包括一些臨床診斷的學習、價值觀的改變,參加第一階段醫師資格考試的經驗,以及接觸到一些較不尋常的病人的記趣。最後部分「臨床實習」則包括醫學院第三與第四年的生活,描述到各科實習的心得,以及在實習過程中留下深刻印象的特殊病人。
在照顧癌末的病人時,她領悟出「作為一名醫療照顧者,我的目標是盡量讓他感到舒適,並且幫助他同時能夠掌握醫療方面與精神方面的生活。我並不認為我必須要挽救他的性命或讓他走得漂亮,我只希望幫他走得有尊嚴」。而她很感慨地說出一段醫師的心語:「身為醫療照顧者,實在很難不採用可以救命的技術,而讓病人只接受簡單、非侵襲性的急救方法,然後死亡。不經過一番奮戰就放棄病人,實在不容易做到。死得有尊嚴,在醫院裡並不常見。」她並道出一位同學聽到的病人心聲:「我知道,要醫生親近一個快死的人很不容易。但如果到了什麼話都不對我說的地步,就只有兩種可能:要不是他們以醫生的立場,已經說不出任何鼓勵我的話了,就是他們根本不在乎我。」
作者在書中多處都提到哈佛醫學院特別重視「病醫課」(patient-doctor course)。這課程的名字最凸顯的就是把「病人」放在「醫生」之前,顧名思義這堂課的目的就是要加強以病人為中心的醫療理念。從大一開始,這門課就是必修,直到大三。醫學生在不同階段的學習過程中,透過如何去認識病人、如何獲得病史、如何獲得明確的診斷、如何與師生溝通分享臨床的種種心得,而融合醫病關係、醫學倫理與醫學專業的知識。作者在書中說:「到了二年級更深入醫病關係之後,我發現我與病人之間的關係愈加密切了,而權力落差也更明顯了。我不僅必須討論敏感的問題,還得伸手去觸摸病人。我知道光是說說話並不會傷害到別人的身體,但突然之間,我意識到我這雙探索的手具有做出傷天害理之事的可能性。就在一年級快結束時,我好不容易對訪談有了信心,但學習身體檢查卻又帶來新的、更深的不安全感。雖然上了二年級,每一週都學到更多的臨床技巧,但這種高度的不安全感卻加深了自己不適任的感覺,甚至蓋住了我的成就感。」讀到這裡,的確令人不得不佩服哈佛大學醫學院為了培養出仁心仁術的良醫,用心良苦地設計出如此有心的課程。
書名為《白袍》,作者也多次描述到她穿上這身白袍的心理變化。她發現白袍使她對病人產生一種權威,但也使自己感受到沉重的責任感。在小兒科的實習裡,她因為脫下了白袍而悟出「雖然在歸屬感還不完全的世界裡,我把白袍視為是群體性與合法性的護身符,但我愈來愈不喜歡它加諸在醫病關係上的拘束感。我覺得它讓我比較不人性化,比較定型。一旦我和病人建立起關係,白袍的重要性就退隱到幕後了,不過我還是比較喜歡輕鬆一點的方式。脫下了白袍、看不出長短的差別、也沒有鼓鼓的口袋可供辨別,想要一眼就判定層級的高低,也就變得比較困難了。諷刺的是,卸下了白袍,我反而覺得更能融入整個醫療世界中。」而最後在書中的結尾,作者很感性地說,「我曾經非常喜歡電視節目『急診室的春天』,但現在我偶爾看到時,卻只會注意到其中不實或有錯的地方。我不禁自問,我自己像不像一個醫師?我不敢肯定。但為了讓自己扮演醫師與醫療照顧者的角色更稱職,我猜想我的成長永遠沒有止息的一天。」
最後我想錄下一段作者對學醫這條路所引起的思索,而這使我更相信,學醫這條路最好還是在大學畢業後才開始,這樣比較能培養出心智成熟的醫生。「醫學院念了一年半的這個關頭,我遇到了個人的價值觀及目標與病人的信念相衝突的狀況。我想要了解,如何才能維護病人的價值觀並保護他們的自主權。隨著過去十年來,醫療關係愈來愈以病人為導向之後,我們所面臨的挑戰也愈來愈明顯。為了保護病人的價值觀,我願意做出多大程度的妥協?做出妥協對我來說有多困難?……大學時代是我的自我探索與個人成長的階段。我知道了自己的界限在哪裡,設定了自我規範,也發展出自己的一套價值觀。進入醫學院後,我那套價值觀不夠用了,我得學會讓自己的價值觀與病人的信念互相吻合,並且讓他們的目標實現,同時又不需要犧牲自己的。念大學時,我很努力地想找到自我;現在,我想知道,在別人之所以成為別人的環境裡,我會變成什麼樣。……醫學並未允許我們把病人放在我們的道德標準下檢視。我們必須學會把自己的偏見擱置一旁。」
我深信羅絲曼醫師學醫的心路歷程,可以幫忙醫學生保留他們那分赤子關愛之心,也可以喚醒醫生們自己當年初入醫學殿堂時的那分天真敏感的心,更可以幫忙許多想要學醫,但又不知道這條路是否適合他們的年輕學子。我甚至認為社會大眾也可以藉由這本書了解醫生的養成教育,而更能醫病彼此體恤,共創更好的醫療環境。
前言
白袍
「你絕對不可能猜到我剛才做了什麼事,」羅伊在電話那頭說。他在門診跟著一位主治醫師看診,剛從那兒回來。
羅伊是我們班第一個幫病人做直腸觸診、檢查攝護腺的同學。事實上,除了量血壓之外,那也是大家所執行的第一種檢查程序。那位先生在這次看診中要接受三次檢查──一次由醫師動手,另外兩次由醫學生上陣。這種經驗固然讓病人不太自在,而羅伊也是同樣尷尬。
我把羅伊的事告訴我母親,她很懷疑病人怎麼會答應讓初出茅廬的生手來動他的攝護腺。「病人真的『願意』嗎?」
唯一可以解釋病人之所以會願意的理由,就是羅伊那身白袍。在穿了幾個月的白袍之後,我也已經習慣於病人對我的信任,其實我的能力跟病人的信任完全不成比例。我有個同學在看診時,因為對病人被診斷出的那種病症不熟,只好問:「嗯,你可不可以多告訴我一點這種病到底是怎麼回事?」
病人回他:「我還在等你告訴我咧。」
我們的白袍(胸前印著深紅色書寫體「哈佛醫學院」)是在醫學院新生訓練第一天的白袍典禮上領到的。我們霍姆斯學會(Holmes Society)的白袍典禮一點也不莊嚴隆重。為了行政上的理由,我們班被隨意分成四組(編按:哈佛醫學院實施小班教學制。這四組依美國醫學史上有名的四巨頭Canon、Castle、Peabody和Holmes而命名),每組舉辦各自的典禮,之後一起午餐。大家第一次穿上嶄新的實驗室白袍,都有點忸怩,不時打量別人穿白袍的模樣。之前在學會辦公室外大家歪歪斜斜的排隊領白袍,我排在倒數幾個。等輪到我時,所有小號的都發完了,我領到的那件大了好幾號。
「你可以自己跟別人換,」行政助理說。
穿著剛拆封、還有折痕的白袍一天之後,我們以醫療界正式成員的身分,首次參與門診。
白袍典禮是學校行政單位想出來的新點子,目的是希望在我們踏入醫學院的第一天,為我們宣示醫學生涯就此開展。雖然這件白袍不像一般醫師或住院醫師的那麼長,但它標誌著我們與醫學的密切關係,同時把我們與一般民眾及義工區分開來。
身為一年級的醫學生,我還沒有準備好接受這種關係。上了一整年的課(包括解剖學、藥理學、生物化學、生理學、遺傳學與胚胎學)之後,我的感想是「學,然後知不足」。但是在每個禮拜一的「病人—醫生課程」(Patient-Doctor course,編按:以下簡稱病醫課)中,我發現自己還是穿著白袍繼續訪談著一個又一個的病人。
儘管我在醫學界中的定位不明,但我的白袍依舊引領我走入醫病之間高深莫測的陌生國度。對我的病人而言,白袍代表的就是一般大眾賦予醫師的權威與信任。大部分的病人並不了解,不同的白袍長度代表著不同的醫療階級。白袍就是白袍。大家壓根兒就不管我的白袍明白地昭示著我只不過是個醫學生。我覺得自己好像被烙上了「紅字」〔編按:出自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的小說《紅字》(The Scarlet Letter)〕,但沒有人知道那代表什麼意思。
每個禮拜的訪談是病醫課的一部分,目的是學習面對病人時的重要詢問技巧、正確的態度以及適切的回應。老師教我們有條不紊、仔細地記錄病史,這一點我每週都在不同的病人身上如法炮製,多少有點熟練了。雖然每個禮拜與病人互動的目的是要問出病人的病史,但實際上不如說是我們藉著訪談來學習。上完病醫課,和同學從醫院走回醫學院的途中,安蒂亞發表感想:「實在很討厭耶。我老是在想接下來要問病人什麼問題,根本沒辦法專心聽病人講病情。你想這個情況有沒有可能改善?」
我每次和病人訪談時,他們都會看著我的白袍。我的許多病人都是七十多歲的老人了,二十二歲的我,在他們眼裡一定像個孩子一樣,但這身白袍掩飾了我的青澀,遮蔽了我的生疏,也罩住了我的不安。然而,在醫學的世界裡,我並不因為能夠藏身在白袍之後而覺得輕鬆,白袍反而迫使我去行使我還沒準備好要接受的權力。
穿上白袍,我可以恣意地發問,病人也會覺得自己有義務要回答。他們相信我會不帶批判地傾聽他們的故事,了解他們的症狀與痛苦,並且心懷同情。我從他們私人的問題中蒐集資訊,詢問他們身心生活中最深沉私密的部分。然而他們卻對我一無所知。
此外,這種每週的互動雖然賜予我們權力,卻沒有附帶任何責任。每個禮拜,我帶著幾頁胡亂塗寫的潦草筆記離開病人的房間,然後一去不復返。病人的生活,以及我們之間的互動,最後都濃縮在我的塗鴉中。我完全不需要負責照顧病人,我往後的義務就僅限於保守病人的祕密而已。
在進醫學院之前,要我答應讓醫學生幫我檢查直腸,這種事根本想都別想。不過那一襲白袍可能也愚弄過從前的我。雖然我非常感謝這些病人,讓我有機會可以學會如何訪談以及執行簡單的檢查程序,但我更期待有朝一日,能夠具備真才實學來服務他們。我期待能快點成長,配得上我的白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