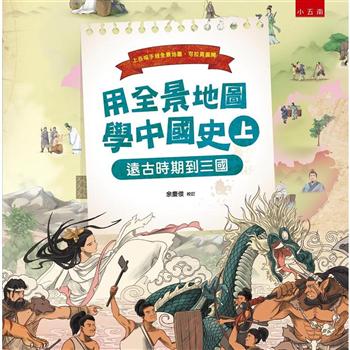一顆檸檬 暗戀的酸澀
週五下午,秋季的落日映紅了半邊天空。
從高一二班的教室看出去,可以看見籃球場,最後一扇窗戶的視野最好。
周安然打掃到最後一扇窗戶附近時,動作停了停,抬頭朝窗外望去。
教學大樓離球場不算近,籃球場上肆意奔跑的少年們,被距離模糊了身形樣貌,遠遠望過去,像是在不停跑動的藍白線條小人。
周安然自認對那個人的身形和樣貌已經十分熟悉,卻也沒辦法在這一堆線條小人中辨認出他。
她收回目光,視線又落向第二組第六排左邊的位子。
位子早就空了。
桌上的書籍沒擺整齊,但也稱不上亂,和它的主人一樣,是所有老師眼中的好學生,卻又不是特別規矩的。
一下課,他經常走得比誰都積極,黑色的書包常常散漫地只掛在一側肩膀上。
因為嫌麻煩,別說班級幹部了,就連小老師都不肯當。
「然然,妳掃好了嗎?」嚴星茜的聲音突然響起。
周安然回過神:「快好啦。」
把清理好的垃圾拿去倒掉後,周安然和嚴星茜的任務就算完成。
兩人回到課桌前收拾書包,嚴星茜回頭看坐在身後的同學:「賀明宇,你還不走啊?」
後桌的男生戴著一副眼鏡,正低頭寫著試卷,聞言抬頭看她們一眼:「等一下就走。」
「那我們先走啦。」嚴星茜也沒再多說,「走吧,然然。」
二班在二樓,周安然挽著她的手下樓。
她父母和嚴星茜的父母是好友,兩個人住在同一個社區,從小一起玩到大。
她們回社區的公車,要在學校的東門外搭乘。而從教學大樓走去東門,是需要經過籃球場的。
想到等一下還能再見到他,周安然頓時感到雀躍,腳步也輕快了一些,就連肩上沉甸甸的書包好像都輕盈了不少。
在球場上,他永遠是最引人矚目的一道風景。
過路的許多學生,無論男女,常常會不自覺地望過去。
周安然混在其中,也就不算顯眼。
這是她一週之內少有的幾次機會,可以在這時候大大方方又不引人注意地注視著他。
樓梯下了一半,嚴星茜想問周安然要不要買杯奶茶再回去,一偏頭就看見旁邊的女生睫毛長而捲翹,嘴角微微翹起,白得近乎發光的臉頰上溢出一個小小的梨渦。
認識這麼多年,嚴星茜還是時不時會被她這副模樣甜到。
只是學校在髮型和著裝上都有要求,周安然向來乖巧聽話,不會刻意打扮自己,臉上還有點嬰兒肥,性格溫順不愛出風頭,在班上就沒那麼顯眼。
嚴星茜不由多看了幾秒。
隨著往下走的動作,周安然嘴邊的小梨渦被快齊肩的頭髮遮住一下,又露出,然後再遮住。
「然然。」嚴星茜晃了晃她的手,「怎麼回事,妳今天好像特別開心?」
周安然的心跳快了一拍:「要放假了,妳不開心嗎?」
「當然開心啊。」嚴星茜繼續盯著她,「但感覺妳今天比平要更開心一點。」
周安然撇開視線:「我媽媽說今晚會做虎皮雞爪,晚上我再送過去給妳。」
嚴星茜最愛周安然的媽媽做的虎皮雞爪,立刻轉移注意力:「然然我愛妳,也愛阿姨。」
出了教學大樓,周安然和嚴星茜繼續有一搭沒一搭地聊著天。不久後,籃球場便撞入了視線。
二中的籃球場非常寬敞,被紅白線條切割成六個標準的場地。
她的視線不自覺先落向第一排第三個球場。
距離慢慢拉近,場上奔跑的少年們不再是模糊的藍白線條,已經能分辨出更具體一點的模樣。
有手長腳長的瘦高個兒,也有身材魁梧一點的,還有頭髮長到大概馬上就要被老師教訓的,以及為了省事,乾脆理成寸頭的。
但都不是他,沒有一個人是他。
哪怕看不清面容,周安然依舊能輕易分辨出,他不在這個球場裡。
她不死心地看向其他球場,卻都沒有看見他的身影。
心裡像是空了一小塊,書包也重新變得沉甸甸的。
有兩個女生在球場邊駐足幾秒後直接離開,朝著她們的方向走來。
擦肩而過的時候,周安然聽見她們的說話聲:
「陳洛白今天怎麼沒在球場啊,他不是每週的這個時間都會留在學校打一會兒籃球嗎?」
「就是說啊,我還以為今天能見到他呢,都好幾天沒看到他了。」
「胡說,妳昨天不是還裝作路過他們教室門口,偷偷去看他了嗎?」
「畢竟最近都沒能看到他嘛。」
語氣和周安然此刻的心情一樣,既失落又悵惘。
她也以為今天還能再見他一面。
明明在下課的時候聽見他說要和朋友一起去打球。
確認他不在球場後,周安然收回視線,心不在焉地看向地面,直到看見嚴星茜的手在她眼前晃了晃,「然然。」
周安然偏頭:「怎麼啦?」
嚴星茜:「我才想問妳怎麼了,剛才明明還很開心,現在又垂頭喪氣的,我和妳說話都沒反應。」
周安然抿抿唇:「妳剛剛和我說什麼了?」
嚴星茜:「問妳要不要買杯奶茶再回去?」
周安然有些愧疚於剛才沉浸在自己的思緒裡,沒認真聽好友說話,她點點頭:「去吧,我請客。」
「太好了!」嚴星茜的性格正好和她相反,大大咧咧的,也沒多想,「正好我這個月零用錢沒剩多少了。」
周安然繼續和她邊走邊聊,二人在經過球場時,她又不由自主地抬頭看了第一排第三個球場一眼,認出場上有一些熟悉的面孔,一個是三班的,剩下幾個都是平常和陳洛白玩在一起的人。
因為和陳洛白玩在一起,她才會覺得熟悉。
但他朋友明明都在打球,他為什麼會不在呢?
周安然不免又開始心不在焉,所以等那句「同學小心」遠遠傳過來的時候,她慢了半拍才抬起頭。
橙紅色的籃球幾乎已經要砸到她面前。
要躲似乎也來不及了。猝不及防的周安然愣在原地,等著劇痛到來。
幾乎是在同一時間,某種清爽的洗衣精香味頓時侵襲鼻間,一隻冷白修長的手從旁伸過來,攔住了那顆近在眼前的籃球。
只有不到兩公分的距離。
周安然可以清楚看見那隻大手上細細的絨毛,和因為用力而微微凸起的青筋,還有腕骨上方那顆她不經意隔著或近或遠的距離,瞥見過幾次、足以讓她瞬間辨認出他身分的小痣,這次終於近在眼前。
原來不是黑色的,而是偏褐色的一小顆。
周安然的心跳倏然亂了節奏。
伴隨著只有她自己聽得見的心跳聲,那隻手的主人的聲音也在她耳邊響起。那聲音比同齡人的聲線還要低沉,卻又帶著幾分少年人特有的清朗。
「差一點砸到女生也不道歉。」
球場那邊的聲音交雜在一起:
「洛哥,你終於來了,等你好久了,還打嗎?」語氣熱絡的。
「抱歉啊,同學。」略帶敷衍的。
「阿洛,老高叫你過去做什麼?」好奇的。
原來臨時被班導叫走了嗎?
周安然的心跳快得厲害,垂在一側的手指蜷了蜷,有點想偏頭去看他的模樣。
嚴星茜剛才也被嚇到,此刻才反應過來,拉著她往旁邊退了兩步,又衝著球場那邊吼:「你們打球不會看一下啊!」
周安然安撫似地拍了拍她的手,到底還是沒忍住,偏頭看向他。
南城的四季不分明。已經進入十月下旬,天氣還熱得厲害,全校大部分的人都還穿著夏季制服。
但有些人好像生來就受上帝偏寵。
男生的身形高挑頎長,二中寬鬆的藍白制服穿在他身上,顯得格外乾淨清爽,被夕陽鍍了一小層金邊的側臉線條流暢俐落,睫毛黑而長,雙眼皮的褶皺很深。
那顆差點砸到她的籃球被他抓在手裡,又抬起隨便轉了兩下,男生的笑容懶洋洋的,目光盯著球場那邊,沒有一絲一毫落到她身上。
周安然高高懸起的心重重落下,被密密的失落重新填滿。
但她不該失落,她應該預知到這一幕才對。
她應該知道他剛才幫助她的行為,只是他刻在骨子裡的教養,至於被他幫助的到底是路人甲還是路人乙,他可能並不在意。
畢竟這不是她第一次受他幫助。
高一報到的那天,正好撞上嚴星茜爺爺的七十大壽,她早早就跟老師請好假,要晚兩天才能過來報到。
周安然的父母那天也有工作,她沒讓他們特意請假來送她,而是獨自來了二中報到。
辦理手續的地方在辦公樓二樓,她來得早,還不見其他人的蹤影。
那天南城下著大雨。周安然慢吞吞地上樓,上完最後一階樓梯,不知是哪個沒素質的人把香蕉皮丟在地上,她沒注意就踩上去,雨天地面又溼又滑,整個人站不住地往後倒。
然後,她跌進了一個灼熱有力的懷抱中,清爽的氣息鋪天蓋地地襲來。
略低的男聲在她耳邊響起:「小心。」
周安然偏過頭,目光撞進一雙狹長漆黑的眼眸中。
一顆腦袋從三樓附近的樓梯扶手邊探出來,有人朝著她這邊大喊:「陳洛白,你快一點。」
像是看清他們此刻的姿勢,對方臉上多了打趣的笑意:「搞什麼,我他媽等你半天了,你居然在這裡勾搭女生,這就抱上了?速度夠快啊。」
周安然的臉微微一熱,也不知道有沒有紅。
旁邊的男生卻像是完全沒注意到她的反應,一將她扶穩後,就迅速鬆開手,抬頭看向三樓附近的那顆腦袋,笑罵道:「有病啊,人家差點摔倒了,我隨手扶一把,你長了嘴就只會用來亂說嗎?」
他穿著簡單的白色T恤和黑色運動褲,黑色的碎髮搭在額前,顯得清爽又乾淨,笑起來的時候,周身有一股壓不住的蓬勃少年氣息。
「那你倒是快上來啊。」
直到三樓的人再次開口,周安然才想起她似乎該向他道謝,但男生卻沒給她這個機會。
他沒再停留,更沒再多看她一眼,轉身大步跨上階梯。
突然起了風,緊臨著二樓的香樟樹被吹得颯颯作響,雨滴順著翠綠的枝葉往下滴落。
周安然在風雨聲中抬起頭,只來得及看見一個奔跑的頎長背影,和被風吹起的白色衣角。
那天,周安然紅著臉在原地站了好久。後腰那一片皮膚都在發燙,像是那隻灼熱有力的手,仍隔著夏末單薄的衣服摟在上面。
心跳快得厲害,腦中全是剛才看見的那張臉。
周安然抿抿唇,突然轉身快步下樓。
她折返回公告欄前,從分班表第一行開始看起。直到她發現剛才聽到的那個名字,就在他們班上的時候,她有種被巨大驚喜砸中的感覺。
她以為高中是會比國中更難熬,除了讀書只剩讀書的一段時間。陳洛白卻像是突然出現的一道光,照亮她灰撲撲的青春。
可惜這道光太耀眼。
說得誇張一點,他幾乎快照亮二中一半女生的青春了,讓人可望不可及。
而周安然能跟他同班,或許已經耗盡了自己的運氣,後來班上安排座位,她和他一前一後,一左一右,隔了遠遠的距離。
加上她性格內向,開學已經一個多月,也幾乎沒能和他說上話,頂多只能算是多打過幾次照面的陌生人。
「不好意思啊。」球場上又有聲音傳來。
說話的是他們班的一個男生,叫祝燃,是陳洛白關係最好的朋友之一。
周安然從回憶中回過神,想起自己還沒跟他道謝。她張了張嘴,沒來得及開口,祝燃的聲音再次響起,「陳洛白,你還站在那裡幹嘛,快過來打球啊。」
陳洛白的手上還拿著剛才差點砸到她的那顆球,像是習慣性地隨手轉了幾下:「今天不打了,我媽過來接我。」
「別啊,洛哥。我們今晚都還等著和你一起吃飯呢。」另一個叫湯建銳的插話。
陳洛白淡淡地瞥他一眼:「是等我吃飯還是等我結帳啊?」
湯建銳「嘿嘿嘿」地笑了,絲毫沒有覺得不好意思:「都一樣嘛。」
陳洛白朝祝燃那邊揚了揚下巴:「今晚還是我請,叫祝燃先幫你們結帳,我之後再轉給他。」
「那你趕緊走吧。」
「是啊,別讓阿姨久等。」
陳洛白把球砸過去,笑罵:「你們怎麼這麼不要臉?」
男生的手高高揚起,扔球時,手臂因為發力,青筋微微凸起,彰顯著和女孩全然不同的力量感。
周安然不由想起,這隻手在那天穩穩扶住她的感覺,不自覺恍神了一下。
再回神時,陳洛白已經闊步離開,距離她已有好幾步之遙。
接過球的湯建銳在原地運了幾下,又衝著他喊:「下週見啊,洛哥。」
夕陽下,陳洛白頭也不回,只是抬起手朝後面揮了揮,掛在右肩上的黑色雙肩包隨著這個動作輕輕晃悠了下,橙紅的光線也在上面跳躍。
周安然沒勇氣叫住他,到了嘴邊的一句「謝謝」最終還是沒能說出口。
嚴星茜挽住她:「我們也走吧。」
周安然輕輕「嗯」了聲。
走在前方的男生身高腿長,距離越拉越遠。
怎麼就沒能跟他說一聲謝謝呢?周安然有些懊惱地想著。
※
嚴星茜也盯著那個背影看了幾秒,突然道:「然然,我好酸啊。」
周安然努力壓下這股情緒:「酸什麼啊?」
嚴星茜:「酸陳洛白啊。」
周安然:「?」
嚴星茜是個追星女孩,心裡只有她的偶像,是班上極少數不怎麼關注陳洛白的女孩之一,平日她們也很少聊起他。
「妳酸——」周安然頓了頓,本來可以順著話題,直接用「他」代替,但她出於一種說不出的私心,小聲念了一遍他的名字,「妳酸陳洛白做什麼呀?」
「都說上帝幫人關了一扇門,就會再幫人另開一扇窗。反正我是沒看見上帝幫我開的小窗戶,」嚴星茜皺著臉,「但我看見上帝幫陳洛白開了一條通天大道。」
周安然不禁莞爾:「妳這是什麼奇怪的歪理。」
「哪是歪理?妳看嘛,他爸爸是知名企業家,媽媽是知名律師事務所的高級合夥人,外公和外婆都是大學教授,典型的含著金湯匙出生的大少爺。上次月考甩了第二名二三十分。今天老師給我們看他的作文,那一筆字大氣又好看。長相嘛……雖然不是我的菜,但肯定是我們學校的校草,完全不輸給偶像,還勝在清爽乾淨。」
嚴星茜停了停,掰著手指算:「家世、智商、長相,一般人只要占一樣,就能一輩子生活無憂了,他居然同時占了三樣,妳說氣不氣人?」
周安然心裡有些發悶,胡亂應了一句:「是啊。」
就是太優秀了,所以才會讓人望而卻步。
嚴星茜像是又想起了什麼:「啊,對了,聽說我們學校的籃球隊教練當初還想勸他去校隊,我們學校校隊打高中聯賽都是能爭前三的水準,主力多少都有望走職籃道路,教練能看中他,說明他的水準已經和普通人拉開一大截了。」
前面高高瘦瘦的少年步伐很大,和她們的距離已經越來越遠,像是在預示將來她們和他的差距只會越來越大。
嚴星茜這樣沒心沒肺的女孩,像是連這點都能察覺到,長長嘆了口氣:「算了,不說了,越說越酸,我們快去買奶茶吧。」
陳洛白已經出了校門,澈底消失在她眼前。
周安然收回視線:「嗯。」
垂頭走了沒幾步,就聽見旁邊的嚴星茜突然哼起歌:「去你個山更險來水更惡,難也遇過,苦也吃過,走出個通天大道,寬又闊——」
嚴星茜的聲音甜美,唱起來格外有反差感。
周安然笑了起來,心裡悶住的那股氣又散了一些:「怎麼突然哼起這首歌?」
嚴星茜「啊」了聲:「我也不知道,突然就哼了,可能是因為剛剛聊了通天大道,不過還是以前的歌好聽,現在的歌都是些什麼鬼?」
周安然打趣地看向她:「要是妳偶像要出新歌的話呢?」
嚴星茜苦著臉:「別說了,也不知道何年何月才會出新歌。」
周安然到家的時候,兩位家長都還沒回來。
她把書包放在客廳的沙發上,先去廚房洗米煮飯,而後才折回客廳,拎起書包進了自己的房間。
周安然把數學作業拿出來,又從一旁的書架上抽出自己的筆記本,不小心翻開其中一頁時,她的指尖停頓了一秒。
這一整頁紙整整齊齊地寫滿了詩詞。
她的目光卻直接落向第五行、第七行和第九行。
上面的詩句分別是——
『白雲還自散,明月落誰家。』
『芳林新葉催陳葉,流水前波讓後波。』
『誰家玉笛暗飛聲,散入春風滿洛城。』
就連寫他的名字也不敢光明正大,每次都只能這樣小心翼翼地把自己的心思隱藏於其中。
心情好像又複雜了起來。
酸的、甜的、澀的交雜在一起。
都是和他有關的。
但想起下午那個越走越遠的背影,周安然抿抿唇,把複雜的心情壓下去,將筆記本翻到新的空白頁,收斂心神開始寫作業。
雖然有一點難,但還是想要努力一點。
想追上他的步伐,想離他更近一點。
寫到其中一題的時候,周安然的思緒突然卡住,她咬著唇,重新整理思緒,拿在手裡的筆無意識地在筆記本上劃動。
等到她反應過來的時候,小半張紙上已經快寫滿了「通天大道」幾個字。
回家的路上,嚴星茜將這首歌哼了一路。本來只是小時候愛看的電視劇片尾曲,但一和他扯上關係,這幾個字好像也被賦予了不同的意義,沾上那些又酸、又甜、又澀的心情。
|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檸檬汽水糖(上)(首刷限定版)的圖書 |
 |
檸檬汽水糖(上)(首刷限定版) 作者:蘇拾五 出版社:英屬維京群島商高寶國際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出版日期:2024-02-07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檸檬汽水糖(上)(首刷限定版)
你是我青春的代名詞,
也是我難以忘懷的遺憾。
★晉江潛力作家 蘇拾五 治癒愛情力作,收穫無數網友好評!
★天資聰穎‧全能學霸 陳洛白 ╳悄悄追愛‧自卑女孩 周安然
★陳洛白像是夏季的一陣風,抓不住、摸不著,也抱不到。
個性害羞且自卑的周安然,因為一場邂逅,
再也忘不了讓她一眼淪陷的少年——陳洛白。
她用盡整個青春暗戀她,卻因為自己不夠勇敢,
只能眼睜睜看著受眾人追捧的男孩,和其他人越走越近。
她以為這輩子和陳洛白再也沒有交集,
卻在某一天從書包內找到一封情書,而且字跡和陳洛白一模一樣……
周安然在看見落款那一瞬間,心跳逐漸加速,
以為這段暗無天日的暗戀即將迎來終點,
結果卻換來無盡的難堪和羞愧——
「陳洛白怎麼可能寫情書給妳。」
周安然的聲音隱約帶出一絲哭腔,「是啊,他怎麼可能喜歡我。」
作者簡介:
蘇拾五
晉江甜寵小說作家,其筆下人物鮮明,故事扣人心弦。
擅長描繪每個人心中最酸澀難忘的暗戀。
代表作:《我看上你哥啦》、《你這是犯規啊》、《檸檬汽水糖》(高寶書版)。
新浪微博:@苏啊苏拾五
章節試閱
一顆檸檬 暗戀的酸澀
週五下午,秋季的落日映紅了半邊天空。
從高一二班的教室看出去,可以看見籃球場,最後一扇窗戶的視野最好。
周安然打掃到最後一扇窗戶附近時,動作停了停,抬頭朝窗外望去。
教學大樓離球場不算近,籃球場上肆意奔跑的少年們,被距離模糊了身形樣貌,遠遠望過去,像是在不停跑動的藍白線條小人。
周安然自認對那個人的身形和樣貌已經十分熟悉,卻也沒辦法在這一堆線條小人中辨認出他。
她收回目光,視線又落向第二組第六排左邊的位子。
位子早就空了。
桌上的書籍沒擺整齊,但也稱不上亂,和它的主人一樣,是...
週五下午,秋季的落日映紅了半邊天空。
從高一二班的教室看出去,可以看見籃球場,最後一扇窗戶的視野最好。
周安然打掃到最後一扇窗戶附近時,動作停了停,抬頭朝窗外望去。
教學大樓離球場不算近,籃球場上肆意奔跑的少年們,被距離模糊了身形樣貌,遠遠望過去,像是在不停跑動的藍白線條小人。
周安然自認對那個人的身形和樣貌已經十分熟悉,卻也沒辦法在這一堆線條小人中辨認出他。
她收回目光,視線又落向第二組第六排左邊的位子。
位子早就空了。
桌上的書籍沒擺整齊,但也稱不上亂,和它的主人一樣,是...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一顆檸檬 暗戀的酸澀
二顆檸檬 像夏天的風
三顆檸檬 和你並駕齊驅
四顆檸檬 為你伸張正義
五顆檸檬 如果再勇敢一點
六顆檸檬 大膽地靠近你
七顆檸檬 未落款的情書
八顆檸檬 他怎麼可能喜歡我
九顆檸檬 還是年少的你
二顆檸檬 像夏天的風
三顆檸檬 和你並駕齊驅
四顆檸檬 為你伸張正義
五顆檸檬 如果再勇敢一點
六顆檸檬 大膽地靠近你
七顆檸檬 未落款的情書
八顆檸檬 他怎麼可能喜歡我
九顆檸檬 還是年少的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