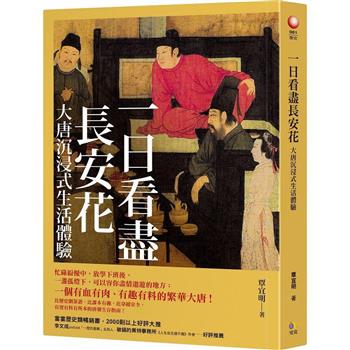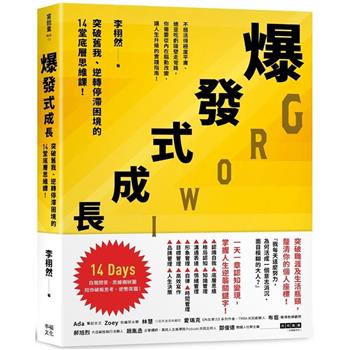作者說,我們現在要回到「何為香港」的問題,「何為香港」即是「What is Hong Kong?」,後面包括「何時香港」、「何處香港」、「如何香港」或者「何如香港」,即是探問香港是怎樣做出來的。
這是一條香港唯一走得通的道路,非常艱難,也可能很漫長,但卻不是不可能的任務。只有破解偏執狂政局,我們香港人才可以結伴走到隧道的出口,共同體的政治才可能邁進良性循環的中道,拒絕最壞的選項,不因為固執單一教條所認可的最好而捨棄「包羅超廣泛利益」的較不壞選項。
我們面前的現實不容樂觀,甚至可以說是很險惡,但此刻我們仍要抱有希望。抱有希望,我們才會願意風雨同路,不離不棄,堅毅忍耐,專注於細緻而不粗暴的據理力爭。
香港人可能已經不相信明天會更好,但我們不能喪失想像明天的能力。
是荒誕,又如何?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是荒誕又如何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210 |
二手中文書 |
$ 332 |
小說/文學 |
$ 395 |
文學作品 |
$ 395 |
中文現代文學 |
$ 465 |
中文書 |
$ 465 |
世界國別史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是荒誕又如何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陳冠中
原籍寧波,上海出生,香港長大,曾住台北六年,現居北京。七六年創辦香港《號外》雜誌。他的其他著作:
1.波希米亞中國(合著)
2.我這一代香港人
3.事後:本土文化誌
4.下一個十年:香港的光榮年代?
5.盛世:中國2013年
6.中國天朝主義與香港
7.香港三部曲
8.建豐二年
陳冠中
原籍寧波,上海出生,香港長大,曾住台北六年,現居北京。七六年創辦香港《號外》雜誌。他的其他著作:
1.波希米亞中國(合著)
2.我這一代香港人
3.事後:本土文化誌
4.下一個十年:香港的光榮年代?
5.盛世:中國2013年
6.中國天朝主義與香港
7.香港三部曲
8.建豐二年
目錄
Ⅰ
3香港未完成的實驗
28建制派的背叛
43香港作為方法之與李歐梵的對話
63愛國者的憲法、公民與歷史教育
Ⅱ
73並行不悖:數齣戲的印跡、幾個人的塵網
94隨想古早味香港
98香港設計的幾個主題
101是荒誕又如何?
104眾妙之合:搞掂心態、工夫精神、創新意識
110後發城市的創新文化發展
135論多樣時尚性與全球化年代時裝的剛性
Ⅲ
147引介許寶強:四九年後的香港左翼
151未然的已然:周俊輝.香港.當代
155吳強的《憂鬱的中產階級》
158亞當.威廉姆斯的《煉金術士之書》
161梁文道的《關鍵字》
163紀念詩人、散文家、小說家也斯
165在北京看守所的日子
168從1978年說起劉天蘭
171艾勁:1992與1997
174給黎堅惠《天空之鏡》的電郵
175鄧小宇的《女人就是女人》
177鄧小宇的《吃羅宋餐的日子》
179馬家輝的《日月》
181沈旭暉的《國際政治夢工場》
185胡晴舫的《辦公室》
187巴宇特的《迷失上海》
190定位與漂移:年輕身體力行者的感覺
195《我這一代香港人》簡體版自序
197綠色+和平
199城市主義者的經濟學
205美國怎麼了?
211全球化:從時髦詞到詛咒
217善的脆弱性與人類生活的基本條件
225後 記
3香港未完成的實驗
28建制派的背叛
43香港作為方法之與李歐梵的對話
63愛國者的憲法、公民與歷史教育
Ⅱ
73並行不悖:數齣戲的印跡、幾個人的塵網
94隨想古早味香港
98香港設計的幾個主題
101是荒誕又如何?
104眾妙之合:搞掂心態、工夫精神、創新意識
110後發城市的創新文化發展
135論多樣時尚性與全球化年代時裝的剛性
Ⅲ
147引介許寶強:四九年後的香港左翼
151未然的已然:周俊輝.香港.當代
155吳強的《憂鬱的中產階級》
158亞當.威廉姆斯的《煉金術士之書》
161梁文道的《關鍵字》
163紀念詩人、散文家、小說家也斯
165在北京看守所的日子
168從1978年說起劉天蘭
171艾勁:1992與1997
174給黎堅惠《天空之鏡》的電郵
175鄧小宇的《女人就是女人》
177鄧小宇的《吃羅宋餐的日子》
179馬家輝的《日月》
181沈旭暉的《國際政治夢工場》
185胡晴舫的《辦公室》
187巴宇特的《迷失上海》
190定位與漂移:年輕身體力行者的感覺
195《我這一代香港人》簡體版自序
197綠色+和平
199城市主義者的經濟學
205美國怎麼了?
211全球化:從時髦詞到詛咒
217善的脆弱性與人類生活的基本條件
225後 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