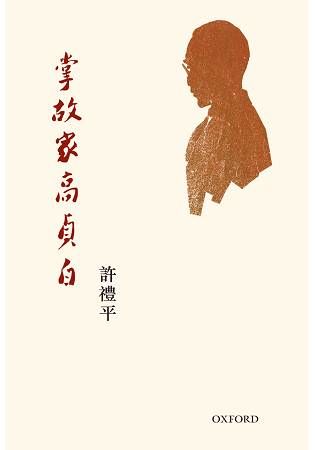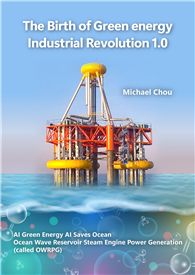作者 高貞白又名高伯雨
中國現代最重要的掌故家之一。祖父楚香、父親舜琴經營名號元發行、元章盛、元得利等南北行生意。家底豐厚,不愁衣食,跟名家習書畫、學篆刻,遊學英國。在上海與唐雲笙(唐大郎)、王辛笛等往來,開始從事寫作。編過報紙副刊,五十年代開始為報紙寫專欄「望海樓雜筆」「聽雨樓隨筆」等,一寫就是五十多年。譯寫有《英使謁見乾隆記實》《紫禁城的黃昏》。一九六六年三月,創辦《大華》半月刊,一九六八年停刊後,一九七○年一月復刊為月刊,《聽雨樓隨筆》十卷已結集出版。
徐亮之:伯雨為文如其為學,為學如其為人。其為人,溫而毅,直而婉;不信不言,不果不行;用其文其學,博而不雜,精而不執;深而不刻,淺而不薄;大而不無當,泛而不無歸。──友人中吾未見有如伯雨者也。
瞿兌之:在中國的史書中,往往只看見興亡大事的記載,或者官式的表面記錄,而當時人們實際上是怎樣活動的,只有從其他的來源中才能體會到。這就使得從事掌故學的人要負起相當重的責任了。我翻閱高先生的聽雨樓隨筆,覺得字字精采,至今不厭重讀。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掌故家高貞白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240 |
二手中文書 |
$ 403 |
社會人文 |
$ 437 |
中國當代人物 |
$ 474 |
中文書 |
$ 474 |
社會人物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掌故家高貞白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許禮平
《舊日風雲》正續集的作者,一九五二年生於澳門,廣東揭陽人。少無大志,唯雅好翰墨。早歲在東瀛編纂《貨幣書目知見錄》、《中國語文索引》 ,七十年代為香港中文大學編《中國語文研究》,八十年代創辦問學社、翰墨軒,九十年代創辦《名家翰墨》月刊、叢刊。復嗜鑑賞,以文物蒐羅為養志之需。
許禮平
《舊日風雲》正續集的作者,一九五二年生於澳門,廣東揭陽人。少無大志,唯雅好翰墨。早歲在東瀛編纂《貨幣書目知見錄》、《中國語文索引》 ,七十年代為香港中文大學編《中國語文研究》,八十年代創辦問學社、翰墨軒,九十年代創辦《名家翰墨》月刊、叢刊。復嗜鑑賞,以文物蒐羅為養志之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