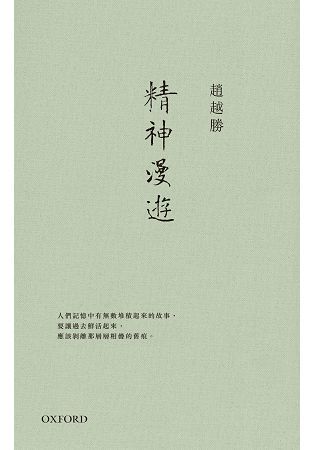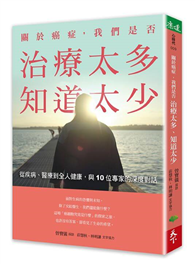這是《燃燈者》一書的作者趙越勝第二部散文集。
如揚之水(趙麗雅)所說,趙越勝的文字好看,激情是它的特色之一,談文學,談音樂,都如此。又因為作者的專業本是哲學,有沉靜、睿智為底色,激情便從不至於「文藝化」。不論音樂與文學,評論,大多是「外國的月亮」,卻又懷抱了「一顆中國心」,創意造言,每取自中國古典文學的寶庫。於是古今中外融為一爐,一枝筆或挾風霜,或染五色,雨驚雲落,星斗交輝,引領看官歌哭於精神漫遊之所。這是它獨特的魅力,而且保持至今。
| FindBook |
有 3 項符合
精神漫遊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371 |
文學 |
$ 437 |
中文書 |
$ 437 |
現代散文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精神漫遊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趙越勝
人文學者。1978年進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參加籌辦《國內哲學動態》。1979年進社科院研究生院,讀現代西方哲學,後獲碩士學位。1982年進社科院哲學研究所現代西方哲學研究室。其創辦的文化沙龍,對1980年代中國大陸影響深遠。為「文化:中國與世界」編委會核心成員。1989年,移居法國。著有《燃燈者》等。
趙越勝
人文學者。1978年進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參加籌辦《國內哲學動態》。1979年進社科院研究生院,讀現代西方哲學,後獲碩士學位。1982年進社科院哲學研究所現代西方哲學研究室。其創辦的文化沙龍,對1980年代中國大陸影響深遠。為「文化:中國與世界」編委會核心成員。1989年,移居法國。著有《燃燈者》等。
目錄
好看(趙麗雅) ix
《精神漫遊》的漫遊 1
純潔的自殺 17
永恆的困惑 29
走向無壓抑的文明 43
單面人與單面思想 57
土地的歌唱 79
語言就是語言 91
詩的智慧 103
瀆神與缺席 125
滄海月明珠有淚 159
動盪時代的心魂 179
《隨想》與隨意 235
《精神》獻辭 247
《精神漫遊》的漫遊 1
純潔的自殺 17
永恆的困惑 29
走向無壓抑的文明 43
單面人與單面思想 57
土地的歌唱 79
語言就是語言 91
詩的智慧 103
瀆神與缺席 125
滄海月明珠有淚 159
動盪時代的心魂 179
《隨想》與隨意 235
《精神》獻辭 247
序
推薦序
好看 趙麗雅
越勝打電話來,說他舊年寫下的「精神漫遊」即將結集出版,因以作序為囑,理由是當年在《讀書》連載的時候,專欄的這一名稱是和我一起商定的。「有這麼回事嗎?」我已渾然不記。而我記憶力從來不好,不僅開設專欄的經過,且連越勝討論的書,也幾乎沒有留下印象,雖然那時候多是讀過並且很有些感想的。
檢閱日記,與越勝聯繫密切的一年是一九八八年,初識大約也是這一年。三月一日的日記中記道:下午周國平、趙越勝到編輯部來。「趙較周健談得多,周嘗稱趙是一團意識,確乎如此。他酷愛音樂,家中唱片無算,哲學意識便緣自音樂感受,而音樂感受又滲入的是哲學意識。
他絕對忍受不了沒有藝術的生活,因而工業文明(技術時代)的前景就顯得格外可怕」。又同年五月十九日裏有這樣一段:日前嘗致簡越勝論詩,趙覆函曰:「與其用這許多理論表達把詩弄成一個大而無當的概念,不如乾脆把詩看作『無』。這樣,徹底的空泛走到了它的反面,『無』成了一個最具體的概念。萊布尼茨問道:『萬物皆在,為什麼偏偏無不在』?這真是振聾發聵的一問。一切皆在,無自然在,無不在,則無物在。這從空間和時間上看都有充分的根據。詩在希臘的含義便是『使⋯⋯在場』,『使⋯⋯現相』,也就是『無中生有』。」我曾如何「論詩」,早就不復記憶,當年看到越勝覆信中的文字,或也是「一團意識」的感覺罷。關於稿件往來,日記裏也有不多的幾段記述。——九月五日:下午趙越勝打電話來,說本來準備動手寫第三篇稿子《純潔的自殺》,但由於朱正琳一家的離去(他們到北京來玩,在越勝家住了十幾天)而感到悵然若有所失,以至於悲從中來,被一種無可名狀而又難以自拔的悲愁苦悶牢牢攫住(強為之名,可謂「畏」吧),無法舉筆。到了晚間,又接到趙的電話,他說,第五個開頭(前四個已進了字紙簍)已經擬就,並馬上唸給我聽。又,九月十日:到趙越勝家送書,他給我唸了剛剛完成草稿的《純潔的自殺》。——雖然往事保存在記憶裏的已經不多,不過總還記得當日越勝逢有新作成篇,都要打電話來講述文章大要,並且挑幾個得意的段落誦讀一番。
今天重溫越勝的文字,最覺熟悉的便是聽他朗誦過的片段。而對於作者來說,這裏隱含一點成功的喜悅,卻更是一種鍛煉文字的方法,即以上口與否,檢閱文字的節奏韻律。以此記起暢安先生也每每如此,可以說是一種習慣,也可以說是一縷古風。
好看,是當年我在《讀書》的時候,與內容並列的審稿標準,當然首先是主編的意旨,而被我們「融化在血液中,落實在行動上」。那時候在辦公室裏與吳彬坐對面,誰得獲一份好看的稿件,便常常是一個重要話題,並且為此興奮不已。至於好看的標準是怎樣的,《讀書》的作者和讀者都相與會心。
越勝的文字屬於好看一類,激情是它的特色之一,談文學,談音樂,都是如此。又因為作者的專業本是哲學,有沉靜、睿智或者說哲學的批判為底色,激情便從不至於「文藝化」。不論音樂與文學,評論所及,大多是「外國的月亮」,卻又懷抱了「一顆中國心」,創意造言,每取自中國古典文學的寶庫。於是古今中外融為一爐,一枝筆或挾風霜,或染五色,雨驚雲落,星斗交輝,引領看官歌哭於精神漫遊之所。這是它獨特的魅力,而且保持至今。
《牡丹亭》的《驚夢》一折裏有一段人人熟悉的唱詞:「嫋晴絲吹來閒庭院,搖漾春如線。停半晌,整花鈿,沒揣菱花,偷人半面,迤逗的彩雲偏。步香閨怎便把全身現。你道翠生生出落的裙衫兒茜,豔晶晶花簪八寶填,可知我一生兒愛好是天然。恰三春好處無人見,不隄防沉魚落雁鳥驚喧。則怕的羞花閉月花愁顫。」「一生兒愛好是天然」,通常讀「好」為四聲,獨朱英誕《李長吉評傳》整理者之一李均在該書「出版說明」中道,「『美』又即是『好』,如《牡丹亭》裏杜麗娘唱『可知我一生兒愛好是天然』,人皆以為杜麗娘愛『天然』,其實是愛『好』也」(海豚出版社二〇一二年)。這是令人十分贊同的意見。愛好」,唯美是務也。越勝便最是懂得精神世界裏的「好」,並且能夠用「好」的文字說出來。
當然另一面則是不能容忍對「好」的褻瀆和毀滅。此際忽然想起一則古人筆記中語:「元稹為翰林承旨,朝退,行鍾廊,時初日映九英梅,隙光射稹,有氣勃然,百寮望之曰:『豈腸胃文章映日可見乎。』」這本筆記裏的紀事多不可信,卻是偏多生新之意象而每教人生出歡喜,這一段文字,即很想移贈於越勝。
其實越勝的文字之好,思之深湛,本無須我妄置一詞,遠離萬水千山選中我來作序,我想,更多的是一位《讀書》的作者憶念他和《讀書》在一起的時代以及因此結下的情份,情份究竟有多深,無法測量,卻是隔了近三十年的時光,依然觸手可及。
好看 趙麗雅
越勝打電話來,說他舊年寫下的「精神漫遊」即將結集出版,因以作序為囑,理由是當年在《讀書》連載的時候,專欄的這一名稱是和我一起商定的。「有這麼回事嗎?」我已渾然不記。而我記憶力從來不好,不僅開設專欄的經過,且連越勝討論的書,也幾乎沒有留下印象,雖然那時候多是讀過並且很有些感想的。
檢閱日記,與越勝聯繫密切的一年是一九八八年,初識大約也是這一年。三月一日的日記中記道:下午周國平、趙越勝到編輯部來。「趙較周健談得多,周嘗稱趙是一團意識,確乎如此。他酷愛音樂,家中唱片無算,哲學意識便緣自音樂感受,而音樂感受又滲入的是哲學意識。
他絕對忍受不了沒有藝術的生活,因而工業文明(技術時代)的前景就顯得格外可怕」。又同年五月十九日裏有這樣一段:日前嘗致簡越勝論詩,趙覆函曰:「與其用這許多理論表達把詩弄成一個大而無當的概念,不如乾脆把詩看作『無』。這樣,徹底的空泛走到了它的反面,『無』成了一個最具體的概念。萊布尼茨問道:『萬物皆在,為什麼偏偏無不在』?這真是振聾發聵的一問。一切皆在,無自然在,無不在,則無物在。這從空間和時間上看都有充分的根據。詩在希臘的含義便是『使⋯⋯在場』,『使⋯⋯現相』,也就是『無中生有』。」我曾如何「論詩」,早就不復記憶,當年看到越勝覆信中的文字,或也是「一團意識」的感覺罷。關於稿件往來,日記裏也有不多的幾段記述。——九月五日:下午趙越勝打電話來,說本來準備動手寫第三篇稿子《純潔的自殺》,但由於朱正琳一家的離去(他們到北京來玩,在越勝家住了十幾天)而感到悵然若有所失,以至於悲從中來,被一種無可名狀而又難以自拔的悲愁苦悶牢牢攫住(強為之名,可謂「畏」吧),無法舉筆。到了晚間,又接到趙的電話,他說,第五個開頭(前四個已進了字紙簍)已經擬就,並馬上唸給我聽。又,九月十日:到趙越勝家送書,他給我唸了剛剛完成草稿的《純潔的自殺》。——雖然往事保存在記憶裏的已經不多,不過總還記得當日越勝逢有新作成篇,都要打電話來講述文章大要,並且挑幾個得意的段落誦讀一番。
今天重溫越勝的文字,最覺熟悉的便是聽他朗誦過的片段。而對於作者來說,這裏隱含一點成功的喜悅,卻更是一種鍛煉文字的方法,即以上口與否,檢閱文字的節奏韻律。以此記起暢安先生也每每如此,可以說是一種習慣,也可以說是一縷古風。
好看,是當年我在《讀書》的時候,與內容並列的審稿標準,當然首先是主編的意旨,而被我們「融化在血液中,落實在行動上」。那時候在辦公室裏與吳彬坐對面,誰得獲一份好看的稿件,便常常是一個重要話題,並且為此興奮不已。至於好看的標準是怎樣的,《讀書》的作者和讀者都相與會心。
越勝的文字屬於好看一類,激情是它的特色之一,談文學,談音樂,都是如此。又因為作者的專業本是哲學,有沉靜、睿智或者說哲學的批判為底色,激情便從不至於「文藝化」。不論音樂與文學,評論所及,大多是「外國的月亮」,卻又懷抱了「一顆中國心」,創意造言,每取自中國古典文學的寶庫。於是古今中外融為一爐,一枝筆或挾風霜,或染五色,雨驚雲落,星斗交輝,引領看官歌哭於精神漫遊之所。這是它獨特的魅力,而且保持至今。
《牡丹亭》的《驚夢》一折裏有一段人人熟悉的唱詞:「嫋晴絲吹來閒庭院,搖漾春如線。停半晌,整花鈿,沒揣菱花,偷人半面,迤逗的彩雲偏。步香閨怎便把全身現。你道翠生生出落的裙衫兒茜,豔晶晶花簪八寶填,可知我一生兒愛好是天然。恰三春好處無人見,不隄防沉魚落雁鳥驚喧。則怕的羞花閉月花愁顫。」「一生兒愛好是天然」,通常讀「好」為四聲,獨朱英誕《李長吉評傳》整理者之一李均在該書「出版說明」中道,「『美』又即是『好』,如《牡丹亭》裏杜麗娘唱『可知我一生兒愛好是天然』,人皆以為杜麗娘愛『天然』,其實是愛『好』也」(海豚出版社二〇一二年)。這是令人十分贊同的意見。愛好」,唯美是務也。越勝便最是懂得精神世界裏的「好」,並且能夠用「好」的文字說出來。
當然另一面則是不能容忍對「好」的褻瀆和毀滅。此際忽然想起一則古人筆記中語:「元稹為翰林承旨,朝退,行鍾廊,時初日映九英梅,隙光射稹,有氣勃然,百寮望之曰:『豈腸胃文章映日可見乎。』」這本筆記裏的紀事多不可信,卻是偏多生新之意象而每教人生出歡喜,這一段文字,即很想移贈於越勝。
其實越勝的文字之好,思之深湛,本無須我妄置一詞,遠離萬水千山選中我來作序,我想,更多的是一位《讀書》的作者憶念他和《讀書》在一起的時代以及因此結下的情份,情份究竟有多深,無法測量,卻是隔了近三十年的時光,依然觸手可及。
丙申陽月十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