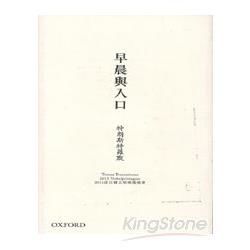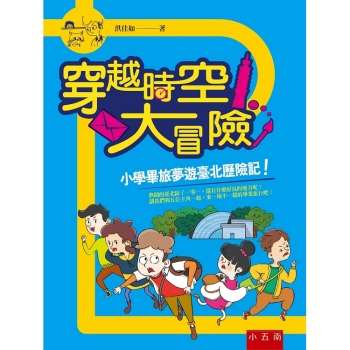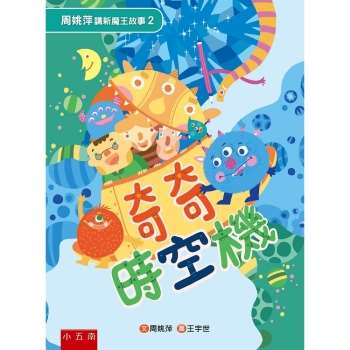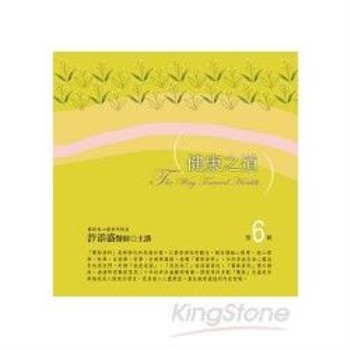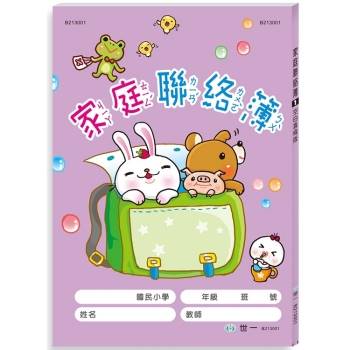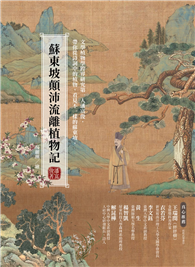譯者序
能編譯這本瑞典語和漢語雙語的托馬斯.特朗斯特羅默詩選是我的榮幸,也是件既充滿詩意和樂趣又具有挑戰性和難度的工作。在此特別感謝我的詩人老友、此項目策劃人和主編北島的信任和委託,感謝牛津大學出版社的老朋友林道群的支持和配合。沒有二位的幫助,這本詩集不可能出版。
出雙語詩集的意義自然是譯文和原文可以對比,正如主編在總序中提出的要求,「母語與譯文的嚴格對照」。即使讀者並不一定掌握原文(母語),但對原詩形式、結構、音律等等,依然可以有一個基本印象。因此,我在翻譯中努力遵照這條要求,力爭不漏一詞一字,音律節奏也盡量符合母語原文,而且在原文有限定詞尾和複數形式時也都盡量在譯文中譯出。此外,譯文的句子結構和詩行排列也盡可能與原文保持一致,便於讀者參照比較。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讀者在閱讀對照原文和譯文時,不僅要注意視覺上的對照,還要考慮聽覺上對照,要特別注意「聲音」。特朗斯特羅默不僅是個詩人,也是個音樂愛好者,音樂也常常是他的詩歌創作的出發點。在他的詩歌創作中,音樂幾乎不可分離。因此紙面的默默閱讀肯定不夠,讀者一定要傾聽其詩歌的「聲音」。
例如,特朗斯特羅默的詩作《快板》。它展現的是詩人日常生活常見的一種狀況,而這也正是詩人的創作出發點:「一個黑色的日子過後」,詩人在鋼琴邊坐下來,演奏一段海頓的曲子。所呈現的「聲音」被描寫成「綠的,活潑而安寧」——以此對照出那句「黑色的日子」後面可感覺到的壓抑精神狀態。詩人要傳達出的是自己的滿意感,「琴鍵得心應手。溫柔的音錘敲打。」但是更主要的是,他表現出的音樂和藝術還給人一種更大的自由感。外部現實具有壓抑人的強制性,但是在山崩石裂一樣的現實事件和對人的要求之外,確實還存在.另一種自由。「音樂是斜坡上的一棟玻璃房/那?石頭在飛,石頭在滾。//這些石頭滾動橫穿而過/但每塊玻璃都完整無損。」
詩歌和音樂——自身的詩歌創作和音樂活動,積極的藝術欣賞——在托馬斯.特朗斯特羅默的生活中一直是重要的組成部分。我們有充分理由相信,他生活中每天(在實際狀況有可能的時候)都在鋼琴前面度過一段時光。既是詩人,又是鋼琴家,正是對特朗斯特羅默的非常確實可靠的身份寫照。
在特朗斯特羅默全部的抒情詩作品中,音樂可以說在多方面一直存在。能讓人想到的不僅是那些明顯有音樂母題的詩作,也是特朗斯特羅默詩歌音調和意象背後能令人注意的傾聽音樂的整體態度——是圍繞其詩作呈現的那種特別的聲學。這種聲學也包括我們通常稱為「寧靜」的狀態——或者用詩人自己的話來說,「這?有音樂喑啞的一半」。這種說法在他1954年出版處女作《詩17首》中就可看到,其中有很多句式表示在整個自然/歷史/宇宙中……都有內在的音樂。其中有「青銅時代的號角/不得安寧的音調」在現時也存在;其中有「樹根發出的聲調就像銅號」;其中有冬天的黑暗「從隱蔽的樂器中發出一陣顫音」;其中至少還有本詩集選入的較長詩作「輓歌」,詩中「距離的音樂交匯合流」,而「這?有音樂喑啞的一半,如樹脂香/環繞著被雷擊傷的針樅樹」。其中還有詩作「早晨和入口」,詩中的自我被抓住,被編織到全部音樂的不受時空限制的掛毯之中。
在特朗斯特羅默後來的創作中,這類的音樂象徵出現得比較少,而是在詩集中包括個別的有直接取自音樂世界的具體母題的詩作。例如,在1958年的詩集《路上的秘密》中有特朗斯特羅默的第一首較長的「肖像詩」,即「巴拉基列夫的夢(1905)」,以及出版於1966年的詩集《音色與軌跡》中包括詩作「一個北方的藝術家」,其中的詩歌自我代表偉大的挪威作曲家愛德華.格里格(1843–1907)。
閱讀這些詩作,往往還必須瞭解其歷史背景。例如「巴拉基列夫的夢(1905)」中,這個年份也是詩名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可或缺,是理解本詩的重要線索。
因為這一年,即1905年,一般來說是俄國革命的先聲。作曲家米利.巴拉基列夫是俄國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出現的那批作曲家的領袖人物,稱為俄國音樂創作本民族特色的「新俄羅斯樂派」,或者叫做「巴拉基列夫圈子」(「強力集團」)。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巴拉基列夫經歷了宗教危機,在晚年他要求所有來訪者跟隨他劃十字:這在本詩中也有反映(「像我一樣劃十字」),但是除此之外沒有更多傳記性細節。也就是說,這不僅是一個作曲家的肖像,更是一首表現藝術家在政治和社會語境中的責任的詩作。本詩提到的戰艦「瑟瓦斯托普爾號」在當時的社會動蕩扮演過重要角色,也出現於愛森斯坦著名電影《戰艦波獎金號》。
巴拉基列夫在音樂會中睡著了,夢見自己被送到該戰艦上,水手向他展示了一件奇怪的樂器,並說「如果你會演奏你就免得一死」。他明白這個樂器是驅動戰艦和戰爭機器的。但是他對這個演奏任務束手無策:無論他的音樂還是他劃十字都不能阻止事件發生。在夢中他聽見執行死刑的鼓聲,但是被音樂廳?的掌聲驚醒。
在「一個北方的藝術家」這首詩中,格里格回到了自己的老家卑爾根之外的鄉間別墅「山妖之丘」。他晚年的創作大大減少,這點在詩中也有所反映——「美麗的陡坡多半沉默無語」——但是突然還有所開啟,帶著「一道直接從山妖那?奇妙地滲透出的亮光」。有關「這山?的錘打」的那些詩句,是指格里格1886年創作的第三小提琴奏鳴曲中的一個主題——進一步還預示了格里格死前那一年的創作,或者用詩中的詞語來說,他要「送出……為了找到上帝的蹤跡」的四首讚美詩。這首詩反映的第三部音樂作品是格里格1875–76年創作的g小調鋼琴謠曲,是以一首挪威民歌為基礎,其開頭幾句是「我知道很多可愛的歌/唱的是這個世界上美麗的國家;/但我從來沒有聽到那些歌/唱的是離我們很近的地方」。
格里格在挪威民間音樂中找到靈感,幫助他創造出活生生的個性化的藝術表達。
長詩《波羅的海》創作於1974年,其中有個章節描寫一位作曲家事業有成但受到政治迫害,「他遭到威脅,降職,放逐」。當他平反之後,又患腦溢血,身體右側麻痹並有失語症——但是他能繼續作曲,還保持了個人風格。「他給他不再能理解的歌詞譜曲—— / 用同樣的方式 / 在哼哼胡言亂語的合唱隊? / 我們表述一點我們的生活」。根據特朗斯特羅默本人的說明,這個作曲家是維沙翁.舍巴林(Vissarion Sjebalin 1902–1963),曾創作多部歌劇並且為普希金的詩作譜曲,公認為俄羅斯合唱曲中上乘之作。詩中提到的成為「主要檢舉人」的舍巴金的學生,是臭名昭著的吉洪.赫連尼科夫(Tichon Chrennikov 1913–2007),1948年曾經擔任蘇聯 作曲家協會主席,也是最高蘇維埃成員,擔任數項蘇共領導職務。
在1978年出版的《真相之障礙》中包括「有關舒伯特」這首詩,描寫弗朗茲.舒伯特(1797–1828)的生活。「他是一個來自維也納、被朋友們稱作『蘑菇』的年輕矮胖紳士,睡覺還戴著眼鏡而且每天早上準時到達寫字台前。/於是樂譜奇妙的百足蜈蚣在那?開始蠕動」。但這首詩不僅關於舒伯特本人,而更多的是關於舒伯特音樂,那些「比其它一切都更加真實的」音調,特別是有關兩部作品。一是C大調弦樂五重奏,有五個弦樂器演奏,使得詩中傾聽音樂的自我能感覺自己「毫無重量」,而且「植物具有思想」。另一部作品是最後這段詩中可反映出的鋼琴四手聯彈f小調幻想奏鳴曲。這兩部作品都是在舒伯特生命最後幾年內完成的。
特朗斯特羅默二十世紀的最後一部詩集《哀傷貢多拉》出版於1996年,書名來自其中一首同名詩作,而該首詩的名稱又是借取弗朗茲.李斯特的音樂作品《哀傷貢多拉之二》。
可見,不瞭解上述這些詩作之後的歷史和文化背景,也就不能充分瞭解其詩作的內涵,甚至影響翻譯的準確性。
我還建議,在閱讀這本雙語詩集時,讀者可以參考我翻譯的特朗斯特羅默和美國詩人羅伯特.布萊的通信集《航空信》(南京譯林出版社2012版)。在這本通信集?,特朗斯特羅默其實提出了一個優秀詩歌翻譯的最好標準,他在1974年2月13日給布萊的信中寫道:
……你的翻譯最好的地方是總能讓我從中找回我當初開始寫這些詩時的感覺。其他譯者提供的不過是已完成詩歌的一種(蒼白的)臨摹,而你把我帶回到起始的經驗。
可見,譯文是否能夠提供原詩的「感覺」或「起始的經驗」,這是一條衡量譯文優劣的最好標準。這條標準也可以呼應英國詩人雪萊為自己制訂的翻譯原則,即「譯文在讀者心中喚起的反應,應該與原文喚起之反應相同」。
毫無疑問,翻譯特朗斯特羅默的詩作,首先必須做到準確和信達,必須嚴格地按照原文(母語)來翻譯,在此基礎上,再努力爭取漢語譯文的流暢和詩意的雅緻。
本詩集的編譯按照同一出版項目之前幾部詩集的體例,前面有總序和譯者前言,而書後有詩人生平和創作年表,對其一生及創作可以一覽無遺。而作為補充,後面加了瑞典學院2011年授予詩人諾貝爾文學獎的授獎詞及頒獎典禮上的致辭,致辭者正是特朗斯特羅默的老友、瑞典詩人及諾貝爾文學獎評選機構瑞典學院院士埃斯普馬克,他最近訪問中國,有一篇介紹當代瑞典詩歌的演講稿,也譯出附後,可作為瞭解特朗斯特羅默生活和創作背景的資料。
最後,我也感謝特朗斯特羅默本人及夫人莫妮卡.特朗斯特羅默對此詩集出版的支持和認可。此外我要感謝瑞典漢學家馬悅然,感謝我的妻子陳安娜,他們一如既往解答我在翻譯中遇到的各種大小疑難問題。這本詩集,其實也是眾多朋友的合作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