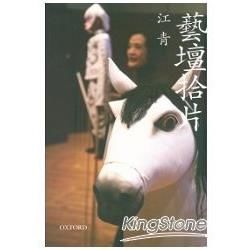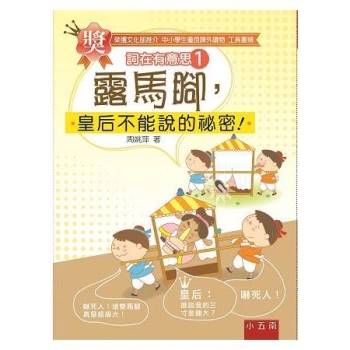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3 項符合
藝壇拾片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292 |
戲劇 |
$ 344 |
戲劇 |
$ 344 |
戲劇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 董橋、郁風、孫康宜專文推薦!
【名人推薦】
˙認識江青這麼多年,我竟無緣一見比雷爾。一連兩個深宵閱讀《藝壇拾片》清樣,我斷斷續續想像比雷爾的學者風範和他的科研成就,慶幸江青人生風雨路上遇得到這樣一位沉實厚道的伴侶。──董橋
˙江青是一個認真的好演員。但是她也體會到,演員的創造發揮到極致也只是一個詮釋者,正如傑出的鋼琴表演家是作曲家的音樂的詮釋一樣,舞蹈也可以詮釋音樂,但是她不想去詮釋音樂,她認為舞蹈創作還要從肢體語言出發,她逐漸走入創作的廣闊天地。─郁風
˙在追求藝術的過程中,江青特別標舉「真我」的重要性。對江青而言,藝術創作不僅是理論技巧的純熟運用,更是個人切身的人生經驗轉化為完美藝術形式與境界之過程。對於江青而言,藝術是生命之至高境界的表現,因此藝術的表現往往與人生情境交相輝映。人生際遇的錯綜複雜與藝術之綜合性如出一轍。──孫康宜
譯者簡介:
江青
一九四六年生於北京,在上海小學畢業後,十歲入北京舞蹈學校接受六年專業訓練。此後她的工作經驗是多方面的,演員、舞者、編舞、導演、寫作、舞美設計。六十年代在香港、台灣從事電影工作時,主演影片二十餘部,並參加數部影片的編舞工作,於一九六七年獲台灣電影最佳女主角金馬獎。一九七○年她前往美國,接觸學習現代舞,一九七三年在紐約創立「江青舞蹈團」(至一九八五年),一九八二年至八四年出任香港舞蹈團第一任藝術總監。她曾任教於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紐約亨特大學、瑞典舞蹈學院以及北京舞蹈學院。一九八五年江青移居瑞典,此後以自由編導身份在世界各地進行舞蹈創作和獨舞演出,並經常參加歌劇和話劇的編導工作,她的藝術生涯也開始向跨別類、多媒體、多元化發展。她的舞台創作演出其中包括:紐約古庚漢博物館、紐約大都會歌劇院、倫敦 Old Vic 劇場、瑞典皇家話劇院、維也納人民歌劇院、瑞士 Bern 城市劇場、柏林世界文化中心、中國國家歌劇院。現居瑞典、紐約。
滴滴點點《聲聲慢》
高行健 聲聲慢變奏
與高行健共「舞」──側寫高行健
從構思到演出──談舞樂儀式劇《玉龍第三國──納西「情死」》
只需用「心」望一眼
成語舞集
從《負.復.縛》到《茶》──與譚盾樂舞二重奏
唐詩意韻與馬勒的精神世界──《大地之歌》創作隨筆
原唐詩
鄭愁予 創譯《大地之歌》歌詞
莊喆 《大地之歌》與我的畫
鄭愁予 馬勒與李白的文化一線牽
程步奎 觀江青編導《大地之歌》舞劇
【舞樂儀式劇本】
玉龍第三國──納西「情死」
【舞劇劇本】
中國核桃夾子祈福迎祥
【電影劇本...
- 作者: 江青
- 出版社: 牛津大學 出版日期:2010-09-01 ISBN/ISSN:0193964880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64頁
- 類別: 中文書> 藝術> 戲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