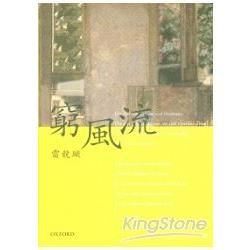提起七十年代的香港大學生,就令人想起曾經追求理想,投身社會運動的那一代青年。這批人後來逐漸轉變,大都安定下來,建立家庭,開展個人事業;少數也有投身政治或其他領域,在現實裏尋求理想的實現。另外,還有一羣卻加入留學的行列,希望擴闊視野,增長見識,反省思索,以待重新出發。雷競璇的留法回憶錄,平實真摯,故事娓娓道來,引人入勝,反映了一個時代知識分子的側面。
作者簡介:
雷競璇
一九七四年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其後留學法國,修讀政治學,集中研究黑非洲國家,歷時七年餘,在波爾多大學得到博士學位。返港後相繼在中文大學及城市大學研究及授課十餘年,編、著有有關選舉、香港及中國政治之中、英文書籍多種,以及在學術期刊發表論文若干篇。後自覺跟不上形勢,數年前辭去教職,改為自由撰稿人,社會與文化評論文章近年多在《信報》刊載。現仍擔任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名譽研究員。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雷競璇的法國留學記《窮風流》是異數中的異數,你很難想像世間竟有這樣坦白的自傳。──崔少明
˙溫情是這本書最動人的特點。我很喜歡雷競璇這種寫法,常在敍述完一段友人的往事之後,忽然躍出,或者為他祈福或者為他感傷。──梁文道
˙《窮風流》向中國人讀者介紹了法國人的「餐桌三位一體」:麵包、紅酒、乳酪──雷競璇譯作「餐上三寶」,甚妙。──高潔
˙此書既是遊記,也是自傳,是學問之章,也是性情之文。──陳雲
˙整本書最教人動容的,肯定是一幅幅入微的人物素描,名叫蘇菲和蕭菲的姐妹花,不顧實際的大學教授,有家歸不得的台灣僑生,多姿多采的非洲同學,執着的畫家朋友。至於描寫前樓後樓的隣居,我想起杜魯福的《婚姻生活》,特別是那位帶點神秘色彩的藍領同志,完全和電影裏的怪房客異曲同工。義務客串當鸚鵡保母的奇趣經驗,實在無法節錄,留待讀者自己翻閱吧。──邁克
名人推薦:˙雷競璇的法國留學記《窮風流》是異數中的異數,你很難想像世間竟有這樣坦白的自傳。──崔少明
˙溫情是這本書最動人的特點。我很喜歡雷競璇這種寫法,常在敍述完一段友人的往事之後,忽然躍出,或者為他祈福或者為他感傷。──梁文道
˙《窮風流》向中國人讀者介紹了法國人的「餐桌三位一體」:麵包、紅酒、乳酪──雷競璇譯作「餐上三寶」,甚妙。──高潔
˙此書既是遊記,也是自傳,是學問之章,也是性情之文。──陳雲
˙整本書最教人動容的,肯定是一幅幅入微的人物素描,名叫蘇菲和蕭菲的姐妹花,不顧實際的大學教授...
目錄
1 窮風流(代序)
上篇 也堪回首
11 求學
48 生活
100 家庭
下篇 思前想後
121 同學少年多不賤
129 彈老調的教授
135 我感,故我在
142 有家歸不得
148 皮埃爾一家
158 鄰居
168 畢業和證書
173 留學書
180 距離
185 巴黎的梧桐樹和時光
193 「二馬力」的聯想
199 到巴黎時,也掃掃墓
205 巴黎的書店
210 假期的哲學
217 波爾多紅酒
224 吃乳酪
232 悼英妮
235 後記
1 窮風流(代序)
上篇 也堪回首
11 求學
48 生活
100 家庭
下篇 思前想後
121 同學少年多不賤
129 彈老調的教授
135 我感,故我在
142 有家歸不得
148 皮埃爾一家
158 鄰居
168 畢業和證書
173 留學書
180 距離
185 巴黎的梧桐樹和時光
193 「二馬力」的聯想
199 到巴黎時,也掃掃墓
205 巴黎的書店
210 假期的哲學
217 波爾多紅酒
224 吃乳酪
232 悼英妮
235 後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