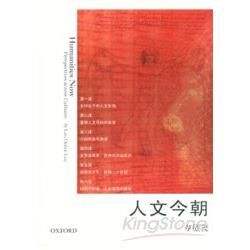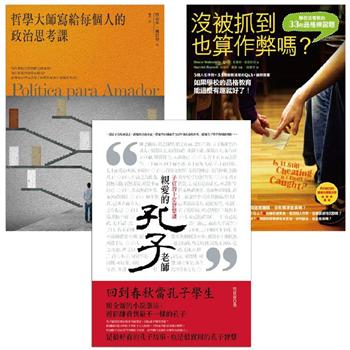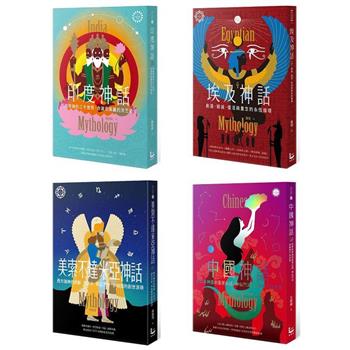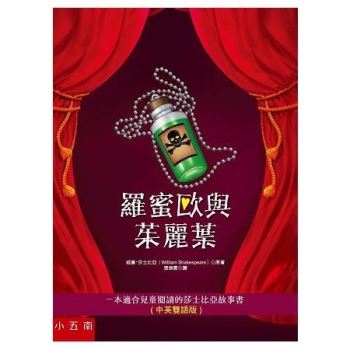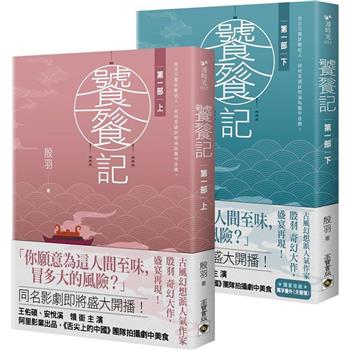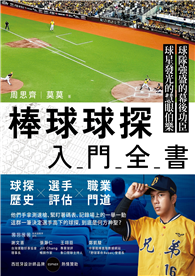作者序
二○○九年秋天,受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之邀,我在港大做了六場公開演講,所用的語言是英文,對象除了在校學生外還有校外社會人士,只要願意報名來聽,一概歡迎。我本以為講這一類有關人文 (Humanities) 的題目,對一般人可能枯燥無味,一定門可羅雀,卻沒有想到全場爆滿,報名的將近一百人。這一個現象,令我驚喜莫名,也不知所措,雖然盡心準備,而且盡量採用非學術性或較易懂的學術著作,但講起來仍然困難重重,我必須用較淺顯的英語把幾個我最關心的課題──文學、電影、音樂、建築——講出來,並將之和今日香港的日常生活連在一起,真是談何容易!在這個經濟掛帥的金融中心,談這些“非主流”的冷門學問,更有點吃力而不討好。
但我依然勉力而為之,因為我自認是一個“非傳統”的人文主義者,這些都是我個人最關心、也最有興趣的題目,即使我的演講方式有點“高不成,低不就”,我還是感到一種使命感。況且這六個題目都是我自己定的,從學術的立場看來的確有點好高騖遠,但我在港多年來“浮游”於學院門內門外,自願當“兩棲動物”,還不是為了推廣我心目中的人文願景?甚至有點“逆反心理”,越是處在這個商業環境,我越覺得有挑戰性。所以為這六場演講讀了不少書,大多是在坊間書店買得到的,(書單列於每回之後),以英文的居多,因為我覺得在香港這個國際大都會有此需要,也和我近年來讀西文書的興趣有關。六場演講下來,我並不滿意,因為從課堂上走出來講學術──這個嘗試本身就有點不配套,我高估了自己的能力 (包括英語表達能力),也可能低估了聽眾的水準,雖然大部分聽眾在孜孜細聽,我也偶爾看到不耐煩的面部表情。好在每次演講後,主辦的單位安排兩位講評人,對我的講題和內容深入討論,也促使聽眾踴躍提問,令我獲益良多。
這六場演講,主辦方面本來就有出書的想法,甚至場場安排錄影,鄭重其事。我在鎂光燈照耀之下,頓覺自己在演戲,但卻沒有背好“台辭”。我一向不寫演講稿,只準備大綱,有時便驚慌失措。這才發現,雖然自己有教學三十多年的經驗,畢竟不是一個演說家,同是在課室裡講書,(港大陸佑堂二樓的會議室 convocation room) 但不是上課;同是學生在聽,但又有不少校外人士參加。在這個“混雜”(mixed)的聽眾面前,我真的不知道如何演這幾場戲。
雖然我表現欠佳,但自覺演講的內容還是有根據的,不是信口雌黃,因為我從引用的各類書中找到不少“知音”,都是對人文有深度關懷的學者、作家、藝術家和理論家,令我覺得非但吾道不孤,而且世界上還有那麼多知名的知識份子早在我之前已經關心這些議題了。所以我必須公開承認:我的大部分觀點都不是獨創,而是“引他山之石”的“derivative discourse”(衍生論述);換言之,此非一家之言,而是“眾說紛紜”,只不過我做了一點總結心得罷了。內中很多問題還是沒有想清楚,有待進一步研究和思考。
我決定用中文把這個演講集寫出來,為的是中文讀者群 (除了香港之外還有中國內地和台灣) 畢竟比懂英文的人數為多,另一方面則是我的英文書寫能力已經達不到我的要求,我的中文但求通順易懂,寫起來較英文快得多,但我列的書目大半還是英文,好在內中不少已有中文譯本,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照閱讀。
在這篇小序中我不擬重述本書內容,反正全書篇幅不長,讀者可以直接進入“文本”。想聲明的是,事後的中文追記,雖根據當時的每一場演說大綱(在前五場印發),但細節有所出入。此書雖用演講口氣,但和演講時的次序不盡相同,事後添加的內容也不少,相信大多數讀者都不是在場聽眾,聽過的人可能至今也忘了。(將來是否把錄影帶公開尚未決定。)
在此我要特別感謝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的總監,也是我的好友陳婉瑩教授,和港大人文學院院長蔡寬量 (Daniel Chua) 教授,沒有這兩位熱心人士在百忙之中為我的演講系列“催生”,《人文今朝》恐怕也沒有今朝。英文的題目是:Humanities Now,是我自己起的,心中想到的典故是影片 Apocalypse Now (港譯《現代啟示錄》,語帶危機感;副標題 Perspectives across Cultures 則是蔡院長加上去的,意謂視野是“跨文化”的,事後思之,我在這方面作的還不夠。
我也要感謝每一場的兩位講評人──大半是港大教授,他 / 她們在百忙之中親臨參加討論,非但指正了我的不足之處,而且把一種良好的學術風氣帶給在場的非學術聽眾,令我感激不盡。
最後我要感謝幾位最熱心的聽眾,有的已經變成了我的朋友:徐曦、張雪紅、呂書練、葉朗年 (還是一個中學生)、劉庭善、賴雪芬、Saya Paranee 和李令喬。
我妻李子玉每場都來捧場,事後又善言安慰,為我打氣,讓我感到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書蟲”。
本書之寫作承蒙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之“公共文化計劃”及港大“杜鵑 (1972) 基金”贊助,謹此致謝。
二○一○年七月十七日於九龍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