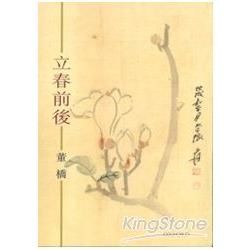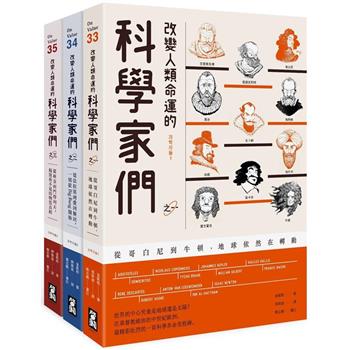字裏燈影
署名愛麗思的女士來電郵說她在友人家中看到我寫的一幅毛筆字,問我平日是磨墨寫字還是用墨汁寫?兩樣都有:寫大字貪方便,通常我用日本桐華墨汁;寫小字順手磨墨不費勁,寫出來的字墨色時濃時淡也靈動,也好看。先父從來不用墨汁,寫招牌大字都在大硯池裏磨墨,我小時候替老人家磨墨磨多了,一大早磨一池清水磨到太陽升得高高的才磨成濃墨,累壞了。老一輩人都講究磨墨。我在煮夢廬讀書那些年也替亦梅老師磨墨。王念青先生倒不要晚輩磨墨,情願自己磨,說磨墨練腕力,磨了墨手腕聽使,大字小字得心應手。
他還愛用井水磨墨,也愛用井水洗筆洗硯,說是小時候鼓浪嶼私塾老師教的,老了念舊,不忍割捨。萬隆念青室後園那口古井井洞很深,井水冷冽,王先生洗完筆硯總是順便洗手洗臉,乾乾淨淨坐在花梨樹下喝茶聊天。花梨他說就是黃花梨,跟紫檀一樣貴重,南洋很多,他家大門外斜路旁邊一株老樹他說是紫檀。一個廣東木匠存了一大堆老花梨老紫檀,專替王先生做書架書櫃,雕花雕得清淡,手工一點不俗氣,都是王先生挑古書裏的圖樣教他雕的。我那時候年紀小,什麼都不懂,八十年代拜識王世襄先生才曉得紫檀黃花梨明清家具案頭木器學問大了去。念青室還藏了一大叠清宮御用佳紙,暗龍宣,竹青箋,大理紙,安南紙,梅花玉版箋,花絹箋,王先生高興了都挑出來教我辨認,說是他父親那輩人到京城做買賣陸陸續續買回來珍藏,那股紙香五六十年了我還記得,清清幽幽像樟木箱子裏的衣香,像古廟禪房的輕烟味,偶爾還散發些麝香。王先生從來捨不得用那些老紙寫字,一九五七年他到台北觀光帶了一張托人求溥心畬墨寶,溥先生寫五言律詩〈登燕子磯〉,行草飛揚,筆筆生姿。那幅字至今掛在王先生長孫王思明美國家中,思明年前還拍了彩照給我懷舊:「亂後悲行役,空尋孫楚樓。蕭蕭木葉下,浩浩大江流。地向荊襄盡,山連吳越秋。伊人在天末,瞻望滿離憂」。
王先生求溥心畬鈐「溥儒」龍印,溥先生真鈐了:「一是清宮舊紙宜帶龍氣,」王先生笑得很高興。「再者龍印辟邪!」思明常說他爺爺一生迷信,愛集藏書法不愛多收國畫,古人說的「畫是八重天,字是九重天」,字的地位遠在畫之上,還說家裏掛字可以鎮宅。記憶中念青室掛的確實都是字,董其昌墨寶尤其多,說董思白居鄉豪橫,老而漁色,連房子都遭人火燒,書畫竟是雙絕,領導風騷數百年,實在奇怪:「我從小喜歡他的字,」王先生說,「碰到愜意的都買,老家先人集藏的一些後來也歸了我,朝夕相對,領悟日深!」老先生連一手字都像董其昌。亦梅老師家裏藏的幾件扇頁冊頁也是王先生割愛讓出來的。上海 大畫家吳湖帆外祖父沈韻初留下一批董香光,連齋名「寶董閣」也傳給外孫,聽說王先生戰前為兩幅香光字幅真偽跟吳湖帆通了幾次信,難怪念青室偏廳一幅董其昌條幅綾 邊吳湖帆題跋。那幅字跟我家寫張籍〈梅溪〉一幅很像,都是香光壯歲之作。去年除夕 我在西泠印社拍賣會上收進來的倒是晚年的行草,寫「落花寂寂啼山鳥,楊柳青青渡水人」,魏文伯舊藏。魏文伯是湖北人,一九二五年加入共青團,翌年入黨,一九二九年考入北平郁文大學政治科,任校內中共支部書記。
一九三○年代多次進出監獄,屢任報刊書記,中學教員,抗戰時期領導鄉民抗日,當縣長。一九四九年後當過人民檢查署分署檢察長,軍委會政委副主任,司法部副部長,上海市委書記,華東法政學院院長。文革受迫害,七九年平反,當國務院司法部部長。八三年補選為中共中顧會委員。一九八七年八十二歲在上海病逝。魏文伯是書法家協會理事,工詩詞,工書法,出版過詩鈔和書法選。毛澤東祕書田家英收藏甚富,《田家英與小莽蒼蒼 齋》裏〈藏友之交〉說,收藏過程中,「胡繩、李一氓、蕭勁光、梅行、史莽、魏文伯、孫大光、蕭華、方行、朱光等,都給予田家英真摯的幫助」。田家英收藏的董其昌有沒 有魏文伯替他找到的書裏沒說。書裏倒說田夫人董邊喜歡董其昌的字,早年經常輪換掛在臥室裏,抄家封宅之後一幅也看不到了。姓董的都偏愛董其昌的字,聽說過好幾位了。
鄧之誠《骨董瑣記》說董其昌、劉石庵書法非不工,特有姿無骨,皆人品限之。他說劉石庵媚事大貪官和珅,為和珅寫屏條,上款致齋尚書命書,自署下款也極恭謹。那是偏見了, 為人題字誰不客客氣氣落款?王念青先生開玩笑說書法練出美姿難如登天,管它有骨無骨!魏文伯藏過的這幅「落花寂寂」沒有上款反倒乾淨了。詩是王維〈寒食汜上作〉七絕:「廣武城邊逢暮春,汶陽歸客淚沾巾。落花寂寂啼山鳥,楊柳青青渡水人」,董其昌只寫後兩句,暮春景色都在字裏。聽說北京去年秋拍有一件楊士惠刻的象牙鼻煙壺,浮雕楊柳岸邊旅人涉水春遊,背面刻的也是王維這十四字。楊士惠是老北京工藝世家子弟,竹木牙角著名雕手,我出世那年他雕蟈蟈白菜一舉成名,一九五二年經徐悲鴻指教創作《頤和園》。從前杏廬先生珍藏楊士惠一件象牙煙壺,刻歲朝清供,真漂亮,杏廬說是抗戰勝利翌年在琉璃廠買的。我玩竹木牙角幾十年,從來買不到刻董其昌書法的文玩,沈葦窗先生說徐伯郊先生有一件竹臂擱刻香光行書,說什麼都不肯相讓:「字極好,刻得也好!」愛麗思電郵抱怨她拜師學書許多年,書法至今寫不出風格,歸咎臨帖臨僵了,要我說說心得教教她。我不在行,也不會教,更不敢當老師。不好為人師是跟余英時學的。
余先生說安徽桐城派古文巨子姚鼐寫信給戴震要拜他為師,戴震回信說:「至欲以僕為師,則別有說,非徒自顧不足為師,亦非謂所學如足下,斷然以不敏謝也!」我寫〈七十長箋〉說想拜余先生為師,余先生來信引了戴震接下來的一句話:「僕與足下無妨交相師,而參互以求十分之見,苟有過,則相規,使道在人,不在言,斯不失友之謂,固大善」。我遵照這層意思改寫了〈七十長箋〉的結尾,也抄錄了戴震的話給愛麗思一閱,愛麗思小楷謄抄一遍讓我看看她的字。小字端正極了,用功再練一練不難更像張充和。她說她喜歡張充和的字,西泠拍賣買不到,到處收集印了出來的張充和書法細細臨摹。愛麗思這份心思實在難得,給充和寫信我會告訴她。寫毛筆字的人少了,愛惜書法的人也少了,愛麗思說她虔心為中國書藝點一盞長明燈。
|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立春前後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356 |
文學 |
$ 366 |
小說/文學 |
$ 418 |
中文書 |
$ 419 |
現代散文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立春前後
《立春前後》是董橋2011至2012年最新寫成的隨筆,隨筆愈寫愈像小說, 因為有人有故事, 很好看。
作者說從前他在倫大亞非學院圖書館讀過周作人一本《立春以前》,封面清雅得要命,幾十年來想買一本那個初版本至今沒找到。壬辰龍年立春是農曆一月十三陽曆二月四日,作者剛過七十, 從心所欲,既然這本新文集既是立春前後出版,書名就叫《立春前後》。也許比周作人的《立春以前》更見?致。老一輩人說「立」乃開始,「春」乃蠢動,一立了春,百草甦醒,一片吉慶:人老了多些吉慶好。
作者簡介:
董橋
曾任《明報》總編輯,《讀者文摘》總編輯,《明報月刊》總編輯,香港美國新聞處「今日世界」叢書部編輯。現任《蘋果日報》社長。
章節試閱
字裏燈影
署名愛麗思的女士來電郵說她在友人家中看到我寫的一幅毛筆字,問我平日是磨墨寫字還是用墨汁寫?兩樣都有:寫大字貪方便,通常我用日本桐華墨汁;寫小字順手磨墨不費勁,寫出來的字墨色時濃時淡也靈動,也好看。先父從來不用墨汁,寫招牌大字都在大硯池裏磨墨,我小時候替老人家磨墨磨多了,一大早磨一池清水磨到太陽升得高高的才磨成濃墨,累壞了。老一輩人都講究磨墨。我在煮夢廬讀書那些年也替亦梅老師磨墨。王念青先生倒不要晚輩磨墨,情願自己磨,說磨墨練腕力,磨了墨手腕聽使,大字小字得心應手。
他還愛用井水磨...
署名愛麗思的女士來電郵說她在友人家中看到我寫的一幅毛筆字,問我平日是磨墨寫字還是用墨汁寫?兩樣都有:寫大字貪方便,通常我用日本桐華墨汁;寫小字順手磨墨不費勁,寫出來的字墨色時濃時淡也靈動,也好看。先父從來不用墨汁,寫招牌大字都在大硯池裏磨墨,我小時候替老人家磨墨磨多了,一大早磨一池清水磨到太陽升得高高的才磨成濃墨,累壞了。老一輩人都講究磨墨。我在煮夢廬讀書那些年也替亦梅老師磨墨。王念青先生倒不要晚輩磨墨,情願自己磨,說磨墨練腕力,磨了墨手腕聽使,大字小字得心應手。
他還愛用井水磨...
»看全部
目錄
自序
新年試筆
字裏燈影
聖誕快樂
七十長箋
和高先生談天
冬心緣
我的舊作
題毛尖新書
春水如藍
南無阿彌陀佛
夕陽何事照金臺
團香
綏園舊事
殘夢水聲中
和傅玫謦欬
風景
香塵
老威爾遜
山河歲月
老崔來玩
深柳先生
麗人行
讀盧前想起的
平兒是玉蘭
雨窗漫錄
消夏散葉
新年試筆
字裏燈影
聖誕快樂
七十長箋
和高先生談天
冬心緣
我的舊作
題毛尖新書
春水如藍
南無阿彌陀佛
夕陽何事照金臺
團香
綏園舊事
殘夢水聲中
和傅玫謦欬
風景
香塵
老威爾遜
山河歲月
老崔來玩
深柳先生
麗人行
讀盧前想起的
平兒是玉蘭
雨窗漫錄
消夏散葉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董橋
- 出版社: 牛津大學 出版日期:2012-02-01 ISBN/ISSN:9780193979048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精裝 頁數:208頁
- 類別: 中文書> 華文文學> 現代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