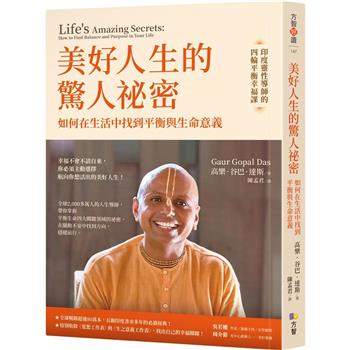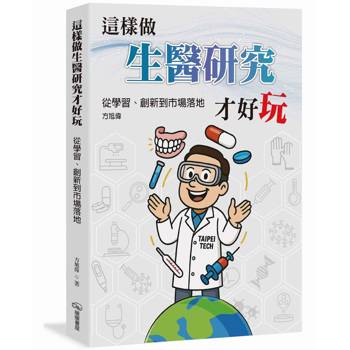代序
本書彙集了二○○七年以來就莫言《酒國》和《生死疲勞》兩部小說所作的幾次討論,包括一篇先以英文出版的分析《酒國》的論文,在北大和華東師大所做三次研討班或讀書會講課和課堂討論記錄,以及我和莫言就這兩部小說和相關文學問題所作的兩次對話。在本書整理出版過程中,適逢莫言獲得二○一二年諾貝爾文學獎,茲收錄兩篇我在第一時間所做的中外媒體訪談,以紀錄當代中國文學這一重要時刻。
莫言的寫作已有近三十年的個人史。從當代中國文學發展脈絡看,這三十年是從相對簡單「回歸文學」、「文學現代化」或「形式創新」走向全面、總體性地重建中國文學與中國社會、中國文學與現代史、乃至中國文學與中國文明之關係的偉大歷史瞬間,其中積累的文學經驗和財富,當有待當下和後世的批評家、文學史家不斷挖掘、探討和回味。在這三十年間湧現的幾茬作家中,莫言既具有一般意義上的代表性(從農村到城市、從鄉土到世界、從底層到「純文學」、從技巧到故事等等),又是一個極為特殊的個案。由他作品構成的世界不僅是時代的一個結晶體,也包含著當代中國語言和文學創造力的內在秘密。選擇《酒國》和《生死疲勞》作為分析和理解這個世界的入口,用意只是想從莫言成熟期的主要作品出發,以此為參照建立起批評的基本眼界和框架,以圖日後再回溯性地去研究莫言早期作品的文學史意義。
在世界文學語境裡看,自一九八二年哥倫比亞作家加西亞.馬爾克斯作為拉美文學爆炸( the Boom)的代表性作家獲諾貝爾文學獎以來,世界文壇上雖然不缺乏優秀作家,但同二戰前後高峰迭起、大師輩出的陣勢相比,可謂處在一個歷史低潮期。只要想想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獲獎的葉芝 ( 1923)、蕭伯納( 1925)、托馬斯.曼( 1929)和尤金.奧尼爾( 1936)──且不提此期間沒有獲獎的普魯斯特、卡夫卡、魯迅、喬伊斯、龐德、夏目漱石,以及意識流、超現實主義、和先鋒派作家群驚人的文學創造力,我們就能合乎歷史尺度地去看待今天世界文學的狀態。即便在中國「當代文學」歷史框架內,以艾略特( 1948)、福克納 ( 1949)、海明威( 1954)、加繆( 1954)接連獲獎為標誌的戰後文學高峰,在今天看似乎也是不可企及的。隨.戰後社會發展;民族解放、反帝、反殖運動的勃興;文化多元化、底層或邊緣文化進入主流文化的大趨勢也逐漸反映在國際主流文學創作和文學接受領域。諾貝爾文學獎越來越多地授予非西方作家、女性作家、和有.混雜文化背景的作家,就是一個側面的映證。但換一個角度看,我們也可以說,在拉美「文學爆炸」之後(或以二○一○年略薩獲諾貝爾獎為收束),還沒有出現另一個具有世界性影響和文學史重要性的民族文學或區域文學創作峰值。當代中國文學,無論就其內在的準備而言還是它所經歷的社會歷史變動之劇烈深刻而言,無疑都最具創造出這種世界歷史性峰值的條件。二○一二年莫言獲諾貝爾文學獎本身談不上是一個事件,因為它無非是對莫言個人創作成就和當代中國文學活力的名至實歸且略顯遲到的承認。但另一方面,這畢竟是一個挾顯赫傳統與世界性威望的文學獎第一次克服西方人種種政治的、意識形態的、文化價值上的偏見而授給了一位在中國生活和寫作的中國作家,其中的象徵意味,又不可不謂深長。
近年來我在不同場合反復提出了「當代性」和「文學性」的問題,撮其要,無非是想指出,合乎文學內部規律的寫作,遵循其自律性,包括文學自身想像、誇張、諷喻、語言遊戲、敘事裂變、乃至形而上層面的布局,是抵達文學和歷史之間終極關係的有效途徑(雖然不是唯一途徑)。換句話說,在語言的藝術作品裡,充分的自由,伴隨著那種情感和心靈的激揚飛翔狀態,實為捕捉現實世界經驗、問題、矛盾的最敏銳的感應器。形式自身的形式化所需能量只能來自歷史,但歷史作為一種感受、體驗、圖景和觀念,作為一個審美和價值的整體,卻依賴於一種形式和結構,具體到小說,是依賴於一種敘事的構形能力。在認識的意義上,文學憑藉文學感性、想像和形式自律性將我們帶入理智無法到達的領域。在認識之外,在情感和道德領域,文學以它的象徵和寓言、諷刺和幽默、悲劇性與喜劇性、激烈的戲劇衝突和平緩的史詩鋪展,為心靈提供一個棲息之所,一種高於歷史、高於哲學的觀照和升華。在所有這些方面,莫言的作品都為我們的思考提供了具體的、當下的例證。
值此結集之際,謹對華東師大、北大和紐約大學的同事和學生致謝。在他們的幫助、支持和積極參與下,我每年回國講學時都得以以暑期研討班或讀書會的形式,和國內外同行分享閱讀當代文學文本的快樂和挑戰。把出現在身邊的、尚無定論而仍在一時一地審美和學術風氣中尋找落座的當代作品,同業已經典化的文學文本和理論文本一視同仁,帶.同樣嚴肅的態度、花同樣的力氣去細讀和討論,這.不僅僅是一種必要的思想和技藝的操練,實乃是我們通向「文學本身」和「意義生產」的唯一真實的入口,也是我們作為當代人彼此間的責任。可以說,沒有「當代文學」,也就沒有文學史,也就沒有所謂「文學本身」,這是當代文學和文學批評的終極含義所在。在過去五年裡,在莫言的《酒國》和《生死疲勞》之外,我們也討論了王安憶的《啟蒙時代》和余華的《兄弟》。《對話啟蒙時代》(與王安憶合著)已於二○○八年由北京三聯出版社出版。希望今後大家能一起把這種討論的興趣和形式繼續下去,並逐步擴大到當代文學其他作家、其他文類和其他方面。
通過閱讀和批評我們找到自己所屬的時代和歷史,同樣,通過閱讀和批評,我們也在更個人的意義上找到友人和友情;通過他們的眼睛、他們的語言,我們獲得了新的感受力,從而擴大了自己的小小世界的邊界。初讀《酒國》時我還不認識莫言,討論《生死疲勞》時我們已一見如故。在紐約和北京的兩次長談,給我以極為難忘的印象,既是知性意義上「長見識」(包括對不自覺地使用起「半自律性」、「本體論」這類行業黑話後而隨即感到的慚愧),也是純粹的酣暢、愉悅、享受。在此感謝莫言的信任、耐心和友誼,並再次對他無時不在、無處不在的語言天才和講故事天才表示敬意。
最後,想借此機會感謝牛津大學出版社(中國)資深編輯,老友林道群先生。一九八九年深冬,當「文化熱」期間西學翻譯討論的群體星雲流散、自己在北京像一個潮水退去後「趴在海灘上那些還光著屁股的學者」一樣枯坐斗室之際,道群忽從香港寄來一本格非剛剛出版的短篇小說集《謎舟》,問我是否願意寫一篇評論。那是我和當代中國文學創作間第一次「親密接觸」,道群正是做媒的人。今天,願以這本小書並借莫言之名,回報道群對當代中國文學成長的關心和幫助。而這書稿的準備拖沓幾年,最後順利面世,也全賴道群如一的鼓勵和效率。
張旭東謹識
2012年10月31日
風Sandy過後紐約大停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