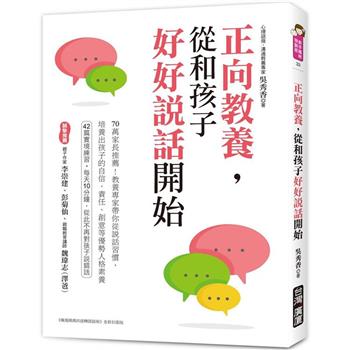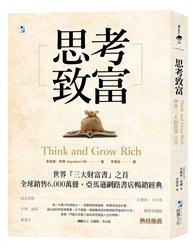編者序
香港文化與社會研討會的第一個十年∕馬傑偉、吳俊雄、呂大樂
2002年,我們三人開始聯繫了十多個研究本土議題的朋友,經過討論,決定於翌年舉辦第一屆香港文化與社會研討會。之後隔年辦了第二、第三屆,並且先後於2006、2009、2011年出版了三冊論文集。參與研討會的人數亦由第一屆的百多人,增長到第三屆的三百多人。
這十年的合作是愉快的經驗。我們以中文寫作來發表自己的本土研究的成果,這聽起來好像沒有甚麼特別,但在過去的十年裡,卻是現時大學體制內很難展開的事情。參與者彼此之間的組織儘管鬆散,但我們本.興趣參與,都樂於隔幾年相聚,認真討論切身的議題和交流研究成果。在這種無制度包袱的狀態下,大家默默工作,相互支持,使多年來各人投入的本土研究,得以延續。
就研究方向而言,由「港式文化研究」,到「文化政治」,再而「香港文化生活」,漸漸由香港文化與社會的大.述,轉向社會變遷的細節,對研究運用的實證材料,要求更加嚴格。到最近,我們三人有感社會代際轉變,是時候引入創新思維,於是邀請了張少強、梁啟智、陳嘉銘接辦第四屆會議。當然我們仍然全力參與,但由他們牽頭,相信提問焦點和分析取向定能更為緊貼社會變遷。本論文集是他們努力的成果。讀者對照一下2006年出版的第一冊,以及你們手中的這一本,應可看到新議題、新方法的引進。期望香港文化與社會研討會,在未來一段長時間,繼續維繫本土學者,為本土研究總結經驗、發掘新知。
本書研究承蒙香港樹仁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南中國研究計劃贊助,謹此致謝。
導言
範式轉移∕張少強、梁啟智、陳嘉銘
香港向來都以單向線性的歷史敘事(narrative)來講述自身的誕生過程,按照「漁村成為亞洲世界城市」,或「荒島變做資本主義天堂」,這樣的演進大綱來編纂「香港故事」。這個「香港故事」亦長期在港人的自我認同之中起.重大作用,為港人扣連彼此之間的歷史連續,個體之上的共同背景,以至尋求發展的未來方向(Ngo,1999)。這個「香港故事」甚至有頗長時間,使得社會大眾深感作為「香港人」的優越,且對香港本土充滿自豪和樂觀。在1997年之前,英國殖民者就利用了這個「香港故事」來促進其統治具有「霸權」(hegemony)或譯作「統識」的力量,既把西方殖民主義之中的「文明使命」透過這個冷戰時期的「香港故事」化為深入民心的「常識」(common sense),亦令社會大眾認同,或難以挑戰,一直包含在這個「香港故事」之中許多有利統治的權力論述。這是何故末代英人港督彭定康作告別演說之時,能向世界如此總結英國的殖民主義功德,並終在港人心中留下未完權威:
英國的施政即將終結,我相信我們有資格這樣的說:對於這裡,我國的貢獻就是提供了可保香港人躍升的台板。法治精神,廉潔及輕度干預的政府,自由社會的價值,代議政治及民主問責的開展。這是一個華人城市,一個非常賦有英國特色的華人城市。沒有一塊曾被支配的領土,在留落下來之時,比這裡更為繁榮。……我絕不懷疑,只要香港人繼續抱持這些他們重視的價值,香港之星將繼續升騰。(Ho, ed. 1997: 104-105)
在1997年後,中國雖然奪回香港主權,還以「一國兩制」之名直接沿用英式殖民體制來建立香港特區政府,可是在特區政府之下的(後)殖民統治卻無力延續這個「香港故事」,令香港失去了曾經有過的內在凝聚力。好像在港英時期,對應這個「香港故事」而見流行的「繁榮安定」論,已在特區政府成立之初,由於經濟急劇衰退一度換來教人頹喪的「經濟低迷」說。下及2007年之時,曾蔭權雖在施政報告中嘗試高舉「黃金十年」的講法來重振這個「香港故事」(香港特區政府,2007: 頁36),可是不足一年即被由美國迷債危機所觸發的全球「金融海嘯」所淹沒(香港特區政府,2008: 頁3, 5–6)。
特區政府的自身表現,更是早在董建華年代之時,已再無身段可如同前港英政府那般,擺出這個「香港故事」來自詡可為香港提供「良好管治」(good government) (Ku,2003)。縱使曾蔭權年代之時,再無好像禽流感或SARS 那樣的嚴重亂子,或 2003年首次七一大遊行那樣接近崩潰的權力危機,但民怨依然籠罩全城,不同的示威抗議照樣湧現街頭,民主政制和民生政策的發展亦見大失人心。最後,曾蔭權本人更由於爆出貪腐醜聞而令特區政府的道德誠信近乎徹底破產。這就進一步使長期在港人共識之中視為應有的香港素質,即今天所講的「核心價值」,好像繁榮,發展,民主,法治,自由,公義,公平,公開,透明,廉潔等,都如骨牌那般接連塌下。故此,後九七香港已因昔日的「香港故事」無法延續,從認知到實踐層面都失掉了可以有效統整局面的論述結構和領導軸心。
隨著昔日的「香港故事」難以再講下去,據此而有的權力秩序又在流逝,後九七香港的自我構成顯然正在呈現根本的範式轉移(paradigm shift)。以集體認同來說,在新媒體衝擊之下,社會大眾,特別是年青一代,早已遠離要由主流文化精英,透過《獅子山下》那般的劇集來替現(represent)他們的「香港故事」。他們反而能在好像facebook的網絡世界,直接陳述自己的「香港故事」,或連為群組來講述屬於自己圈子的「香港故事」。這就使得大量大眾的多重聲音,包括當中的議題,論述,觀點和情感等,都有大量公開發表空間,因而增加了大眾內部的自我扣連,知情能力,言論自主,以及意識號召。引申所至,這亦促成民間社會湧現愈來愈多橫向的連線,各式各樣的公開呼籲,由下而上的權力挑戰,甚或各類大小不一的論述攻勢及公民抗爭。結果,就連主流媒體都要大舉發展網絡業務來鞏固它們的營運,並與線上世界保持互動來吸納網民這個市場。政府也要現身這個線上世界,開設網站和網誌來滲進其中,並於其中進行官方干預及政治宣傳,試圖拉攏網民這個群體。
現在的香港所以特別紛亂,一切都好像只有折騰而無進路,各方都在受挫但還在糾纏,正是在於這場範式轉移確已帶來多元多角多方力量的迅速崛起,並好讓這些力量成為不可迴避的蓬勃主體,也有齊來爭持競逐的動員能力。可是,我們同時需要清楚的是,現時的香港亦非再無縱向的支配,更不是沒有當權者與民眾之間結構性的並不對等及勢力上的強弱懸殊。相反,主流媒體還是擁有大批受眾,對於資訊發放,大眾認知和輿論方向,仍具重大主導作用。特區政府亦都繼續把持最終決策權力,官方政策包括相關的立場,言論和判斷,始終屬於整體焦點,以及影響整體發展的關鍵。要是新媒體本身也是後工業資本主義的運作組件,它的誕生從不意味資產階級的整體優勢已被拉倒而再無唯利是圖的金權政治。北京中央更是無改維持香港「繁榮安定」的調子,在所謂「高度自治」以外,對香港進行自上而下的權力支配,要香港在「一國兩制」之下做一個「經濟城市」。
我們並非單純地認為「香港故事」正從簡單變為複雜。香港從來不只得單一故事,今昔之別也不在於故事面向的增加而是在於「香港故事」中一直存在的多面向特質已變得難以迴避。正如眾多其他香港研究都已指出,有關香港身份認同的議論往往把「香港人」簡化為單一群體,無視他們在階級、性別和族裔等各方面的不同處境(Faure,2003;Pun & Yee,2003; Ku & Pun,2004)。事實上,這亦只是在1997年前,在盛世亢奮的氛圍之下,香港的書寫乃可如此輕易地忽略內部的雜異,無視好像因工廠北移而失業的車衣女工,一直陸續來港的內地移民,生活總在社會底層的邊緣群體,以至在港出生的踞喀兵及其他南亞後裔。結果,整個社會都普遍地以一個所謂的經典「香港故事」來理解香港,並以此簡明但脫節的「香港故事」來迎接原不可知的未來。可是,當孕育這個經典「香港故事」的時空不再,香港所處的權力格局就不得不隨之而變更,原有單向線性的歷史敘事也不得不隨之調整。
本文集的主要貢獻在於收錄了不同學者對此重要轉變的新近研究。這些研究好讓我們有一大發現:昔日的「香港故事」雖然正在失效,卻沒有被大眾常識中新建的「常規」完全取代,因而整體局面總是內藏大量新舊張力和變數。就此,這些研究又提供了兩大線索,好讓我們可以重新思考後九七香港的自我構成如何呈現根本的範式轉移。第一,香港的政治權力格局的重構(尤其是新興政治力量的冒起)和媒體運作條件的改(尤其是新媒體的日益重要),使得任何對大眾事務的觀點和方案都必須面對眾聲喧嘩的洗禮。第二,這些觀點和方案,儘管看起來是為特定力量服務,甚或由特定力量激發出來,往往是頗為混雜含糊,自相矛盾,甚至具有自覺或不自覺的顛覆性。這些研究亦在不同的層面,以不同的題材,相互對照和補充,並可分為以下三大主題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