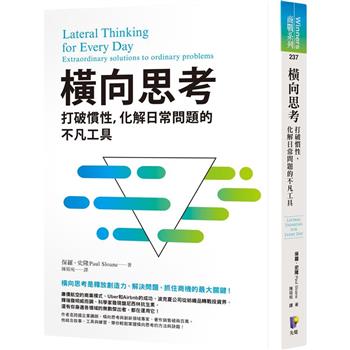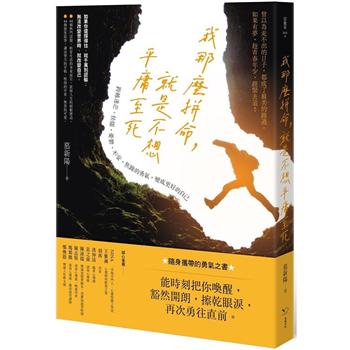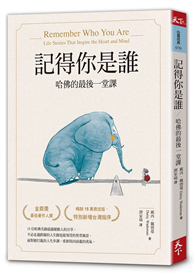二十世紀落幕了。英國歷史學家霍布斯邦在歐洲的視角內,將這個世紀界定為從1914年世界大戰爆發至1991年蘇東解體為止、作為“極端的年代”的短二十世紀。與他的看法不同的是,在本書中,作者將中國的二十世紀界定為從1911至1976年的作為“漫長的革命”的短二十世紀——這是一個極端的但同時也是革命的時代。
本書作者論述了中國在這個“短世紀”中的兩個獨特性:第一個獨特性集中於這個“短世紀”的開端,即在革命建國過程中的帝國與國家的連續性問題。第二個獨特性集中於這個“短世紀”的終結,即革命與後革命的連續性問題。全書由10篇論文組成:
1. “亞洲覺醒”時刻的革命與妥協
2. 文化與政治的變奏
——論中國的“短二十世紀”的開端
──戰爭、革命與1910年代的“思想戰”
3. 二十世紀中國歷史視野下的抗美援朝戰爭
4. 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權的多重構成與六十年代的消逝
5. 1989社會運動與中國“新自由主義”的歷史根源
6. 自主與開放的辯證法
——再論當代中國大陸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
——寫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六十周年之際
7. 兩種新窮人及其未來
8. 代表性斷裂與“後政黨政治”
──“後階級社會”的階級問題及其尊嚴政治
9. 代表性的斷裂
10. 兩岸歷史中的失蹤者
——再問“什麼的平等”?
──《臺共黨人的悲歌》與臺灣的歷史記憶
作者簡介:
汪暉,中國大陸近十年來最受爭議的知識分子、學者,被譽爲新左派領袖,現任清華人文與社會高等研究中心執行主任。曾任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博士後研究、美國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華盛頓大學訪問學者、柏林高等研究所、海德堡大學研究員。汪暉目前研究工作集中於現代中國思想的研究。主要著作有:
1. 《去政治化的政治:短二十世紀的終結與九十年代》
2. 《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四卷本),增訂版2008
3. 《死火重溫》
4. 《亞洲視野:中國歷史的敍述》
章節試閱
“亞洲覺醒”時刻的革命與妥協
──論中國的“短二十世紀”的開端
一、中國的短二十世紀:兩個獨特性
二十世紀終於落幕了。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站在歐洲的視角內,將這個世紀界定為從1914年世界大戰爆發至1991年蘇東解體為止的、作為“極端的年代”的短二十世紀。與他所界定的從1789-1848年的“革命的年代”形成了對比,“極端的年代”充斥著暴力卻並不蘊含類似“雙元革命”(法國革命和英國工業革命)所提供的那種創造性的歷史遺產。與他的看法有所不同,在《去政治化的政治》一書中:我將中國的二十世紀界定為從1911-1976年的作為“漫長的革命”的短二十世紀這是一個極端的但同時也是革命的時代。辛亥革命正是這個“漫長的革命”的偉大開端──不僅是中國的短二十世紀的開端,而且也可以視為”亞洲的覺醒”的一系列開端性事件中影響最為深遠的事件。將這兩個相互重疊但視角不同的”短二十世紀”拼合在一起,我們可以分辨出二十世紀中國在這個”短世紀”中的兩個獨特性:
第一個獨特性集中於這個“短世紀”的開端,即在革命建國過程中的帝國與國家的連續性問題。二十世紀是以亞洲的民族革命和憲政民主為開端的,我們可以將的1905年俄國革命、1905-1907年伊朗革命、1908-1909年土耳其革命、1911年中國革命視為“亞洲的覺醒”的開端性事件。1911年中國革命在極短的時間內建立了亞洲第一個共和國,這使得這場革命具有真正開端的意義。我將1905年俄國革命也放在亞洲革命的序列中,不僅因為它的直接觸發點是爆發在清朝境內的日俄戰爭及俄國的戰敗,而且這場戰爭和革命催化了中國民族革命的進程(正是在這一年,同盟會成立)及共和與改良的大辯論,同時也為伊朗革命和此後的土耳其革命提供了靈感。我們可以將“亞洲的覺醒”與第一吹世界大戰作為帝國崩潰的時代:1905年革命失敗了,但幅員廣大、民族複雜的俄羅斯帝國衰相漸露,最終在革命與戰爭的硝煙中崩潰;俄國革命與民族主義力量相伴而行,民族自決的原則在波蘭、烏克蘭等周邊地區獲得勝利,儘管此後各周邊民族以”加盟共和國”的形式加入蘇聯,但1991年的事件顯示了蘇聯架構與民族原則的深刻聯繫﹔ 1919年,誕生於1867年的奧匈帝國分崩離析,奥、匈各自建立共和國,原來寄居在奧匈帝國框架下的較小民族獲得了民族國家的地位;奧地利社會民主黨設想的那種在帝國範圍內實行革命與變革的民族主義構想(以奧托鮑威爾Otto Bauer為理論代表)徹底失敗了﹔奧斯曼帝國廣土眾民、橫跨歐亞,它的帽起是促成歐洲海洋探險時代的世界歷史事件,但在一戰的硝煙之中,從稍早的革命中倖存下來的帝國趨於崩潰,新生的土耳其脫離了原有的制度多元主義,轉變為一個架構相對單一、幅員大規模縮小的民族國家。在上述三大帝國的相繼崩潰中,民族主義、憲政改革與複合型帝國的崩潰是同一故事的不同側面。1918年,威爾遜的十四條宣言在民族自決的名義下將民族原則置於王朝帝國的原則之上,民族、民族主義和民族國家作為帝國的反題支配了整個二十世紀的政治邏輯。清帝國的命運初看上去跟其他帝國十分相似:1911年的一場局部起義引發了王朝體系的崩潰,分離與獨立的潮流遍及帝國的內外領域。在理論領域,種族中心論的民族主義在漢族、蒙古、西藏和回部都有迴響,革命派的思想領袖之一章太炎更是將清朝與奥匈帝國、奧斯曼帝國相比較。但令人驚異的是:在劇烈的動盪、分裂的危機和外來的入侵之後,脆弱的共和國卻在帝國原有的地域和人口的規模上維持了國家的統一性。如何解釋這一複合型帝國與主權國家之間的獨特的連續性?
第二個獨特性集中於這個“短世紀”的終結,即革命與後革命的連續性問題。在亞洲的“短二十世紀”中,以1917年的俄國革命為標誌,民族革命運動不再單一地與資產階級憲政民主相結合,而是和社會革命和某種帶有社會主義色彩的建國運動相結合。十月革命是歐洲戰爭的產物,但其中迴盪著亞洲革命的氣息,因為它延續了1911年革命將民族革命與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綱領和建國構想結合起來的路線──列寧在1912-1913年率先注意到中國革命的特殊性,即一方面, “社會主義革命... .. 將是受帝國主義壓迫的一切殖民地、一切國家和一切附屬國反對國際帝國主義的戰爭”﹔另一方面,為了在落後的農業國家發展資本主義(一種沒有資產階級的資本主義),就必須建立社會主義的國家和社會主義的行動綱領(一種沒有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運動)。所謂辛亥革命的“社會主義色彩”是指孫文的建國綱領不僅指向一場民族主義的政治革命,而且也以克服資本主義弊端為宗旨的“社會革命”為目標,其主要的內容是以平均地權及受亨利﹒喬治理論影響的土地漲價歸公的改革計劃。將民族運動與社會主義建國運動及國際革命關聯起來,是1911年中國革命區別於1905年俄國革命、1905-1907年伊朗革命、1907-1909年土耳其革命的關鍵之處,它預示了二十世紀的革命將是與十八至十九世紀、以美國革命和法國革命為代表的革命模式非常不同的革命。因此,1911年革命是1905年之後革命序列的一個重要轉捩點,或者說,不是1905年俄國革命,而是1911年中國革命,才是這個革命的(而不僅僅是作為“極端的年代”的)“短二十世紀”的真正開端。短命的辛亥革命為漫長的中國革命吹響了號角。中國革命與俄國革命,以及世界社會主義陣營的確立,改變了十九世紀
以降由單向的資本主義擴張所創造的世界圖景;因此,離開”革命”的視角,事實上不可能理解十九世紀晚期以降整個世界的圖景。然而,伴隨著冷戰的終結,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體系相繼解體,民族原則與市場一民主資本主義體系取得了雙重勝利。在西方,這一過程也被比附於更早時期的帝國解體───民族和人民從專制(蘇聯)帝國的束縛中解放出來,走向新的憲政民主。在蘇聯東歐地區,革命與後革命之間的斷裂一目了然。但為什麼在霍布斯邦所說的“極端的年代”終結之後,恰恰是中國──我們很難忘記蘇東轉變的多米諾效應來自1989年的北京──不但保持了政治結構、人口構成與國家規模的完整性,而且在社會主義國家體制的基礎上完成或正在完成一種以市場經濟為導向的大轉變?
上述兩個問題中的第一個涉及帝國與民族國家、帝制與共和的關係問題,第二個涉及社會主義國家體制與市場經濟的關係問題。正如在1911年之後的動盪與分裂的歲月中,人們難以判斷中國的未來一樣,在1989年之後,沒有人預料到中國會在政治延續的模式下獲得如此高速的經濟增長。就政治結構而言,中國的體制是1949年革命建國的產物;就國家規模和主權關係而言,當代中國的完整性卻可以追溯至清王朝與誕生於1911年革命的新生共和國之間的連續性之上。換句話說,革命與連續性的問題──不可避免地,它也可以表述為連續性中的斷裂問題──凝緊了中國的”短二十世紀”的重要秘密。無論是對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的解釋,還是對當代中國及其未來的討論,都離不開對這一問題的基本判斷。
二、革命與連續性的創制
革命與連續性的這種關聯不是歷史的宿命,也不是某種文化原理的必然產物,它們都是在特定的歷史事件中誕生的,是事件的參與者在各種歷史合力制約下的創造物。事件不僅涉及那些有形的人物和故事,思想、價值、習慣和傳統等無形的力量也參與事件的創造,並在事件的爆發中重新組合。也許可以說,沒有革命的爆發就不存在我們在這里所討論的連續性問題,但連續性卻不能看作是革命的自然延伸。1911年武昌起義及隨後在中國南方形成的“鬆散的跨省革命聯盟”並沒有力量完成全國範圍內的革命建國,1912年2月12日,在南方革命黨人與北方勢力的博弈和談判之後,清帝下詔遜位,革命派、立憲派和北洋集團在“五族共和”的旗幟下形成了一個出人意料的妥協,初期的革命建國運動由此展開為一系列曲折、複雜和動盪的事件。如何估價這一進程?首先對南北妥協及清帝遜位詔書在清朝與民國的主權繼承關係上的影響作出論述的,是日本憲法學家有賀長雄。他在發表於1913年的文章《革命時代統治權轉移之本末》中,將主權問題從革命建國(武昌起義及南京臨時政府成立)轉向南北議和及清帝遜位詔書,提出中華民國的主權係由清帝“禪讓”而來。有賀氏的身份是袁世凱的憲法顧問,他的法理論述有看清晰的政治目標,即為袁世凱擔任民國大總統提供合法性。他後來也直接參與了袁氏帝制復辟的活動。在革命史的敘述中,南北議和、清帝遜位、袁世凱被選為臨時大總統只能是革命不徹底以至失敗的標誌。事實上,清帝遜位後,當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的名義施行內政、外交時,孫文明確指出“共和政府不能由清帝委任組織”,其後又在國民黨一大宣言中就革命後“與反革命的專制階級謀妥協”問題做了自我反省。但是,南北議和最終在”五族共和” 這一點上達成妥協,可以作為透視民國的興替關係或“連續性的創制”的一個窗口。由於“主權在民”的最高原則的確立,這一妥協只是主權連續性創制的一個環節。在“短二十世紀”的“漫長的革命”中,新的門爭是圍繞誰是“人民”、如何界定“人民”、誰代表“人民”這一現代革命的中心問題而展開,但上述妥協的結果仍然難以繞過,這是因為在隨後發生的帝制復辟、五四運動、南北戰爭、抗日戰爭、國共博弈,以及圍繞國際承認而展開的內外鬥爭中,重建和更新這一連續性而不是否定或拋棄這一連續性,成為不同政治力量隱而不宜的前提。即便在反對袁世凱稱帝的“護國戰爭”中,聲稱“獨立”的各省也並不以分離主義為訴求,而是以重建統一的民國為前提。在世界各大帝國──哈布斯堡、霍亨佐倫、羅曼諾夫、奧斯曼──相繼解體的時刻,中國的各種政治力量──舊的與新的───逐鹿中原的政治目標已全然以獲取國家統一為前提。
三、帝國與國家、北方與南方
霍布斯邦說,如果要為十九世紀尋找一個主題的話,那麼,這個主題就是民族國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民族國家取代帝國成為二十世紀的主要故事,民族主義、人民主權、憲政體制、主權單一性、條約及談判構成了戰後民族主義敘事的主要方面,與之相對立的就是帝國、君主權力、專制政體、多元宗主關係
、朝貢及軍事征服。不但在民族主義的敘事中,“走向共和”就是從帝國走向民族國家的政治過程,而且在國際政治領域,主權已經是一個與民族國家規範性地相互關聯的領域。在歷史研究領域,國家建設、民族主義、大眾動員、公共領域,沒有一個不是與民族國家這一範疇緊密相關。
但是,本文開頭提及的第一個獨特性,即在革命中誕生的帝國與國家的連續性問題,卻在這個順暢的敘述中留下了一些值得思考的問題。首先,如上文已經論述,與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各大帝國在“走向共和”過程中分裂為多個民族國家、或加盟共和國不同,辛亥革命在“五族共和”的口號下通過“大妥協”完成了清朝與民國的主權轉讓,主權連續性成為此後國內政治博弈的規範前提。在蘇聯崩潰後,中國是前二十世紀農業帝國中唯一一個將這種連續性維持至二十一世紀的國家。其次,帝國向民族國家的轉化有一系列的歷史前提。就前一方面看,在清代歷史中,帝國建設與國家建設存在著若干重疊,但這些重疊並不能等同於從帝國向國家過渡的自然進程。從清朝入關,到十八世紀普遍性的帝國體制的形成,再到十九世紀中後期由於西方列強的侵迫和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簽訂而發生的一些制度改革,清朝的內外關係持續發生者變化。劃定邊界,實施邊界內的行政管轄權,核定貿易准入及其規模等通常被視為民族國家標誌的現象,在清朝的對外關係──尤其是北方內陸關係──中早已存在,並不斷發展。1884年新疆建省也是這一進程的有機部分,它說明多元權力中心的帝國體制不是僵固不變的,主權單一化的過程也是帝國體制自我鞏固的產物。就後一方面看,現代中國不僅在族群關係、宗教關係和地緣關係上承續了清朝的遺產,並通過主權轉讓使其合法化,而且在其後的制度設計中也保留了諸如民族區域自治這樣的多元體制安排──從革命的視野來看,這些制度安排所體現的社會內容(如土地改革的不同進度及不同方式等等)也正是“必要的妥協”。1997年香港回歸、1999年澳門回歸標誌著歐洲殖民主義帝國體制的正式終結,但特別行政區制度卻可以視為某種帝國時代宗主權在民族一國家時代的變體。正如帝國內部的集中化趨勢不能視為民族國家的萌芽而是帝國建設的一部分一樣,民族區域自治不能視為帝國遺產的自然遺存,而是歷史傳統在新的主權原則和民族平等原則下產生的新型創制。即便在一百年之後,中國西南、西北的自治區城及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的矛盾和衝突也仍然與這一帝國-國家的複合關係有著歷史的關聯。這些現象表明帝國與國家無法清晰劃定為兩種截然不同的政治體。如果清朝與民國的主權連續性標誌著中國的獨特性,那麼,帝國與民族國家相互滲透的現象卻是普遍的。我們可以在美國、俄國、印度和許多“民族國家”體制及其行為方式中發現“帝國的"要素。在二十一世紀,曾經被視為十九至二十世紀資本主義最適合的政治外殼(列寧語)的民族國家越來越捉襟見肘,資本主義世界正在被人們描述為帝國。伴隨著二十世紀的落幕,歷史學家們發現從帝國到民族國家的敘述過於單一,兩者之間實際上存在看許多交叉重疊,那些被歸結為帝國的特徵不但存在於過去和現在,而且還在歐洲的區域整合進程中顯示著某種新的政治形態。在這個意義上,帝國形態與民族一國家形態本身並不提供褒貶的根據,人們需要根據不同政治體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的存在狀態對之進行判斷,即相對單一的族群構成與多族群構成的政治形式本身,並不提供政治判斷或道德判斷的根據。判斷政治體的根據是歷史性的和政治的。
在革命爆發的背景下產生的上述連續性是一場錯綜複雜的戲劇性產物。幕前的每一個勢力──南方革命黨人、袁世凱為代表的北方力量(軍人集團、蒙古勢力及不贊成共和的北方省份)、皇室,以及立憲派人士──有著各自不同的利益訴求和政治目標, 但都認同“合滿、漠、蒙、回、藏五族完全領土,為一大中華民”(《遜位詔書》)這一前提。即便處於南北戰爭狀態,這一前提本身也從未喪失合法性。如何解釋這一現象?怎樣分析主權連續與革命-反革命的關係?
為了解釋這一問題,需要先看晚晴與民國初期以北方與南方、內陸與海洋的分野而展開的兩種中國觀。這兩種中國觀並不單純是地域性的,其中也包括了政治價值:前者是以清朝地域和人口為中心的多民族共同體,晚清立憲派的君主立憲、虛君共和及相對於“內競的”漢族民族主義而言的“外競的”大民族主義”,就是這一多民族共同體的政治表達;後者是以傳統明朝地域反其人口為中心的漢人共和國,晚清革命者的排滿革命主張、漢族民族主義(國粹主義)和“主權在民”理論都是這一漢人或以漢人為絕對中心的民族國家的合法性根源。革命黨人的“排滿主張”是一種政治革命的訴求,並不必然或全然等同於“漢人民族主義”,但說其中若隱若現地存在著一種漢人共和國的構想是有大量歷史資料的根據的。革命史學歷來以南方、海洋為中心,這與同盟會及其前身興中會、光復會、華興會展開革命活動的中心區域有看密切的關係。1980年代,海外史學界曾發生過革命中心到底在南洋還是在國內──主要是兩湖和湖江──的爭論,但從更為寬廣的視野看,後者不但與海外華人想像的以明代中國版圖為中心的中國完全重壘,而且也與近代史學的海洋中心論相互呼應。中國學術界對於晚清洋務運動、工商業發展、沿海城市及新興階級及團體的出現做了大量的研究,若將這些工作與有關革命活動在美洲、日本和南洋的研究綜合起來,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支持革命活動和革命活動得以展開的南方-沿海的地域脈絡。海洋中心論是與資本主義的全球性發展密切相關的。海外華人深受種族歧視之苦,他們對中國的理解與反清復明的訴求相互糾纏,“如果中國的政府是由漢人而非滿人組成,海外華人大規模參與辛亥革命的情形恐怕不會發生。”這一點正好與孫中山等人的“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民族主義思想相互激盪。在革命之後,革命黨人迅速調整了他們的反滿民族主義主張,明確地以“五族共和”相標榜,但我們也不難在鄒容、陳天華、章太炎、孫中山、汪精衛、朱執信等人的革命思想中找到脫離大清而獨立建立漢人共和國的因數。1911年武昌起義後鄂軍都督府發佈的文稿和全國通電,均以漢人居住的“十八省”相號召,以致很容易讓人產生革命等同於依循明朝版圖建立漢人的、獨立的民族國家的錯覺。從實際的政治勢力分佈來看,南京臨時政府及參議院的席位也完全為內地省份代表和漢人所佔據,這與革命後南方與北方形成兩個政府的格局正好相互對應。
“亞洲覺醒”時刻的革命與妥協
──論中國的“短二十世紀”的開端
一、中國的短二十世紀:兩個獨特性
二十世紀終於落幕了。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站在歐洲的視角內,將這個世紀界定為從1914年世界大戰爆發至1991年蘇東解體為止的、作為“極端的年代”的短二十世紀。與他所界定的從1789-1848年的“革命的年代”形成了對比,“極端的年代”充斥著暴力卻並不蘊含類似“雙元革命”(法國革命和英國工業革命)所提供的那種創造性的歷史遺產。與他的看法有所不同,在《去政治化的政治》一書中:我將中國的二十世紀界定為從1911-1976年...
作者序
在1911年革命尚在孕育之中的時刻,1907年,年僅26歲的魯迅在一篇古文論文中,用一種古奧的文風,談及他對剛剛降臨的世紀”的觀察:
意者文化常進於幽深,人心不安於固定,二十世紀之文明,當必沉邃莊嚴,至與十九世紀之文明異趣。新生一作,虛偽道消,內部之生活,其將愈深且強歟?精神生活之光耀,將愈興起而發揚歟?成然以覺,出客觀夢幻之世界,而主觀與自覺之生活,將由是而益張歟?內部之生活強,則人生之意義亦愈邃,個人尊嚴之旨趣亦愈明,二十世紀之新精神,殆將立狂風怒浪之間,恃意力以闢生路也。
魯迅用兩句話概括了他所說的“二十世紀之新精神”,即“掊物質而張靈明,任個人而排眾數。”這兩句話中的“物質”指由英國工業革命所引導的“十九世紀物質文明”,即資本主義經濟﹔”眾數”則指由法國大革命所開創的”十九世紀政治文明”,即憲政民主及其議會一政黨制度。魯迅宣稱:”十九世紀”,的創造力在其世紀末已經式傲,自由平等正在轉變為凌越以往專制形式的新的專制形式。因此,正在降臨的新世紀為中國所確定的目標是超越歐洲雙元革命及其後果,建立一個每一個人都獲得自由發展的“人國”。
這是中國歷史中最早的關於”二十世紀”的表述之一。對於當時的中國人而吉,這個概念如同天外飛來的異物,因為在此之前,並不存在所謂”十九世紀”,也不存在”十八世紀”。1907年是光緒丁未年,或清光緒三十三年。光緒是滿洲入關後的第九位皇帝。在魯迅的文章中,作為”二十世紀”對立面的”十九世紀”並非指涉此前的中國歷史,而是由法國革命和英國革命所開創的歷史時代。但對於魯迅而言,只有將”二十世紀”這一異物作為我們的使命,中國才算獲得了”自覺”。為什麼如此呢?因為十九世紀歐洲的”雙元革命”正是晚清中國的改革和革命浪潮所確立的目標。從1860年代起,在兩次鴉片戰爭失敗的陰影下,中國開始了以富國強兵為內容的”洋務運動”;伴隨甲午戰爭(1894)的失敗,這場”師夷長技以制夷”的運動直接地轉變為以戊戌變法為標誌的政治改革運動,其內容之一,便是模仿歐洲立憲政治,建立國會,將王朝改變為”國家”。這場政治改革運動的失敗標誌著一個民族革命時代的降臨,在洶湧澎湃的革命浪潮中,共和國正在平地線的另一端漸漸升騰,而推動這個新中國誕生的力量不就是歐洲的民族主義、市場經濟、物質文明和政治體制嗎?因此,即便中國不存在西歐和俄國意義上的”十九世紀”,為了超越晚清改革和革命的目標,”二十世紀”也將是中國的使命或獲得”自覺”的契機。
在這個意義上,”二十世紀”不僅是”十九世紀歐洲”的異物,也是內在於”二十世紀中國”的異物。異物不是一個,而是許多個:倡導”君主立憲”的康有為同時寫作了不但超越他自己提出的”君主立憲”主張而且超越整個”十九世紀”全部內容的《大同書》,呈現了一幅綜合了儒家思想、佛教理念和烏托邦共產主義的世界圖景;激進的民族革命者章太炎用”齊物平等”的思想深刻地批判了”十九世紀”的國家主義、種族主義、政黨政治、憲政民主和形式平等,他本人也成為這場革命運動內部的”異類”;即便是1911年革命的領袖孫文也試圖將兩場對立的革命-即”十九世紀”的民族革命和富強運動與”二十世紀”的社會革命──綜合為同一場革命。如果主權國家;民族認同、政黨政治、公民社會、工業革命、城市化、國家計畫、市場經濟,以及與之相適應的教育體制和媒體文化,構成了這一時代中國社會變革的基本內容,那麼,作為異物的”二十世紀”就潛伏於其內部。換句話說,二十世紀中國的大部分變革內容乃是”漫長的十九世紀”的延伸或衍生,但又內在地包含了其對立面和否定物。用魯迅的語言來說,即”二十世紀之新精神,殆將立狂風怒浪之間,恃意力以闢生路也。””意力”表達的是一種能動性,一種超越客觀條件而從事創造的能量,但這種超越客觀條件的創造性能量並不是純粹的主觀性,而是一種將鬥爭目標納入更廣闊範圍的產物。
在中文裏,”政治”的含意取決於句體的語境,但並不存在political與politics之間的嚴格區分。在一個多民族帝國的地基上創建一個單一主權的共和國,同時讓單一主權國家內在地包含了制度的多元性; 通過否定政黨和國家的文化運動來界定新的政治,同時創造出一種區別於歐洲十九世紀的政黨和國家的政治類型;以人民戰爭的形式推進土地改革、政權建設及政黨與大眾之間的循環運動,形成一種具有超政黨要素的超級政治組織,在一個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均未成熟的社會裏推進一場指向社會主義的階級運動,將政治性和能動性展開為階級概念的重要內容......總之,在一個以多民族的農業帝國裏不但發生了階級政治,而且發生了“社會主義革命”,這一現象不能直接從現實條件內部推演出來,毋寧是政治化的產物。 。
2004年,在為《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所寫的序言中,我曾說:”在漫長的二十世紀裏,中國革命極其深刻地改變了中國社會的基本構成,我們不可能僅僅在”中國”,這一範疇的延續性中說明現代中國的認同問題。我希望今後的研究能夠在這方面提供新的歷史解釋。”我想補充的是:也正是這個世紀將“中國”
帶入了一個難以從“過去”中衍生而來的時代,從而任何對於”中國”的界定都無法離開對於這個世紀的解釋。這本論文集就是從《興起》結束的地方開始的,他集中於探索二十世紀中國及其政治過程。在過去十年中,我已經將“二十世紀” 從“漫長的”修訂為“短促的”,其核心部分是從1911年辛亥革命前後至1970年代中期“文革”結束前後的“作為短世紀的漫長的革命”。在這個世紀中,政治化與去政治化是相互糾纏、反復出現的現象,但也可以視為不同時期的主導趨勢。因此,我們不妨從政治化、去政治化和重新政治化的脈絡探索這個世紀的潛力。
我從三個路徑出發思考二十世紀中國的政治化,即政治整合、文化與政治、人民戰爭。這三個主題誕生於革命與戰爭的時代,但又以不同的形式出現於其他歷史時期。政治整合將對國家形式的探索展開為一個政治競爭的過程──這裏所指的政治競爭不僅是不同政治力量之間的競爭,而且是不同的政治原理之間的競爭,從這一激烈的競爭過程中產生的”國家”包含了強烈的政治性,因此,僅僅抽象地說明”國家”或“民族一國家”是無法把握“國家”與政治過程的關係的,持續的文化運動刷新了對於政治的理解,重新界定了政治的議題和領域,創造出一代新人;人民戰爭不但是從根本上改變現代中國城鄉關係和民族認同的政 治動員過程,而且也對我們熟悉的政治範疇如階級、政黨、國家、人民等等進行了改造與重構。離開了政治化的複雜過程,我們幾乎不能歷史地把握這些政治範疇在二十世紀語境中的獨特意義。這三種政治化的過程滲透在整個二十世紀中國的方方面面:政治化既體現為激進的革命與策略性妥協的過程,也表現為將青年問題、婦女解放、勞動與勞工、語言與文學、城市與鄉村等等問題納入“文化”的範疇,讓政治成為一個創造性的領域﹔既體現為將軍事門事、土地改革、政權建設、統一戰線融為一體的“人民戰爭”,也呈現為人民戰爭對十九世紀以降的各種政治範疇的轉化,例如政黨與大眾運動之間的邊界模糊了,政權不同於傳統的國家機器,階級成為階級化過程(如農民成為無產階級政治力量),等等。在1950-1960年代,即便在主權概念籠罩之下的國際政治領域,抗美援朝戰爭和中蘇兩黨論戰,也提供了軍事和國際關係領域的政治化案例。
二十世紀的政治創新是與持續的戰爭、革命和動盪密切相關的。伴隨1989-1992年的世界性轉變,由中國革命和俄國革命為標誌的社會主義運動以失敗告終。“短世紀”以這一悲劇性的方式告終為人們理解二十世紀提供了一種否定性的視角,即將政治化過程本身視為悲劇的根源,進而拒絕一切與這個世紀的政治直接相關的概念──階級、政黨、民族、國家、群眾和群眾路線、人民和人民戰爭等等。然而,這些概念在什麼時候、在什麼意義上是政治化的,又在何種條件下趨向於去政治化?以階級概念為例,它在二十世紀的政治動員中產生了巨大的作用,但這種動員包含了兩種可能性:其一,即便在身份或財產權意義上並不隸屬於某個階級,也可以成為某一階級的馬前卒或戰士,如農民或出身統治階級的知識分子成為“無產階級”的主體甚至領袖;其二,階級出身成為僵固不變的制度化的身份標記,成為衡量敵我的基本標準。兩者都可能產生動員,但前者是政治化的,後者卻是去政治化的。再以政黨為例,人民戰爭條件下的政黨與群眾路線有著密切的聯繫,所謂“從群原中來,到群眾中去”,由此產生了巨大的政治能量和活力﹔但在執政條件下的政黨卻常常與群眾相互隔絕,蛻變為一般性權力機器,形成了政黨國家化的現象,亦即政黨的去政治化現象。因此,與許多試圖在這些範疇之外尋找新政治的方法有所不同,我試圖對這些範疇自身及其演變進行分析,從中理解政治化與去政治化的樞紐和邏輯;即便這些範疇全部源自“十九世紀”,我也試圖從中找到內在於它們的異物,因為正是這些異物使得這些舊範疇在特定語境中煥發出巨大的能量。
在同一個意義上,探尋新的政治也不可能離開對於這些異物的解釋。從對文化政治的解釋到對人民戰爭及其演變的思考,從對後政黨政治的追溯到對齊物平等的研究,本書的各個章節就是對於這些內在於二十世紀政治實踐的異物及其可能性的探究。就像布洛赫(Ernst Bloch)筆下的“希望”一樣,作為被壓抑的現實,異物很可能會以新的形態、在不同以往的關係中,作為未來再度出現於我們的時代。
在1911年革命尚在孕育之中的時刻,1907年,年僅26歲的魯迅在一篇古文論文中,用一種古奧的文風,談及他對剛剛降臨的世紀”的觀察:
意者文化常進於幽深,人心不安於固定,二十世紀之文明,當必沉邃莊嚴,至與十九世紀之文明異趣。新生一作,虛偽道消,內部之生活,其將愈深且強歟?精神生活之光耀,將愈興起而發揚歟?成然以覺,出客觀夢幻之世界,而主觀與自覺之生活,將由是而益張歟?內部之生活強,則人生之意義亦愈邃,個人尊嚴之旨趣亦愈明,二十世紀之新精神,殆將立狂風怒浪之間,恃意力以闢生路也。
魯迅用兩句話概括了他所說的...
目錄
1“亞洲覺醒” 時刻的革命與妥
-----論中國的”短二十世紀”的開端
一、 中國的短二十世紀:兩個獨特性
二、 革命與連續性的創制
三、 帝國與國家、北方與南方
四、 民族自決與”落後的北方”
五、 三種政治整合:議會多黨制、行政集權與革命建國
33文化與政治的變奏
-----戰爭、革命與1910年代的”思想戰”
序論:”覺悟”的時代
一、 從”文明衝突”到”文明調和”
二、 洪憲帝制、政體危機與”新舊思想”問題
三、 調和論與二十世紀新(舊)文明
111二十世紀中國歷史視野下的抗美援朝戰爭
一、”對中國、對朝鮮、對東方、對世界都有利”:
抗美援朝戰爭的歷史條件
二、人民戰爭轉向國際主義聯盟戰爭的政治意義
三、並非結論:停戰體制與去政治化條件下的戰爭
161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權的多重構成與六十年代的消逝
一、 中國與六十年代的終結
二、 去政治化的政治與黨國體制的危機
三、 去政治化的政治與現代社會
四、 霸權的三重構成與去政治化的政治意識形態
231 1989年社會運動與中國”新自由主義”的歷史根源
------再論當代中國大陸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
一、1989年社會運動的歷史條件與”新自由主義”的反歷史解釋
二、1990年代的三個思想階段及其主要問題
三、為什麼從現代性問題出發
305自主與開放的辯證法
-----寫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六十周年之際
一、 獨立自主及其政治內涵
二、 農民的能動性
三、 國家的角色
四、 主權結構的變異
五、 政黨國家化的悖論
六、 金融危機還是經濟危機
329兩種新窮人及其未來
-----階級政治的衰落、再形成與新窮人的尊嚴政治
前言
一、 新窮人與新工人的誕生
二、 不確定的主體:農民工、工人階級或新工人?
三、 打工短期化、法律維權與政治正義
四、 工人國家的失敗與代表性的斷裂
371代表性斷裂與”後政黨政治”
一、 全球政治的代表性危機
二、 重構二十世紀中國的代表性政治原理
三、 “後政黨政治”的條件
四、 理論辯論與政黨的”自我革命”
五、 人民戰爭與群眾路線
六、 階級重組與階級政治的衰落
七、 “後政黨政治”與憲政改革的方向
389代表性的斷裂
----再問”甚麼的平等”?
序言:政治體制與社會形式的脫節
一、 再問”什麼的平等”?
二、 齊物平等與”跨體系社會”
453兩岸歷史中的失蹤者
----《臺共黨人的悲歌》與臺灣的歷史記憶
489當代中國歷史巨變中的臺灣問題
----從2014年的”太陽花運動”談起
一、 兩岸政治關係的危機與統派的式微
二、 反服貿運動與反TPP
三、 政治認同的至關重要性與兩種規則的衝突
525人名索引
1“亞洲覺醒” 時刻的革命與妥
-----論中國的”短二十世紀”的開端
一、 中國的短二十世紀:兩個獨特性
二、 革命與連續性的創制
三、 帝國與國家、北方與南方
四、 民族自決與”落後的北方”
五、 三種政治整合:議會多黨制、行政集權與革命建國
33文化與政治的變奏
-----戰爭、革命與1910年代的”思想戰”
序論:”覺悟”的時代
一、 從”文明衝突”到”文明調和”
二、 洪憲帝制、政體危機與”新舊思想”問題
三、 調和論與二十世紀新(舊)文明
111二十世紀中國歷史視野下的抗美援朝戰爭
一、”對中國、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