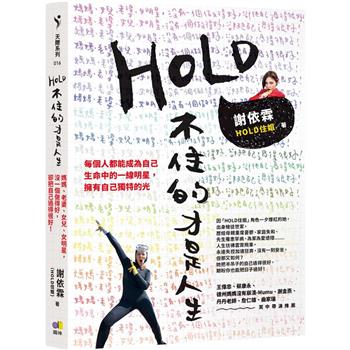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社會學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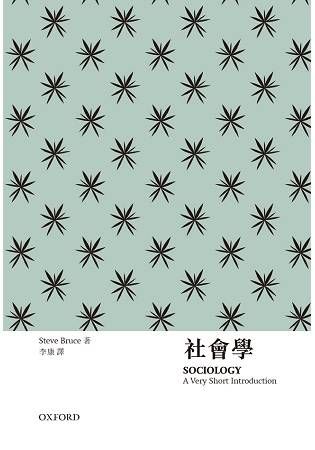 |
社會學 作者:Steve Bruce / 譯者:李康 出版社:牛津大學 出版日期:2016-08-01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220 |
二手中文書 |
$ 237 |
社會學 |
$ 279 |
中文書 |
$ 279 |
社會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社會學
內容簡介
布魯斯此書出色地完成了一件艱鉅的任務,很少社會學家能有這樣的自信和把握能力,全書的論述既具檃議性又見出作者的智慧和學識,文筆簡潔淺白易讀。
序
序言
社會學既廣受歡迎,又備遭痛責,而這正是它的力量的體現。比它更早確立的那些學科門類嘲笑它是個缺乏經驗的新手,但卻採納了它的某些視角。而普通人也在譏諷那些職業從事社會學的人的同時,又不加思索地接受了它的一些假定。至於政府,則一方面指責它是一門暗中破壞道德和社會紀律的學科,另一方面卻又僱用着社會學家來評估自己的政策。
透過這等荒唐局面的發生頻度和內在性質,可以看出我們對這門學科的擔憂。這或許是出於我職業性的多疑,但從某種角度上來說,社會學家面臨着荒唐,而歷史學家卻似乎並無這等遭遇。鑒於諸如此類的幽默之語並不能絕好地傳達箇中滋味,我只想舉一個例子。這個絕妙之例取自英國一部叫做《放風者》(Minder ) 的電視片集,是八十年代一部精彩的喜劇片,講的是一幫小流氓和倫敦的下等生活。有兩個挺招人喜歡的小混混討論着他倆共同的老相識,一個剛從監獄裏放出來的傢伙。一個宣稱,他倆的朋友在監獄裏一直在學習,如今已是大有進步:「哈,他現在已經拿了個公開大學* 的學位,社會學的。」第二個問道:「那他現在再也不偷了?」頭一個回答說:「哪兒啊!不過他現在可明白自己為啥會幹這活兒了!」
這番嘲諷套着好幾層意思:社會學對流氓有吸引力( 大概是因為它主要研究的是各種社會問題);社會學揭示了個人行動背後的社會起因,從而解除了人的責任感;社會學天真幼稚,可任由老於世故的人擺弄。至於這門學科是否真的該當這些指控中的某一項甚或全部,讀完這本入門書就會清楚了。
比起自然科學家來,社會科學家們會發現更難在彼此之間達成共識。箇中緣由我們讀下去就會明白了。譬如說,處在物理學前沿的研究者們可能會發生激烈的爭論,但面對一本入門性的物理學教科書,用權威性的口吻陳述已經被這門行當認可的基本知識,已經初步摸清這學科門道、出了師的學徒們是會建立起充分的共識的。與此相反,各種入門性的社會科學教科書常常會把自己的科目描述成一系列彼此相爭短長的視角。在此強調是甚麼使我們相互分離,我想會有些益處。如果我們打算對社會世界的某個方面給出說明,那就得特別關注這些視角各自的邏輯推論,這樣就很容易理解這些需要解決的爭論。就像選舉中的政客們那樣,具體學派的擁護者們努力要使自己這伙和對手之間「涇渭分明」。但是,也就像上了台的政客們那樣,當這同一幫擁護者真正下手來做社會學(而不只是宣揚他們的社會學品牌)時,往往會退回某種共同的中間立場。
這是一本通識入門,篇幅安排的局促倒使我免了全面系統地勾畫這門學科的責任。相反,我打算努力傳遞出社會學眼光的獨到本質。這將分三步來完成。首先,我會考察說社會學是一門社會科學的講法意味着甚麼,以此來說明這項事業的地位。在第二、三、四章裏,我會嘗試說明這門學科的一些最基本的假設。而在最末一章中,我會努力揭穿一些不幸頗為盛行的名不副實者的面目,把他們清除出社會學,從而澄清這項事業。
社會學既廣受歡迎,又備遭痛責,而這正是它的力量的體現。比它更早確立的那些學科門類嘲笑它是個缺乏經驗的新手,但卻採納了它的某些視角。而普通人也在譏諷那些職業從事社會學的人的同時,又不加思索地接受了它的一些假定。至於政府,則一方面指責它是一門暗中破壞道德和社會紀律的學科,另一方面卻又僱用着社會學家來評估自己的政策。
透過這等荒唐局面的發生頻度和內在性質,可以看出我們對這門學科的擔憂。這或許是出於我職業性的多疑,但從某種角度上來說,社會學家面臨着荒唐,而歷史學家卻似乎並無這等遭遇。鑒於諸如此類的幽默之語並不能絕好地傳達箇中滋味,我只想舉一個例子。這個絕妙之例取自英國一部叫做《放風者》(Minder ) 的電視片集,是八十年代一部精彩的喜劇片,講的是一幫小流氓和倫敦的下等生活。有兩個挺招人喜歡的小混混討論着他倆共同的老相識,一個剛從監獄裏放出來的傢伙。一個宣稱,他倆的朋友在監獄裏一直在學習,如今已是大有進步:「哈,他現在已經拿了個公開大學* 的學位,社會學的。」第二個問道:「那他現在再也不偷了?」頭一個回答說:「哪兒啊!不過他現在可明白自己為啥會幹這活兒了!」
這番嘲諷套着好幾層意思:社會學對流氓有吸引力( 大概是因為它主要研究的是各種社會問題);社會學揭示了個人行動背後的社會起因,從而解除了人的責任感;社會學天真幼稚,可任由老於世故的人擺弄。至於這門學科是否真的該當這些指控中的某一項甚或全部,讀完這本入門書就會清楚了。
比起自然科學家來,社會科學家們會發現更難在彼此之間達成共識。箇中緣由我們讀下去就會明白了。譬如說,處在物理學前沿的研究者們可能會發生激烈的爭論,但面對一本入門性的物理學教科書,用權威性的口吻陳述已經被這門行當認可的基本知識,已經初步摸清這學科門道、出了師的學徒們是會建立起充分的共識的。與此相反,各種入門性的社會科學教科書常常會把自己的科目描述成一系列彼此相爭短長的視角。在此強調是甚麼使我們相互分離,我想會有些益處。如果我們打算對社會世界的某個方面給出說明,那就得特別關注這些視角各自的邏輯推論,這樣就很容易理解這些需要解決的爭論。就像選舉中的政客們那樣,具體學派的擁護者們努力要使自己這伙和對手之間「涇渭分明」。但是,也就像上了台的政客們那樣,當這同一幫擁護者真正下手來做社會學(而不只是宣揚他們的社會學品牌)時,往往會退回某種共同的中間立場。
這是一本通識入門,篇幅安排的局促倒使我免了全面系統地勾畫這門學科的責任。相反,我打算努力傳遞出社會學眼光的獨到本質。這將分三步來完成。首先,我會考察說社會學是一門社會科學的講法意味着甚麼,以此來說明這項事業的地位。在第二、三、四章裏,我會嘗試說明這門學科的一些最基本的假設。而在最末一章中,我會努力揭穿一些不幸頗為盛行的名不副實者的面目,把他們清除出社會學,從而澄清這項事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