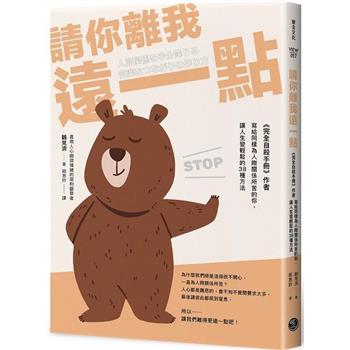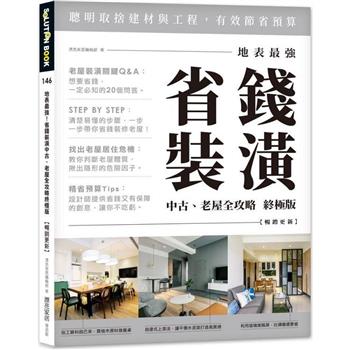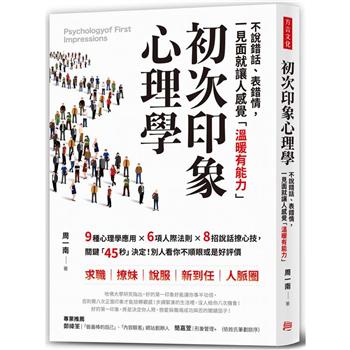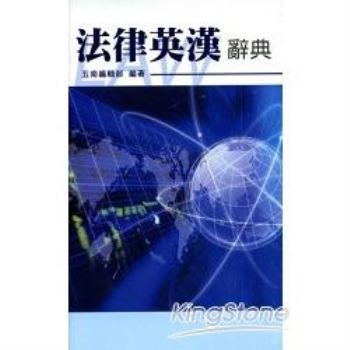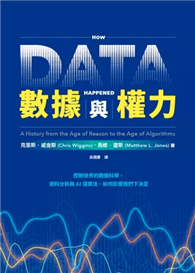第一章
理論是甚麼?
在近代的文學和文化研究中有許多關於理論的討論──我要提醒你注意的是,這可不是指關於文學的理論,而是純粹的「理論」。對任何一位不在這個圈子裏的人來説,這種用法一定顯得很怪。 「關於甚麼的理論?」你肯定會這樣問。要回答這個問題的確是意想不到的困難。它既不是任何一種專門的理論,也不是概括萬物的綜合理論。有時理論似乎並不是要解是甚麼,它更像是一種活動──一種你或參與,或不參與的活動。你有可能被捲入到理論中去,你也有可能教授或學習理論,你還有可能會痛恨或懼怕理論。只不過,所有這些對於理解甚麼是理論都不會有多大的幫助。我們被告知,「理論」已經使文學研究的本質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不過説這話的人指的不是文學理論,不是系統地解釋文學的性質和文學的分析方法的理論。比如,如今當人們抱怨文學研究的理論太多了的時候,他們可不是説關於文學性質方面的系統思考和評論太多了,也不是說關於文學與顏與眾不同的特點的爭辯太多了。遠非如此,他們指的是另外一回事。
確切説,他們指的關於綜合性問題的爭辯太多了,而這些問題與文學幾乎沒有任何關係,還有,要讀那麼多很難懂的心理分析、政治和哲學方面的書籍。理論簡直就是一大堆名字(而且大多是些外國名字),比如德里達(Jacques Derrida)、福柯(Michel Foucault)、依利格瑞(Luce Irigaray)、拉康 (Jacques Lacan)、芭特拉(Judith Butler)、阿爾都塞 (Louis Althusser)、斯皮瓦克 (Gayatri Spivak)。
那麼,理論究竟是甚麼呢?問題的一部分就在於理論這個詞本身,它指兩個不同的方面。一方面,我們可以舉「相對論」為例,那是一套已經論證過的定理。另一方面就是對理論這個詞的最普通的用法。
「勞拉和邁克為甚麼分手了?」
「噢,按照我的理論,那是因為……」
理論這個詞在這裏是甚麼意思?首先,理論表示「思考、猜測」。不過,一個理論又不同於一個猜測。如果說「我猜想那是因為……」就意味著有一個正確的答案,而我碰巧不知道,那麼就説「我猜想大概邁克總是抱怨,勞拉煩他了。不過,等他們的朋友瑪莉來了,我們就知道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了」。與之相反理論是一種判斷,不論瑪莉説甚麼都不會影響這種判斷,它是一種解釋,其正確或或謬誤都是很難證實的。「我的理論是……」也聲明你要提供一種並不顯而易見的解釋。在這樣的開場白之後,我們期待的可不是講話人接着説:「我的理論是,因為邁克與薩瑪瑟有曖昧關係。」這算不上一種理論。根本不需要甚麼敏鋭的理論才華就可以推斷出,如果邁克與薩瑪瑟有曖昧關係,當然會影饗勞拉對邁克的態度。有趣的是,假如説話人真是這樣講,「我的理論是邁克與薩瑪瑟有曖昧關係」,那麼這種曖昧關係的存在立刻就變成了一種推測,而不是確切的事實,因而也就可能成為一種理論。不過,能成為一般説來,要稱得上是一種理論,它必須不是一個顯而易見的解釋,這還不夠,它還應該包含一定的錯綜性,比如:「我的理論是勞拉一直在暗戀著他的父親,而麥克總是做不到成為他理想中的人。」一個理論必須不僅僅是一種推測:它不能一望即知;在諸多因素中,它涉及一種系統的錯縱關係;而且要證實或推翻它都不是件容易事。如果我們記住這些要素,那麼弄懂「理論」是甚麼就容易多了。
文學研究的理論並不是關於文學性質的解釋,也不是解釋研究文學的方法(儘管這些也是理論的一部分,而且本書的第二、五、六章裏也會論集這些)。理論是由思想和作品匯集而成的一個整體,很難界定它的範圍。哲學家羅蒂(Richard Rorty)對一種始於十九世紀的混合類型有過如下闡述:
從歌德、麥考利、卡萊爾和愛默生的時代開始出現了一種新類型的著作,這些著作既不是評價文學作品的相對短長,也不是思想史,不是倫理哲學,也不是關於社會的預言,而是所有這些融為一體,形成一種新的類型。
要給這種包羅萬象的類型取個名稱,最簡便的就是理論這個詞。它已經成為專指那些對表面看來屬於其他領域的思考提出挑戰,並為其重新定向的作品的詞。那麼,是甚麼使有些作品成為理論呢?以下便是最簡單的解釋。被稱為理論的作品的影響超出它們自己原來的領域。
雖然這種簡單的解釋算不上一個令人滿意的定義,但它似乎的確概括了六十年代以來所發生的事實:從事文學研究的人已經開始研究文學研究領域之外的著作,因為那些著作在語言、思想、歷史或文化各方面所做的分析都為文本和文化問題提供了更新,更有説服力的解釋。這種意義上的理論已經不是一套為文學研究而設的方法,而是一系列沒有界限的、評説天下萬物的各種著作,從哲學殿堂裏學術性最強的問題到人們以不斷變化的方法評説和思考的身體問題,無所不容。「理論」的種類包括人類學、藝術史、電影研究、性研究、語言學、哲學、政治理論、心理分析、科學研究、社會和思想史,以及社會學等各方面的著作。討論中的著作與上述各領域中爭論的問題都有關聯,但它們之所以成為「理論」是因為它們提出的觀點或論證對那些並不從事該學科研究的人具有啟發作用,或者説可以讓他們從中獲益。成為「理論」的著作為別人在解釋意義、本質、文化、精神的作用、公眾經驗與個人經驗的關係,以及大的歷史力量與個人經驗的關係時提供借鑒。
如果理論是根據它的實際效果定義的,把它作為改變人們的觀點,使人們用不同的方法去考慮他們的研究對象和他們的研究活動,那麼這些效果是哪種類型的效果呢?
理論的主要效果是批駁「常識」,即對於意義、作品、文學、經驗的常識。比如,理論會對下面這些觀點提出質疑。
●認為言語或文本即言語人「腦子中所想的東西」。
●認為作品是一種表述,在某個地方存在着它的真實性,它所表述的是一個真實的經驗,或者真實的境況。
●認為事實就是給定時間內的「存在」
理論常常是常識性觀點的好鬥的批評家。並且,只是一種歷史的建構,是一種看來似乎已經很自然的理論,自然到我們甚至不認為它是理論的程度了。理論既批評常識,又探討可供選擇的概念。它涉及對文學研究中最基本的前提或假設提出質疑,對任何沒有結論卻可能一直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事情提出質疑,比如意義是甚麼作者是甚麼?你讀的是甚麼?「我」,或者寫作的主體、解讀的主體、行為的主體是甚麼?文本和產生文本的環境有甚麼關係?
舉個甚麼樣的例子對一些「理論」加以説明呢?我們不要泛泛地談理論,還是深入到兩位最著名的理論家的一些深奧的著作中,看看能得到些甚麼吧。我舉兩個相關但又截然不同的例子,它們涉及對於「性」丶「作品」和「經驗」這些常識性觀點的批評。
法國思想史學家福柯在他的《性史》(The History of Sexuality)書中分析了他所謂的「壓制的假設」:通常人們認為,在比較早的時期,尤其是十九世紀,性一直是被壓制的,所以現代人便奮力解放它。福柯認為「性」根本不是一種被壓制的自然的東西,而是一
種錯綜的理念,是由一系列社會實踐、調査、言論和書面文字──也就是「話語」,或者「推論實踐」製造出來的──所有這一切在十九世紀共同製造了「性」。各種人的談論──醫生的、神職人員的、小説家的、心理學家的、倫理學家的、社會福利工作人員的、政治家的,等等──我嗎把這些談論與壓制性行為的理念聯繫在一起,事實上,正是在這些談論中才出現了我們稱為「性」的東西。福柯寫道:
關淤「性」的概念,以一種人為的統一把解剖學中的不同維成部分、生理功能、行為、情感、悠望的滿足等聚合在一超,而且使你能把這種虛構的统一看作一種根本的原因,一種無處不在的意義,一種處處皆有的、有待破譯的秘密。
福柯並不是否認具體的性行為的存在,也不是否認人在生理上有性別之分、有性器官。他要聲明的是在十九世紀出現了一些新的方法,把原本相去甚遠的、各個不同領域裏的東西一些我們認為與性有關的行為、生理的區別、身體的部位、心理的不同反應,還有最不同的社會意義,組合到一個統一的範疇之內(即「性」)。
人們談論和對待這些行為、情感和生理功能的方式創造了一個完全不同的、人為的統一體,叫作「性」,它已經被認為是個人屬性的根本了。
這樣,通過這個十分關鍵的逆轉,被稱為「性」的東西又被視為各種紛繁現象的起因,各種現象的歸一產生了「性」的理念。這個過程賦予性行為一種新的重要意義和一種新的角色,使它成為個人本質的秘密。說起「性慾」和我們的「性本質」的重要性時,福柯説:
我們已經達到了這樣一種境地,我們從多少個世纪以來一直被視為瘋狂的東西中期待我們的可知性……從一直被視為不知為何物的慾望中期待我們的屬性。因此,我們才會認為它如此重要,我們才會在它的周圉築起一道肅然的防線,我們才如此謹慎地去了解它,因此也才有了這樣一個現實, 即幾個世紀以來,它對我們的重要性已經超過了靈魂的重要性。
十九世紀使「同性戀」成為典型,幾乎成為一個「種類」。這正是一個能夠説明性是如何被作為個人秘密,如何成為個人屬性的根源的例子。早期,對於同性之間的性行為有過指責之詞(比如稱之為雞姦),但現在它已經不是行為,而是一個屬性問題了,不是某人是否有違反禁忌的行為,而是它是否「確實是」一個同性戀者。福柯寫道:雞姦是一種行為,而如今,同性戀已經成為一個「種類」。從前是人們可能會搞的同性戀行為,而現在它已經成為性行為的一個核心問題,或者叫根本觀念問題,是決定一個人的本質的根本問題:他是一個同性戀者嗎?
在福柯的理論中,「性」是由與各種社會習俗和實踐聯繫在一起的話語建構起來的:就是醫生、神職人員、行政官員、社會福利人員,甚至小説家們用以 對待他們認為是性行為現象的各種話語。但是這些話語把性描述為先於其本身而存在的東西。現代人大部分接受了這種描述,並且指責這些話語和社會習俗是在力圖控制和壓制它們自己正在建構起來的性。福柯在他的闡述中把這個問題扭轉了過來。他把性作為種結果而不是起因。他認為性是那些力圖分析、描繪,並且規範人類行為的話語的產物。
福柯的分析是歷史領域中一個議題如何發展成為「理論」的例子。正因為它給從事其他領域研究的人以啟迪,並且已經被大家借鑒,它才能成為理論。從公理原則旨在具有普遍指導意義這方面説,它並不是一條關於性行為的理論。它聲稱是對一個具體的歷史發展的分析,不過它顯然具有更廣泛的意義。它鼓勵你懷疑那些被認為是自然的,是先天給定的事物。反過來,問一問,它會不會是專家的話語的產物,會不 會是一種與聲稱描述它的知識話語相聯繫的實踐?按照福柯的理論,是要認識人類真諦的嘗試把「性」作 為人類本質的秘密創造出來的。
思考發展成理論的一個特點就是它提供非同尋常的、可供人們在思考其他問題時使用的「思路」。這種思路之一就是福柯提出自然的性行為與壓制性行為的社會力量(權力)之間那種假設的對立可能只不過是一種串通一氣的關係:正是社會力量使「性」──它們表面上要控制的事物──成為真實存在。再進一步──如果你願意的話,可以稱之為額外收穫──就是問一問,這種假相,即權力和人們認為是被它壓制 的性之間的串通正向了甚麼目的呢?當這種相互依賴被當成相互對立時,結果是甚麼呢?福柯對此做出的答案是,這種假相使權力無所不在你認為自己通過提倡性而抵制了權力,但事實上你卻是不折不扣地按照權力規定的條件行事。我們換一種方式來説,迄今為止,由於這個被稱為「性」的東西似乎是存在於權 力之外的一一是一種社會力量企圖控制,卻又無可奈何的東西一所以,看起來權力也是有限的,全然不是威力無比的(它連性都無法馴化)。然而,事實是,權力是無所不在的,它深入到各個角落。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文學理論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59 |
二手中文書 |
$ 255 |
小說/文學 |
$ 284 |
文學 |
$ 335 |
世界文學總論 |
$ 369 |
外國文學研究 |
$ 381 |
中文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文學理論
很難想像還能有另一本文學理論入門書會比這一本更加清晰,也難以想像別的一本書在這麼有限的篇幅裏能講出這麼多的內容。卡勒的闡述技巧向來備受讚譽,他這本書表現出講述文學理論最佳的方式和風格。
作者簡介:
Jonathan Culler
著名文學評家,美國康奈爾大學英文與比較文學系教授。
譯者簡介:
李 平
專業譯者
TOP
章節試閱
第一章
理論是甚麼?
在近代的文學和文化研究中有許多關於理論的討論──我要提醒你注意的是,這可不是指關於文學的理論,而是純粹的「理論」。對任何一位不在這個圈子裏的人來説,這種用法一定顯得很怪。 「關於甚麼的理論?」你肯定會這樣問。要回答這個問題的確是意想不到的困難。它既不是任何一種專門的理論,也不是概括萬物的綜合理論。有時理論似乎並不是要解是甚麼,它更像是一種活動──一種你或參與,或不參與的活動。你有可能被捲入到理論中去,你也有可能教授或學習理論,你還有可能會痛恨或懼怕理論。只不過,所有這些對於...
理論是甚麼?
在近代的文學和文化研究中有許多關於理論的討論──我要提醒你注意的是,這可不是指關於文學的理論,而是純粹的「理論」。對任何一位不在這個圈子裏的人來説,這種用法一定顯得很怪。 「關於甚麼的理論?」你肯定會這樣問。要回答這個問題的確是意想不到的困難。它既不是任何一種專門的理論,也不是概括萬物的綜合理論。有時理論似乎並不是要解是甚麼,它更像是一種活動──一種你或參與,或不參與的活動。你有可能被捲入到理論中去,你也有可能教授或學習理論,你還有可能會痛恨或懼怕理論。只不過,所有這些對於...
»看全部
TOP
作者序
前言
許多文學理論入門書都會對各種批評「學派」作出一番描述,理論被説成是一系列不能用同一標準衡量的「研究方法」,它們各自都有自己的理論地位和批評責任。但是各種理論介紹所確認的理論流派──結構主義、解構主義、女權主義、心理分析、馬克思主義、新歷史主義──又有許多相同之處。這就是人們為甚麼評説「理論」,而不是講那些具體的論述。介紹理論比較好的辦法是討論共同存在的問題和共有的主張,討論那些重要的辯論,但不要把一個「學派」置於另一個「學派」的對立面,討論各種流派內的明顯不同。
這要比概括論述不同理...
許多文學理論入門書都會對各種批評「學派」作出一番描述,理論被説成是一系列不能用同一標準衡量的「研究方法」,它們各自都有自己的理論地位和批評責任。但是各種理論介紹所確認的理論流派──結構主義、解構主義、女權主義、心理分析、馬克思主義、新歷史主義──又有許多相同之處。這就是人們為甚麼評説「理論」,而不是講那些具體的論述。介紹理論比較好的辦法是討論共同存在的問題和共有的主張,討論那些重要的辯論,但不要把一個「學派」置於另一個「學派」的對立面,討論各種流派內的明顯不同。
這要比概括論述不同理...
»看全部
TOP
目錄
vii 前言
ix 致謝
1 第一章 理論是甚麼?
23 第二章 文學是甚麼?它有關係嗎?
57 第三章 文學與文化研究
73 第四章 語言、意義和解釋
91 第五章 修辭、詩學和詩歌
107 第六章 敘述
123 第七章 敘行語言
141 第八章 屬性、認同和主體
157 附錄 理論學派與流派
173 參考書目
178 推薦閱讀書目
ix 致謝
1 第一章 理論是甚麼?
23 第二章 文學是甚麼?它有關係嗎?
57 第三章 文學與文化研究
73 第四章 語言、意義和解釋
91 第五章 修辭、詩學和詩歌
107 第六章 敘述
123 第七章 敘行語言
141 第八章 屬性、認同和主體
157 附錄 理論學派與流派
173 參考書目
178 推薦閱讀書目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卡勒 譯者: 李平
- 出版社: 牛津大學 出版日期:2016-07-01 ISBN/ISSN:9780199416660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192頁 開數:32開(19,6*13cm)
- 類別: 中文書> 世界文學> 世界文學總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