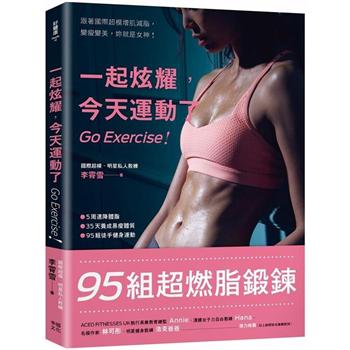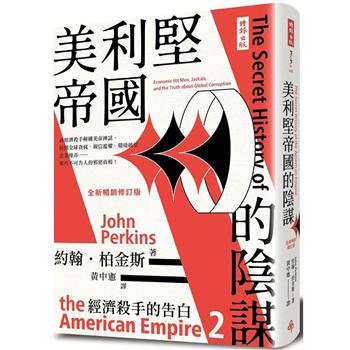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尋回香港文化(合集) 《尋回香港文化》+《都市漫遊者》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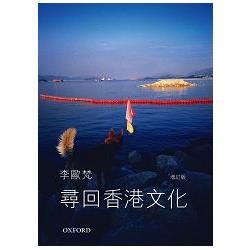 |
尋回香港文化(合集)-《尋回香港文化》+《都市漫遊者》 出版社:台灣商務 出版日期:2015-07-01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平裝 / 280頁 / 14 x 19.6 cm / 普通級/ 單色印刷 / 初版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323 |
小說/文學 |
$ 356 |
文學作品 |
$ 418 |
中文書 |
$ 419 |
社會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尋回香港文化(合集) 《尋回香港文化》+《都市漫遊者》
內容簡介
十多年前,李歐梵教授從美國哈佛大學提前退休,定居香港。香港成為他現在的家,四九年前作者輾轉從河南到台灣,再負笈美國留學教書,幾十年後再跟香港人結婚,回到故地,感慨之餘更以思考香港文化為己任,這就是作者居住香港的觀察和批判思考。十多年前分別以《尋回香港文化》和《都市漫遊者》兩書出版,現結為一集。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李歐梵
2015年香港書展年度作家,河南太康人,台灣大學外文系畢業,美國哈佛大學博士、香港科技大學人文榮譽博士,中央研究員院士。現為香港中文大學講座教授。曾任美國哈佛大學中國文學教授。曾任教普林斯頓大學、印地安那大學、芝加哥大學、加州大學洛杉磯校區、香港科技大學、香港大學。著述包括:《鐵屋中的吶喊:魯迅研究》、《中國現代作家中浪漫的一代》、《中西文學的徊想》、《西湖的彼岸》、《上海摩登》、《狐狸洞話語》、《世紀末囈語》、《尋回香港文化》、《都市漫遊者》、《清水灣畔的臆語》、《我的哈佛歲月》、《蒼涼與世故》、《又一城狂想曲》、《交響》、《睇色戒》、《人文文本》等。
李歐梵
2015年香港書展年度作家,河南太康人,台灣大學外文系畢業,美國哈佛大學博士、香港科技大學人文榮譽博士,中央研究員院士。現為香港中文大學講座教授。曾任美國哈佛大學中國文學教授。曾任教普林斯頓大學、印地安那大學、芝加哥大學、加州大學洛杉磯校區、香港科技大學、香港大學。著述包括:《鐵屋中的吶喊:魯迅研究》、《中國現代作家中浪漫的一代》、《中西文學的徊想》、《西湖的彼岸》、《上海摩登》、《狐狸洞話語》、《世紀末囈語》、《尋回香港文化》、《都市漫遊者》、《清水灣畔的臆語》、《我的哈佛歲月》、《蒼涼與世故》、《又一城狂想曲》、《交響》、《睇色戒》、《人文文本》等。
目錄
一尋回香港文化
3香港回歸五周年有感
7為香港打氣
21香港與上海
25通事與通才
32文化政策與文人空間
36小眾變大眾
39沒有昨日的酒店文化
43臥虎藏龍為何迷倒美國?
47藝術節
51博物館
55古蹟換新顏
59成龍的電影
63香港導演許鞍華
67香港牛棚書院
71香港大學講習班
75絕望之於希望
79獅子山下有感
83香港媒體與公共性
88香港的高等教育
二都市漫遊者
103澳門,歷史幽魂的棲息地
107馬來西亞,從現代發現傳統
111新加坡,多元文化都市
114新馬華人,新三民主義
118台灣,與惡俗為清流
122深圳,發現文化動力
126北京,在北大校園散步
129上海,時尚與品味
133上海圖書館的文人空間
137紐約,浩劫後的反思
141美國人VS紐約客
145世界文明的衝突
149零點地
153世界主義的心態
155全球化的文化爭論
159從梁啟超到世界主義
163全球華人與世界主義
166尷尬的過度現在化
170好書與好書店
174知識份子的當代作用
178報紙的反思空間
185文化雜誌與文字之美
189詩人企業家的靈感
193中國第六代導演
197尋找城市的文化建築
201生活方式的原味
205電影文化的幕後英雄
209渡假遨遊歷史與文化
212奧運精神之多少
216多元英語勢不可擋
220國語還是普通話
224方言、國語與文學
228艾薩克。史坦
232台灣媒體的語言暴力
236奏出祖國的悲壯
244日常生活的文學
247夏日讀書不沉重
258都市漫遊者
3香港回歸五周年有感
7為香港打氣
21香港與上海
25通事與通才
32文化政策與文人空間
36小眾變大眾
39沒有昨日的酒店文化
43臥虎藏龍為何迷倒美國?
47藝術節
51博物館
55古蹟換新顏
59成龍的電影
63香港導演許鞍華
67香港牛棚書院
71香港大學講習班
75絕望之於希望
79獅子山下有感
83香港媒體與公共性
88香港的高等教育
二都市漫遊者
103澳門,歷史幽魂的棲息地
107馬來西亞,從現代發現傳統
111新加坡,多元文化都市
114新馬華人,新三民主義
118台灣,與惡俗為清流
122深圳,發現文化動力
126北京,在北大校園散步
129上海,時尚與品味
133上海圖書館的文人空間
137紐約,浩劫後的反思
141美國人VS紐約客
145世界文明的衝突
149零點地
153世界主義的心態
155全球化的文化爭論
159從梁啟超到世界主義
163全球華人與世界主義
166尷尬的過度現在化
170好書與好書店
174知識份子的當代作用
178報紙的反思空間
185文化雜誌與文字之美
189詩人企業家的靈感
193中國第六代導演
197尋找城市的文化建築
201生活方式的原味
205電影文化的幕後英雄
209渡假遨遊歷史與文化
212奧運精神之多少
216多元英語勢不可擋
220國語還是普通話
224方言、國語與文學
228艾薩克。史坦
232台灣媒體的語言暴力
236奏出祖國的悲壯
244日常生活的文學
247夏日讀書不沉重
258都市漫遊者
序
前言
最近幾年,我發現自己的中文文章有點精神分裂。我對於當代文化的關注,似乎已經超過學術研究的範圍,而想親身介入,用一種叫主觀的文體做文化批評,所以學術的深度不足。但另一方面我似乎又不願意放棄學院中的文化理論,甚至在雜文中也引經據典,生怕學界同行以為我已淪落江湖,作不了學者。然而我對近代十年來美國學院中的「文化研究」(culture studies)的理論導向,也頗有不滿之處,它非但不注視文化本身的意涵──特別在一個世界性的多元語境──而且往往把文化作為學院政治的符碼,多以性別和種族的「弱勢」立場來反對資本主義的主流文化。把這種理論用以分析美國以外的其他地區的文化,免不了就有偏差,往往主題先行,表態至上,面對於細節的掌握和分析失之淺漏,而且語言過度抽象,長篇大論之餘,反而不知所云。
我得這一種矛盾反應,形之於文,就表現在這兩本集子(另一本《都市漫遊者:文化觀察》)的各篇雜文之中。這些文章,大部分是應《亞洲週刊》總主編邱立本先生之邀而定期寫就的「文化觀察」專欄,本擬寫完一年半載就停筆讓賢,生怕自己文思枯竭之後,無法維持該欄應有的水準,然而在邱先生堅持之下又欲罷不能,目前還在時斷時續的寫着。持續的主要原因是該刊的讀者群範圍較廣,地域遍及中、港、台、新、馬,和歐美華人社區,而且除了學界知識分子之外尚包括各地政界和商界的白領階級,我想每一個寫文化評論的人都希望自己的觀點能夠得到較廣泛的共鳴,甚或引起爭論,發生影響,但我又往往覺得自己屬於「小眾」,曲不高而和寡,所以也很少顧及到自己文章的流傳度。這又是另一種矛盾。
《亞洲週刊》上刊載的文章,「公共性」較強,所以我很少做個人抒情式的感喟(此類文章已收入其他集子中),然而「公共批評」的文體定位比抒情散文也更困難。我不願把自己架空──高高在上,故作客觀──所以往往作介入式的論述,而這種介入的出發點就是香港。最近幾年,我已經變成半個香港人:來港居住和任教的時間越來越長,所以親身介入香港文化的機會也越來越多,文章的內容涉及香港的分量也越重──甚至佔滿了一本集子。(這也是牛津大學出版社林道群先生的主意,他多年來為我編輯文集,在此要再致謝意。)其他的文章另編成本書的第二部分,則較注重某些理念(如「全球化」和「世界主義」)的討論和香港與其他亞洲城市──特別是上海──的比較。這個「雙城記」目前已成為熱門話題,我算是始作俑者之一,十幾年前初創此意的目的是為我的上海都市文化研究(見《上海摩登》一書),開拓一個更廣闊的比較空間,卻沒有料到我的「理論」竟被急驟變化的現實所取代,則非我意料所及。然而,我認為都市文化的互動是多元文化的必備條件,不是你死我活的經濟問題。目前香港人對上海的恐懼或嫉妒,和上海人自覺已經超越香港的自大自滿,都是不必要的心態。對於我這個「都市漫遊者」,任何一個有文化生機的大都市,我都有興趣,而且樂觀其成,所以最近有些上海學者批評我對於新舊上海都太過樂觀,因此也產生觀察和研究上的偏差。也有香港學者私下對我說我對香港太過偏愛,甚至愛之太深而責之益切。我對於這些批評都一概接受,並且歡迎進一步的討論。我之所以處處為當代華人的都市文化──上海、香港、台北、新加坡、吉隆坡、檳城──打氣,皆是基於一種信念:我認為當代文化的範疇就是都市,而中國讀者對於都市文化的認識──特別是都市文化的多元性和國際性──往往不足。「五四」以來,中國的城鄉分歧愈來愈深,但知識分子雖大多生活在都市卻處處以鄉村為依歸,所以才會產生「鄉土中國」的心態。中國的都市文化的發展,當然是不均衡的,而貧富不均和階級不平等一向是最為知識分子詬病的現象。然而這一種基於社會正義(social justice)的批評態度,往往也對都市文化產生偏見,或從道德或從經濟立場出發,把都市文化的種種弊病批評得體無完膚,特別對都市的通俗文化更視之如敝帚。如此看來,非但上海禁不起這種嚴格的審視,而且香港可能更乏善可陳,不愧為「文化沙漠」。
我個人並不贊同這種心態和立場。但更重要的是:我認為對都市文化應該培養一種「文化敏感」(cultural sensitivity),這種「敏感」應該是一種理性和感性、思維和形象的混合體,單靠抽象理論或印象觀察都嫌不足。這兩個集子中的文章,也可說大多是用來磨練我對都市文化的敏感性,是否有成,自當留待讀者決定。我一向對自己的語言能力(特別是中文)的信心不足,也許我的文體無法充份駕馭或表達我的意念和感想,在港台各散文大家面前,我只有自慚形愧。然而,能夠把這麼多有公共性的文化批評文章公諸於世,我自覺非常幸運。願在此再次向發表過這些文章的香港報刊雜誌──《亞洲週刊》、《明報月刊》、《明報》副刊、及《信報》文化版──表示謝意。除此之外,我竟能在一兩年間寫出這麼多文章,自己也覺得意外,這份靈感的來源,當然是我的妻子玉瑩。我們結婚時,我曾答應把今後所寫的每一本書獻給她,此二書算是開始。
最近幾年,我發現自己的中文文章有點精神分裂。我對於當代文化的關注,似乎已經超過學術研究的範圍,而想親身介入,用一種叫主觀的文體做文化批評,所以學術的深度不足。但另一方面我似乎又不願意放棄學院中的文化理論,甚至在雜文中也引經據典,生怕學界同行以為我已淪落江湖,作不了學者。然而我對近代十年來美國學院中的「文化研究」(culture studies)的理論導向,也頗有不滿之處,它非但不注視文化本身的意涵──特別在一個世界性的多元語境──而且往往把文化作為學院政治的符碼,多以性別和種族的「弱勢」立場來反對資本主義的主流文化。把這種理論用以分析美國以外的其他地區的文化,免不了就有偏差,往往主題先行,表態至上,面對於細節的掌握和分析失之淺漏,而且語言過度抽象,長篇大論之餘,反而不知所云。
我得這一種矛盾反應,形之於文,就表現在這兩本集子(另一本《都市漫遊者:文化觀察》)的各篇雜文之中。這些文章,大部分是應《亞洲週刊》總主編邱立本先生之邀而定期寫就的「文化觀察」專欄,本擬寫完一年半載就停筆讓賢,生怕自己文思枯竭之後,無法維持該欄應有的水準,然而在邱先生堅持之下又欲罷不能,目前還在時斷時續的寫着。持續的主要原因是該刊的讀者群範圍較廣,地域遍及中、港、台、新、馬,和歐美華人社區,而且除了學界知識分子之外尚包括各地政界和商界的白領階級,我想每一個寫文化評論的人都希望自己的觀點能夠得到較廣泛的共鳴,甚或引起爭論,發生影響,但我又往往覺得自己屬於「小眾」,曲不高而和寡,所以也很少顧及到自己文章的流傳度。這又是另一種矛盾。
《亞洲週刊》上刊載的文章,「公共性」較強,所以我很少做個人抒情式的感喟(此類文章已收入其他集子中),然而「公共批評」的文體定位比抒情散文也更困難。我不願把自己架空──高高在上,故作客觀──所以往往作介入式的論述,而這種介入的出發點就是香港。最近幾年,我已經變成半個香港人:來港居住和任教的時間越來越長,所以親身介入香港文化的機會也越來越多,文章的內容涉及香港的分量也越重──甚至佔滿了一本集子。(這也是牛津大學出版社林道群先生的主意,他多年來為我編輯文集,在此要再致謝意。)其他的文章另編成本書的第二部分,則較注重某些理念(如「全球化」和「世界主義」)的討論和香港與其他亞洲城市──特別是上海──的比較。這個「雙城記」目前已成為熱門話題,我算是始作俑者之一,十幾年前初創此意的目的是為我的上海都市文化研究(見《上海摩登》一書),開拓一個更廣闊的比較空間,卻沒有料到我的「理論」竟被急驟變化的現實所取代,則非我意料所及。然而,我認為都市文化的互動是多元文化的必備條件,不是你死我活的經濟問題。目前香港人對上海的恐懼或嫉妒,和上海人自覺已經超越香港的自大自滿,都是不必要的心態。對於我這個「都市漫遊者」,任何一個有文化生機的大都市,我都有興趣,而且樂觀其成,所以最近有些上海學者批評我對於新舊上海都太過樂觀,因此也產生觀察和研究上的偏差。也有香港學者私下對我說我對香港太過偏愛,甚至愛之太深而責之益切。我對於這些批評都一概接受,並且歡迎進一步的討論。我之所以處處為當代華人的都市文化──上海、香港、台北、新加坡、吉隆坡、檳城──打氣,皆是基於一種信念:我認為當代文化的範疇就是都市,而中國讀者對於都市文化的認識──特別是都市文化的多元性和國際性──往往不足。「五四」以來,中國的城鄉分歧愈來愈深,但知識分子雖大多生活在都市卻處處以鄉村為依歸,所以才會產生「鄉土中國」的心態。中國的都市文化的發展,當然是不均衡的,而貧富不均和階級不平等一向是最為知識分子詬病的現象。然而這一種基於社會正義(social justice)的批評態度,往往也對都市文化產生偏見,或從道德或從經濟立場出發,把都市文化的種種弊病批評得體無完膚,特別對都市的通俗文化更視之如敝帚。如此看來,非但上海禁不起這種嚴格的審視,而且香港可能更乏善可陳,不愧為「文化沙漠」。
我個人並不贊同這種心態和立場。但更重要的是:我認為對都市文化應該培養一種「文化敏感」(cultural sensitivity),這種「敏感」應該是一種理性和感性、思維和形象的混合體,單靠抽象理論或印象觀察都嫌不足。這兩個集子中的文章,也可說大多是用來磨練我對都市文化的敏感性,是否有成,自當留待讀者決定。我一向對自己的語言能力(特別是中文)的信心不足,也許我的文體無法充份駕馭或表達我的意念和感想,在港台各散文大家面前,我只有自慚形愧。然而,能夠把這麼多有公共性的文化批評文章公諸於世,我自覺非常幸運。願在此再次向發表過這些文章的香港報刊雜誌──《亞洲週刊》、《明報月刊》、《明報》副刊、及《信報》文化版──表示謝意。除此之外,我竟能在一兩年間寫出這麼多文章,自己也覺得意外,這份靈感的來源,當然是我的妻子玉瑩。我們結婚時,我曾答應把今後所寫的每一本書獻給她,此二書算是開始。
二○○二年七月十九日於香港
|